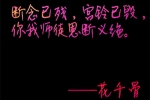喊出故乡名字作文800字记叙文【一】
自己一个人生活在外,家里的亲人依旧守在故乡,养育我的地方我不能抛弃,正是这些落后的观念深深植入爷爷奶奶的脑海,才造就了故乡里比任何一个地方都要落后、都要贫困。懂点事理的阿爷携着妻子儿女远离了故乡,而六叔他像木桥一样守护着故乡和那两个老人,在外发展前途多少可以更为憧憬,可六叔却没有。也是,在现实面前我们都很平凡,不争什么?不拿点什么?就要永远被困在故乡那个穷酸僻壤的地方。一旦有了好的以后,也可为称得上光宗耀祖,不枉费当初做下了背井离乡的这个决定。命运是有好多人不服的`,因为它对我们不公平,但时间久了人也就慢慢变得现实,在现实的强词夺理下一切都由不得我们,只有臣服、只有忍受与习惯。我身在他乡,也称游子,我心系故乡,那短短是时光只因无法磨灭,所以刻骨铭心。当我一个人,踩着满地枯叶回到这里,沾满身上的全是黄土气息,爬上很高的山顶神清气爽,我想我还是属于这里,因为心灵在这里能安稳,像漂浮已久的浮萍找到了依靠,像迷失了回家的孩子找到了方向,像远途旅客在沙漠中找到了绿洲,属于这个地方的我永远属于大山、大地、黄土、高坡。
这是我送你的风景,答应你的大好河山已经食言了,我只好用文字勾勒想象一幅美景,而美景,不过是我向你提起过的故乡。
早春,我的故乡一片青葱嫩绿,洒满山间角落里每一抹春色表现得格外夺人眼球,像酝酿好久的一幅画,绿色背景做铺垫。拐过山最后一个弯,木桥早已不复当年,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水泥桥,脚上还有一缕春意,踩过去看见竹林一片。风吹着竹叶仿佛点头含笑,一整个竹林正在晨曦中摇起纤细的腰肢,扭动的身体,手舞足蹈。走过竹林有条过道,上面几家瓦房,瓦上爬满青苔,炊烟笼罩得朦朦胧胧,披上一层白色纱衣,这是黄昏的嫁妆,新娘是这几户人家。故事可以在我笔下向你娓娓道来,可我不知的是你能否真的明白,就像这层白雾,隐隐约约间飘到山后坠跌,消失。怎么看都觉得像是雾里看花,看不清结局。晚上,这片天空被描得很黑,是谁画上了几颗星星让星光洒满你的肩膀?又是谁素描了你我之间整个平淡人生?是我把星星画在天上让星光洒满你的双肩,又是我素描了我们之间整个平淡人生,是我的不小心,硬生生的毁了这份友谊。坐在水泥桥上,听着河水潺潺流过,像弹奏的小夜曲,清脆悦耳,月光倾泻在水面上,依稀中仿佛还看见倒映在水里你的脸,美得就如那缕月光,清澈的瞳孔,干净的脸庞,我犹记得未曾遗忘。
秋天,像个掠取绿色的画家,涂上金黄,这里金黄一片,田里金黄一大片,思念慢慢老了学会了脱发,叶子被一片片落得利索,我想你也想得利索。干净的枝丫就等秋风将它折下,也好学着落叶归根。落叶是树的,树允许它离去归根,但枝丫是樵夫的,樵夫拾起的不可能叫归根,就像你被城市带走的也不再叫我的。我还想再到山顶那片草坪上坐一坐,还想和你谈谈我们的梦想,我想当一名作家,你想当一名医生,我想写我们的故事,你想治愈我们内伤,这里一个多么悲凉的故事。可能以后回到这里都是我孤身一人,这片草坪的草枯萎又变嫩绿,嫩绿又变枯萎,轮番了十余载春秋,这里有的只不过还是我一个外人。我怀念我的故乡,却怀念的又不仅仅是故乡,我写的是我的故乡,可又不仅仅单单写故乡,至少,故乡的风景是我送你。那些花开,你又记得多少?我的故乡,执笔之前总会想到你,落笔之前又会再次想起你,直到我合上日记,走出门外抬头一看,满天烟火。这时,烟火是你,留给我的纵然只是转瞬即逝的美,得不到也成了意外。
走了好远还是一个人,背后随着脚步慢慢淡出了你的故事,我离开了故乡,感觉每一步都走得很沉重,下不去脚像捆绑了一层枷锁。我终究还是回到了这座城市,这里繁华热闹喧嚣这里高楼大厦随处可见,这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可是这里,却开始让我心生厌恶。
喊出故乡名字作文800字记叙文【二】
“叮铃铃,叮铃铃,”一阵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一看日历,今天的安排是:上午9点至10点去新华书店选书,中午1点至3点把买来的书看一遍,今天的安排真是复杂,我不由得说道,唉,还不是为了准备采访20xx年的奥运会吗?想到这里,我看了看时间,快到9点了,该去新华书店买书了,到了书店后,书架上的书使我眼花缭乱,我找到了专属于记者的书,挑了几本适合我的.书,便去结帐了,接着,我慢慢的往家里走,到了家里后,差不多11点了,我就去吃饭了,吃完后,我就把今天买来的书拿出来看了,把重要的地方记录了下来,在采访时,该问哪个明星什么问题?我都要做一个详细的记录,就这样,我一直在看书,入了迷,竟然忘记了吃晚饭,等我回过神来后已经8点多了,就随便吃了点东西填饱了肚子就行了,吃完后,我又进房间继续我的工作了。就这样,一天,飞快的过去了。
这就是我的一天,为了能采访自己国家主办的奥运会,我还会继续努力的,加油!加油!
喊出故乡名字作文800字记叙文【三】
来这座城市已是一年有余了,虽不处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也不处在城市灯红酒绿的繁华之所,但是晚上的一盏盏路灯发出昏黄的光芒告诉我自己还是处在城市之中。身处城市的喧嚣之中,丝毫不到大城市的优越,反倒越来越思恋故乡。故乡虽与这座城市相隔只在咫尺之遥,但是一年到头却也难得回一次故乡。不是计较那几十块钱的车费,而是临在假期的时候总是被一些琐事缠得脱不开身来。也不知道家前面的那颗白杨树是否又长高大了些没有;也不知道门前的那窝竹子是不是越长越茂盛了;也不知门前的那颗桃树开花了没有。
人生的道路上有太多的不得已,然则我们只有默默去承受。为了我十岁开始离家住校。那时候是一星期回一次家,总是觉得一星期是那么的漫长,从周一就开始掰着手指算起,记得那个时候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周五的时候,听到的放学的铃声就是我们听到的最美的乐章。回到家中,父母还在田间劳作,最幸福的是莫过于和父母坐在家里的方桌边吃一顿饭,和弟弟时而吵两句嘴。这样日子周而复始的过了四年。然则岁月逝去,一转眼都到了高中,一周回一次家变成了一月回一次家,回家的次数渐渐的`变少,每次回家总是先给父母打上电话。每次回家父母都刻意在家等着我的归来。第二天天微微亮的时候,父亲便骑着那辆年龄与我相当的自行车到街市上去买些平时舍不得吃的菜。那时候回家我的心情也是相当欣喜的,因为在学校“艰苦”一个月后,终于可以吃到几顿好的。那无疑是一个月中最幸福最高兴的几天,没有繁忙的功课困扰,没有老师的管束,也不为自己以后的前途而担忧,在这几天也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
三年以后,回家的周期变得更长了,一年只能回去两次。哪怕只有两次我还是不愿回去。因为爸妈到沿海打工去了,为了过年能多赚点加班费,也为了过年能节省回来的路费,基本是几年才回来一次。每次回家看到空荡荡的家,看到别人家张灯结彩一家团圆的时候,心里总是有种莫名的忧伤,那个时候最期盼的就是自己赶快的长大,有能力养活父母,他们不在客居于远方的城市,遥望家乡的灯火。
想象总是美好的社会的现实总是那么的残酷,一晃自己已经毕业两年了,自己也还只是客居在城市中混个温饱,父母还是在遥远南方城市打工,弟弟却在北方城市工作。一家人相隔在千里万里之遥,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在一起匆匆的相聚几天,又匆匆的离别,看着父母两鬓开始斑白的白发,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痛。
喊出故乡名字作文800字记叙文【四】
回到西城后我第一时间去了梁老师家。其实停课只有短短一个多星期,时间却仿佛已经过去几个月之久。这些天面对着各种纷繁琐碎的事情,我的内心躁动不安,也忽略了梁杏和梁老师所处的境地。踏上楼梯的时候我不由得心生愧疚。
开门的是梁老师,他见我来了先是吃惊,然后客气地请我进屋坐。我没有看见梁杏,只见到她房间的门是紧闭着的。
“幸好两人都平安无事地回来了,”师母说着倒来一杯水,我这才暗暗放心下来。想到梁老师在外面那些陌生的地方四处奔波找梁杏的情景,那些细节不忍细想。在铁路停运的那几天,父女俩辗转好几趟长途客车,几个日夜不停歇地赶回来。“好在没什么大碍,外面这种形势,听说很多车站进去了就不放人出来,说是要一个一个测体温,出现一个高烧的其他人都得困着。”师母心有余悸地说着这些,梁老师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行了行了,又不是什么大事情……”大抵是不想让梁杏听见这些,她在房间里。
我看了看梁老师,他的头发更加花白了,沉重镜框下的双眼填满疲惫。一会儿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这几天你就过来吃饭吧,外面的东西没家里的干净,这段时间还是身体健健康康的最重要,等这一段时期过去了再说。”我正要推辞,但师母也说:“是的,我就每天多煮你一个人的米饭,不碍事,你下课回来吃就是了。”这让我多少有些不安,但又难以推脱。“等流感过去了,到时候你不想跑一趟就留在学校食堂吃就是。”她又说。
那天傍晚我吃过晚饭才离开。到了吃饭的时间,梁杏才从房间里出来,一脸沉默地坐在餐桌上,头也不抬。吃饭时候的时间变得无比漫长,我坐在梁老师一家中间显得突兀而尴尬,如坐针毡,恨不得立刻吃完离席,但又不能表现得唐突无礼,只能缓慢地嚼着米饭,等待时间分秒过去。梁老师不断喊我多吃,师母则不停往我碗里夹菜,总说我不敢多吃之类的。我发现,屋子里多了我一个人,至少可以使氛围改变了一点点,显得不那么沉寂。这样一想,便觉得不那么尴尬了。梁杏总是第一个吃完,放下碗筷便走回房间,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三天。我总摸不准吃饭的时间,有时候来早了,师母才开始做饭,我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这是最尴尬的时间。我来晚了的时候,饭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但大家都在等我回来才吃,饭菜明显都凉了。
几经犹豫,我终于开口对师母说明天不过来吃饭了,以期中的复习忙碌为由,语气犹豫,毫无底气。师母自然反对,说吃饭在哪里都一样的,不会太耽误时间。但这次倒是梁老师同意我不来了,说要不等方便的时候想过来就过来,显然是不想勉强我。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但在回来的路上竟越想越觉得懊恼,梁老师一家把我当作亲人_样对待,而自己却总因为不善言辞和不习惯接受恩惠而频频拒绝他们的好意,这是多么自私和吝啬的做法。这些年来我—直被这种感情困扰着,有时候真羡慕陆明,从不会因这些待人和相处的细节感到不适或犹豫。有些东西大概你不去想它就不会有那么多困惑了吧,但人与人之间又显然是那么地不同。
日复一日的生活又开始进入循环。有时在沉寂的傍晚听见学校外面马路上消防车开过带来的警报声,会觉得连灾难都成了装点生活的元素。那样的日子是有多么漫长和寂寥。
夏天是确凿地来临了,早在四月的末尾,阳光便显露出暴烈的迹象。这是在南方最常见的景象,冗长的夏季莽撞地提前开始,绵延着迟迟不愿结束。最不缺的就是阳光。相比于春季和秋冬,我还是很乐意夏天的到来,即使气温炎热。阳光热烈地照上一整天,鲜艳而锐利,伴随着蝉鸣,一切显得慵懒又热闹,直至黄昏来临时热气散去。似乎这样一来就能最大限度地消除生活中寂寥的一面。
六月初的一天,我突然见到了宋南。他站在楼梯入口旁边,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很久没回过神来。宋南看起来好像跟以前有些不一样,大概是很久没见,所以不免隔着一些陌生感。
我们来到上一次来的这家小馆子,那些景象依旧是过去的样子,天色将晚,外面的马路上车水马龙。我们开口的第一个话题果然是梁杏,我问他知不知道梁杏去找他,宋南说知道,梁杏去之前给他打过电话。
“我劝她别来了,她不听我说,说非来不可。谁知道后来。”
“你知不知道后来梁老师怎么找到她的?你们有没有替他想想?”我一想到梁老师奔波的样子便很生气。
“没想到后来会那样,没等到她来,我也差点儿被困在车站。我本来想早点回来,但这段期间外面的情况紧张。”宋南带着歉意说。
“这次回来是为了找梁杏?”
“嗯。”
“***妈知道?”沉默了一会儿我又问。
“我说在学校补课。”
我差点儿忘了宋南素来就不被束缚。但从这次的谈话中隐约可以感觉到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他似乎是在刻意地改变自己,和过去撇清关系,变得和所有人一样,也希望得到肯定和认可。大概在那个自由的世界里太久了,他渴望这种年纪里生活中最寻常的一面,如管束、苛责或称赞。那种自由意味着孤独。从他第一次告诉我他要跟他母亲离开的时候我就能隐约感知到这些。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梁杏了,可能以后不会再见她了。”
“……”
“我们都太年轻,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感情,你能说你懂吗?有些代价我们都付不起,这次是流感,但下次呢。梁杏还小,我承认我对她很愧疚。她还有很多东西要面对,要学会现实。我们也一样。”
“……以前我们到处玩儿到处游荡,以为打打架吸吸烟那样的生活就是过得爽快,其实心里都明白不是那样的,但又离不开,害怕孤独罢了。梁杏本来跟我们不一样的,她应该有她的生活。”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只不过是作为路人,恰巧见证了这一幕罢了。但我还是打心底感激宋南,他真诚地把我当作朋友并加以信任。从一开始放浪不羁时就这样,现在他要选择了新的生活,要彻底地离开了,便也把这些告诉了我。
那个傍晚宋南说了很多话,我默默地听着,听得恍然。直到天黑我们才从馆子里出来。临别前宋南给我留了一个新的电话号码,说了一些以后有机会来找他玩之类的话,我们便在学校门口道别。在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宋南。其实当我们说着这些道别的话时我就隐约想到了这些。十几岁的.年纪固然蓬勃,却是生长在夹缝中,总显得无力而又迫切。世界充满变数,一切都是遥远和未知的,包括我们自己。连说声再见都显得吃力,更不谈什么约定、承诺。
世界上所有的告别都是黯淡的,令人恍然。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同学说有人找我。我走进门一看是陆明,他正坐在我的床上,一脸恍惚。见我来了便哆嗦地站起来。
我说:“你怎么突然来了?都这么晚’了。”陆明的脸色显得异常,他一把拉起我就往外走。我问他怎么了’他不吭声,走到离宿舍几十米远空无_人的校道上才停下来。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我有些焦急,一定又出了什么事。
陆明显得很激动,喘气声越来越急促。
“到底怎么了?”
“她***了……”他的声音在颤抖。我瞬间头脑一片空白,又突然觉得好笑,这样的话只在电视里出现过,现在竟然在我面前被最熟悉的人说出来。
“谁?……谁***了?”
“王宏丽,你记得她吧,她给我打了电话,说有了孩子,是我的……”
我一时语塞,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记得他说的那个王宏丽,他曾经把手机上的照片给我看过,说是在加油站上班的,比我们大几岁。当时陆明说只是玩玩而已,没想到他们—直来往。
“怎么办,白桦?”他哆嗦着,眼泪都流了出来。
“你确定那是真的?”
“我不知道,她下午给我打的电话,叫我去找她,我没去,就直接来找你了。”
“她只跟你在一起吗?有多久了?她说的……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我们偶尔也一起出来玩……就那样,白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沉默。陆明捂着脸无力地蹲在地上,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无助的样子。但又觉得这样的情景是如此熟悉,仿佛同样的场景曾经出现过一般。剥开生活给予的层层外衣,此刻在我面前的陆明又成了过去那个因犯了错而显得无措的少年,仿佛时间从没过去。
“你先不要急,”我故作镇定地说,“还有没有谁知道?”
陆明抬头看着我,目光迫切。
“应该没有,”他想了想说,“她也是才发现的。”
“陆明,”我发现我的声音有些颤抖,“你听好了,我们还小,不可能任由那些事情发生,再说我们自己都无法养活自己。你等会儿就给她打个电话,孩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要的,我们还年轻,你想想,不能一辈子就那样过下去的,你无论如何要和她说清楚。”我有些激动,掌心渗出冷汗。陆明也听得恍然。
“明天就去把它打掉,”我听得出我的声音在哆嗦,“你先想好了要怎么跟她说,无论如何不能要。”我竭力地抑制着紧张,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陆明点点头,脸色煞白。
没有别的办法。我一想到这是一个无异于结束一个生命的严峻决定,额角就冒出了冷汗来。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们沉默了好久。校园里空荡荡的,只听得见风吹树上簌簌作响。
“已经很晚了,给***打个电话说晚上不回去了。”我心有余悸。
陆明“嗯”了.一声便又陷入沉默。
“饿了吧?我们先到外面找点吃的。”我又说。
陆明点点头站起来,走路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腿还在颤抖着。
回到宿舍后陆明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后说已经跟王宏丽说了,明天早上就去。那天晚上我们在宿舍的床上挤了一夜,两个人几乎都没有睡着。
漆黑中我感觉到陆明还沉浸在深深的惶恐中,也没有合眼。过去似乎有着无数个如此重复的夜晚,我们躺在黑暗的房间内彻夜说话或沉默无言。那些时光贯穿了成长中整段忐忑不安的时期,而这次不一样。世界上越来越纷繁、越来越巨大的事物正在向我们袭来,在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不安也越来越巨大。
脑海中胡思乱想着这些,时间无比艰难地过去。
我惊醒时陆明正在耳边喊我的名字。“天亮了。”他说。他一夜未睡。
我让同学帮我请假说家里有事得回去一趟,便跟陆明匆匆走出来。车停在附近一个纸厂的院子里,陆明整个人沉浸在一阵恍惚中,倒车的时候两次险些撞到柱子上,为此便越发地着急。
“慢点儿开,我们不急。”我用尽量轻松的语气提醒他。
他脸色汎重,一路上默默无言。
此刻的陆明是无措的,平日里那些坚硬盔甲在惶恐中全部崩塌,而他无措的时刻似乎都在被我见证着,如同依赖一般毫无保留地,从年幼无知时开始,一直持续到此刻我们风尘仆仆地赶去面对更大的恐惧。那么多年。
车驶进清晨的雾水中,两边的房屋、树木和田地在飞快地退后。有一些瞬间我突然觉得像被什么深深击中,我如此切肤地感受到陆明身上的那些感受,那些无助、寂寞和不安。那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享用着相同的岁月,相同的不安和喜悦,而此刻他俨然成了我自己。
喊出故乡名字作文800字记叙文【五】
也有槐树。
春末夏初,满树挂满了一串串莹白的花,味道和香气一样,甜而微涩。
打小儿生长在渤海边上的那个小村子,没什么历史,建筑一律平房,三面环树,后面是一大片苇塘。春天的时候,枣花开了,空气中都是蜜甜蜜甜的香;芦苇长到一人高,风吹过去,绿色的波浪一荡一荡的,就那么一直赶过去,望也望不到边。
上高中要骑车到三十几里地外的`县城,那时一多半是土路。村子里同去上学的没有女孩子,结伴的是几个男生,也有同年级的也有更高年级的。周末休假,和同村的几个男生一块骑车回家。那时星星都开始亮亮的闪了。拐进村子,很清净的街上传来一两声狗叫,嗅着炒白菜的香气,那么温暖的心情,一路回家。
我那时身子弱,骑车技术不好,几个男生嫌我累赘,就糊弄我让我自己先行一步,他们随后追上来。那么坑坑洼洼的路,目光所及,除了地上齐人高的玉米,天上点点的麻雀,一线线的太阳光线,没有活物。一阵风过,玉米叶子唰啦啦从头响到脚,身上不由得汗毛直竖,冒一层细汗,加紧赶路,好不容易望见楼房的影子,才松一口气,回头,还没有那帮男生的影子。
有一次我的自行车坏了,有一个同年级的男生驮我回家,车子骑得飞快。我问他,我沉不沉?他说,不沉,像个书包一样。
如今我们那一群都已长大,学业小成,在城市定居,偶尔相聚,携家带口。可是那些记忆,永远那么美丽,槐香一样甜蜜温暖。
今早我换夏衫的时候,在镜子前旋转,施施然飞个眼风,问:相公,我漂亮吗?老公笑眯眯拍我的头:老漂亮了。
哈哈。
“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