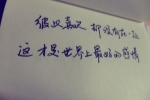小学生睡衣描写作文【一】
大家认识我吗?我长着两只又大又圆的眼睛,锐利的爪子,坚硬带钩的嘴,圆圆的脸和一双宽大的翅膀,与众不同的是我的头部上侧左右各长着一丛毛,很像猫耳朵。你们猜猜我是谁?
对了!我就是鼠类的克星、田园的卫士--猫头鹰。
人家都在电视、画报上见过我们,对我们并不陌生。我们住在郊外或田野的树上,白天休息,晚上出来觅食。我们的眼睛在白天没有多少用处,是个睁眼瞎,但一到晚上,我们的双眼能洞察一切,在黑暗的林间或田野中准确地发现诡秘的鼠类行踪,无论多么狡猾的老鼠也休想在我们的爪下逃生。
我们的翅膀也很特别,翅膀的骨头中间是空的,而且非常大,这样我们能够轻盈地飞起,无声无息地接近捕猎目标,以至于它们往往还没有发觉,就做了阶下囚。
我们猫头鹰是候鸟,冬天,我们到气候温暖、食物充足的'南方去过冬,等到春天来了,我们再回到北方繁殖后代,壮大我们的队伍。
我们的种类有十多种,我们的踪迹遍及世界各地。我们这个庞大的家族,抑制着鼠类带给人类与自然的灾害。不信,你瞧!我们每只猫头鹰一个晚上能吃十五只老鼠,这样一年就能吃五千多只老鼠,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呀!当人类的食粮受到保护,减少了财产被鼠咬的破坏,危及人类生命的鼠疫得以控制,人们不会忘记这里也有猫头鹰的一份功劳吧!
当然功不必自论,我们只希望成为人类的朋友。可遗憾的是,有的人把我们视为灾星,什么夜猫子进宅,祸事到来,这是个别人的偏见,我们不计较;可气的是,有些人大肆砍伐树木,使我们无家可归;更不能容忍的是,有的人用各种器具对我们肆意捕***,照这样继续下去,我们这些鼠类克星就会面临灭绝的危险。我们保护着人类,而威胁我们生命的却恰恰来自于人类。
人类——我们的朋友!你们想到没有,当我们在地球上消失之时,就是鼠害成灾之日。到那时,庄稼被破坏,财物被咬食,鼠疫横行威胁人类生命,再想起我们岂不晚矣!大自然不止一次地向人类发出警告,谁破坏生态平衡,谁就会受到无情的惩罚!
我们真诚希望人类不要再向我们举起屠刀,猫头鹰和人类永远是最亲密的朋友,让我们共同努力消灭鼠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小学生睡衣描写作文【二】
我们是不同的种族,来自不同的国家,身处不同的环境,可是,我们都是孩子,我八岁,你也八岁,这是我们最大的共同点,一句hello,跨越了世俗的等级与仇恨,就这样,我们认识了。隔着铁丝网,两个不同世界的我们一起说话,一起玩耍,我们成为了对方最好也是唯一的朋友。
我们都会有怯懦的时候,都会犯错误,可是,朋友,对不起,我们还做朋友好吗?孩子总是那么善良,那么单纯,即使我的朋友对我做了不好的事,还是愿意选择原谅。我单纯的想,帮助你,会弥补自己曾经的过失,减少自己的愧疚。也因为我们是朋友,所以更想帮助你。也许在孩子的心里,友情便是他们的全部,没有世俗的眼光,没有等级的的观念,有的只是我想跟你做朋友,想要对我的朋友好。小孩的世界对大人来说是幼稚,但对孩子来说就是全部,他们的纯真,会让多少人羞愧。我们都曾经是一个孩子,都曾经拥有那份纯真,可是,它好像在我们长大的路上,慢慢被我们遗失了。
小学生睡衣描写作文【三】
在素描绘画当中,最关键的当然是结构。
现实中很多画家,由于对人物或物体结构缺乏了解,最后只能走形式的路子,在创作中很难拿出具有深度的力作。虽然我们已经有了方便的照相机(现在都使用数码相机)和扫描仪,可以在电脑中处理图形,能够省却很多造型的麻烦,但是,形是形,结构是结构,并不是一个概念。对绘画的过程而言,形是附着在结构之上的表象,而结构才是对象的支撑;外在形的轮廓无法真正表现对象的内在美。
我们所观察到的对象的外形,那是一种表象,一种轮廓。当对象一旦变换位置,而我们又缺乏对结构的了解,就很难着手。在初学阶段,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利用稳定的三角形来确定形体的大体位置和构图,然后再用小的虚拟的三角形、方形等分解被画对象局部的位置,这样的方法最后只能是比葫芦画瓢,照相般描绘对象。
就像我们已经走过了充饥的年代一样,我们已经走过了缺图的年代,正跨入一个读图的时代。各种图形、图像、图库层出不穷,再用照相的方法——抄照片去再现对象,倒不如干脆去搞摄影算了,那我们还不如照相机来得客观。对画家来说,最难以接受的便是被人夸奖为:看画得多好,像照片一样。也就是说,那些个作品没有强烈、强调和更深层次的东西,缺少画家对形体结构的理解和对对象的内涵表现的创意,这又怎么能算得上绘画的艺术作品呢?
艺术的真实,并不是纯客观的真实,而是画家通过自己的感官和手,表现画家内心的感受的一种艺术的真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刻画与刻划。
小学生睡衣描写作文【四】
对于二战,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一次次地回望,透过历史书上的文字、黑白的纪录片、灰黑色矗立的墓碑来了解过去,了解那个压抑而疯狂的年代。
揭露犹太人大屠***的电影不少,诸如《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师》等都是震撼人心的作品。然而因其视角的与众不同,《穿条纹睡衣的男孩》才能给人以独树一帜的灵魂叩击。
在一个8岁的男孩眼里,世界是怎样的?年幼的布鲁诺所看到的,是蓝色苍穹中的黑烟,是广阔天地中的“农场”,还有他固执认为玩“数字游戏”的“条纹睡衣”。童稚的眼光与冰冷的现实交替闪现,让那些残忍变得触目惊心。
“在黑暗的理性萌发之前,用以丈量童年的是听觉、嗅觉以及视觉。”开篇引用英国诗人约翰·贝哲曼的这句话,为电影奠定了基调。
影片开头的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在还没有搬离柏林时,布鲁诺和伙伴们在大街上疯跑,张开双臂作出飞翔的样子,兴奋得大喊大叫。在衣着鲜丽的小男孩身后,一个苍白瘦弱的妇人正在士兵的呵斥下被推搡上卡车。一车的人神色凄惶无助,然而布鲁诺只是兴奋跑过,盲目的嚷着“Goodbye,Jews”(再见犹太人)。也许他只是熟视无睹,也许我们不能指望8岁男孩的同情心。
即便如此,孩子就是孩子,他们能以清澈的眼光分辨人性的善恶,即使一直被教育“犹太人都是恶魔”,布鲁诺也依然纯真地与萨穆尔玩耍,友好地对待为他包扎的犹太老人。孩子所代表的良知深深地折射出现实的丑恶,冰冷的残酷在稚气的眼睛里粉饰太平,然而这样滑稽的扭曲,落在旁观的我们心上才变得令人羞愧,忍不住想要逃离。
“有时候,时代太残酷了,你闭上眼,不忍注视。”
影片的最后,瓢泼的雨声里撕心裂肺的哭喊逐渐归于沉寂,镜头定格在一排排“条纹睡衣”上,无言的控诉在黑暗中回响。大概所有人都想过让布鲁诺不要死。然而在我看来,若不是这个结局,这部电影就没有意义了。悲剧因缺憾而美丽,这种凄美因而动人心魄。
战争是人类文明的罪恶。文明已经无力去替哪些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们祈祷,唯有不断地回望过去,才能阻止那些恐惧与悲伤出现在属于我们的未来。
小学生睡衣描写作文【五】
前几天,我看了一部引人深思的电影,讲的是二战时期德国男孩布鲁诺结识了犹太男孩希姆尔,两人结成好友,最后悲惨地死去。
最令我感动的镜头是看到布鲁诺他们被赶到毒气室时,两个好朋友手握着手,安详地笑着。衣着单薄的两个人还在打着抖,单纯地相信一定会过去,令我难忘的还有他们那两双充满童真的、蓝色眼睛。看到这里,豆大的泪珠滚动到我的脸颊,我感到了战争的残酷。
“为什么?”我不停地问,为什么这一对天真的孩子又成为了纳粹扼***犹太人的又一祭品。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德国人对孩子的“洗礼”,让他们从小心里充满憎恨、邪恶,让多少孩子失去了童真。如果布鲁诺长大会成为一个战争贩子、一个***人机器,那还不如让他怀着“童真”死去,保持永远的天真无邪。战争可以扼***这对好朋友,但扼***不了纯洁的童心和他们那深深的友谊!来吧,手握着手,去到天堂。一个想成为探险家的男孩他有错吗?难道怀着纯真有错吗?不,不,他没错,是战争的错!
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呀!这对好朋友一起上学、一起分享美食,一起笑着拍球,甚至一起进入梦乡。如果没有战争,这对纯真的孩童就不会死,他们的父母也就不会担心,不会死亡!他们一定会一直怀着一颗充满爱的心直到死去。
让我们反对战争、反对残忍,充满童心,直到……永远。
小学生睡衣描写作文【六】
我看着这篇电影,就仿佛来到这位男孩身边,与他同生共死。
这篇电影就是讲述了一位名叫约翰·布鲁诺的小男孩是一位德国人,它的爸爸是一位军官。有一次,他爸爸升职了,被派到乡下去管理犹太人。于是,布鲁诺只好离开了他心爱的伙伴,跟随爸爸来到乡下,但是在那里没有伙伴,他的妈妈只让他在院子里玩,布鲁诺很喜爱探险,经常院子探险。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一位正在修车的军官,向他要一个轮胎做秋千,他跟着一名穿条纹睡衣的犹太人,来到后花园的储藏室里拿到了一个轮胎,并且发现只用爬出窗户,就可来到一片树林。这片树林正是布鲁诺探险的好地方。可仅有八岁的布鲁诺怎么会知道,穿过这片树林就是犹太人的集中营。他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进了树林,穿过小溪,看到了犹太人的集中营。正巧一位叫萨廖尔的男孩坐在那。不久就成了朋友,都把自己的心事告诉对方。后来,布鲁诺知道了萨廖尔的爸爸已经失踪三天了,希望布鲁诺帮忙来找。
第二天,布鲁诺也穿着条纹睡衣进了集中营。布鲁诺与萨廖尔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堪称集中营的地方,竟是一座“***人工厂”烟囱里的黑烟却是毒气。后来,布鲁诺的爸爸命令把犹太人关在一间屋子里,往里面放毒气,他和犹太人都死在这间屋子里。八岁的布鲁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凶手竟是自己的爸爸。这位布鲁诺的爸爸是多么无情、冷酷,布鲁诺的死应该就是对他爸爸的报复。
战争是多么可怕,不仅摧毁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还让那么多的孩子无家可归,甚至失去生命。
请杜绝战争!远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