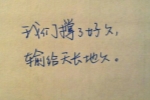写有说话艺术的小作文【一】
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的人把嘴巴的功能的次序颠倒了,嘴巴的第一功能本来应该是吃饭功能,然后才是说话功能,至于这两个功能的先后顺序我想是毫无疑问的,能有不吃饭而成天喋喋不休的人吗?没有;能有不吃饭就能侃侃而谈而且激情昂扬的人吗?没有;可见,吃饭是嘴巴的第一功能应该毫无疑问的了。然而,颠倒过来以后的嘴巴功能变成了什么,傻子都会明白,第一是说话,第二才是吃饭。颠倒过来的次序似乎有精神主义者的高尚之誉,不像我的观点容易落得个物质主义的庸俗之辈。然而我们都是容易上当的人,因为我们人类最大一个缺点就是虚荣心,这个虚荣心害人不浅。本来自己要活着,就先要吃饭,本来是个简单的问题,却因为有了虚荣心的支配容易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复杂化,于是就有了大多数的共识:那就是说话在先,吃饭在后。对于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老祖先就留下很多:“祸从口出”,“静坐莫论他人非”,在老舍先生的茶馆里就张贴着一幅“莫谈国事”的标语。可见,说话问题着实在先,因为你的嘴巴说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了吃饭问题。
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也谈的是说话问题,故事讲得是一个富人家里添了孩子,满月之际,亲朋好友都拿着礼物前去祝贺,其间,大家都说了吉祥祝福的话,无非是这个孩子将来一定“大富大贵”“长命百岁”,然而很不幸的是有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却说了一句:“这个孩子将来是要死的。”结果就遭到了众人的谴责,主人也把他轰了出去。故事完了,鲁迅先生总结说:说孩子要死的倒是真话,因为还从来没有见过不死的人,倘若有,那地球上早都站满了人。而说孩子“大富大贵”“长命百岁”的虽然好听,但是就不一定说的是真话。因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那样的好运。然而事实上说话的结果呢?说真话倒被赶出家门,没得吃上主人备上的宴席;而说假话的呢?却成为主人的座上客。这个故事倒是非常经典,也能够充分为人们说明嘴巴的功能:不能不是说话在先,吃饭在后,因为倘若不会说话,连得饭都吃不上。可见老祖先的经典言论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倘若为了吃饭而说话,说一些假话,奉承话,讨好话,谄媚话,动听话,这于听话的人而言,也就不见得有多受用,甚至还要因为这样的话而被“捧***”。《乌鸦和狐狸》的故事大概连几岁的小孩都知道,狐狸说的话好听不好听,自然很好听;乌鸦的歌声美不美,自然不美;但是受骗的乌鸦还是喜欢听这样的话,结果他一张嘴巴,嘴里的.肉就掉到狐狸的嘴巴里了。这个故事讽喻的道理很浅显,讲假话的狐狸骗到了美味,喜欢听假话的乌鸦反而受到了愚弄。原来为了吃饭而说的话不见的都是“真话”,这于听着的乌鸦而言是有大教训的。如果乌鸦仅仅是只有一口肉,受到欺骗后也许就能马上明白狐狸的险恶用心,以后不再上当听狐狸的假话;然而倘若乌鸦有很多肉,就不一定在乎,说不定自己一高兴,还会专门到家里再衔来一口肉赏赐说假话的狐狸。可见,说假话终究是为了吃饭,而为了吃饭说的话就不一定是真话了。
然而我们终有不为吃饭而说假话的仁人志士,这些人为了自己国家的强大,为了自己民族的复兴,敢于趟真言,揭时弊,以笔为剑,直刺丑恶的咽喉。他们的文章或为匕首,或为投枪,或为手术刀,横扫一切妖魔鬼怪,他们无疑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他们,和那些说假话混饭吃或者只要不说话就能有饭吃的人像比较而言,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他们因为说真话不仅丢掉了饭碗,甚且有的丢掉了性命,但是他们为人民而言,为国家而言的精神却永远被人民深深地记住,他们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丰碑,成为民族的良心。
倘得社会的进步,就不能不说真话;倘得民族的振兴,就不能不听真话。还是回到开始的议题,嘴巴的功能就是一是吃饭,二是说话;而不是一是说话,二是吃饭。如果坚持一是说话,二是吃饭的认识,难免要惹上说话是为了吃饭的嫌疑的。倘若有的饭吃,有的话说,说了真话还受到欢迎,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了。
写有说话艺术的小作文【二】
看到《艺术哲学》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这一定是本偏理论化的哲学书,读过以后,感觉它更像是一本介绍意大利,尼德兰,希腊历史,种族,风俗习惯与艺术的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枯燥乏味,反而更加吸引了我去了解这些城市的过去,去感受它们的文化,去品味它们的艺术生活。
《艺术哲学》是法国的伊波利特·丹纳所著,我看的是张伟所译的,据译者介绍,丹纳是深具传奇性的天才人物,就连他也被丹纳广博的学识、独特的思路、缜密的分析以及精辟的见解所折服,我就更不用说了。这本书一共有三篇,分别是意大利的艺术哲学、尼德兰的艺术哲学和希腊的艺术哲学。大致都是围绕时代,种族和风俗来写,各有各的特点。作者开篇就提出这样一条规律“艺术作品必然与条件完全符合,任何时期的艺术品都是按照这一规律产生的”,然后用意大利的绘画史来证明和应用这条规律。作品与环境必然完全相等,不论什么时代,艺术品都是按照这条规律产生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这条规律同样适用。艺术确实源于生活,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甚至是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必须投身于它们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就拿意大利和尼德兰来说,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意大利的目光转向了健康、有力、活泼的人体,所以意大利绘画多表现理想的美丽的人体;而尼德兰多表现现实的甚至是丑陋的人体。
在意大利,色调是固定的,在佛兰德斯,景物的色调总是随着日光和周围水汽的变化而变。说到这,我又想到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环境下,使得文化具有了差异性,也正因为不同的环境,才有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和艺术。“艺术作品必然与条件完全符合”,在丹纳的条件里,‘种族’是一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因为种族的不同,日耳曼族与拉丁族不仅在艺术上的本性对立在风格与趣味上也形成了类似的对比。“后者与前者相比,虽没有那种塑像般的美妙形体,情趣粗俗一些,性情比较迟钝,但精神的安稳,气质的冷静,使他们能更坚实地把握住理智”。《艺术哲学》从意大利,尼德兰,希腊的地理位置,人种,风俗习惯,历史,政治等因素谈起,到其艺术形式的产生于发展,向我们论证了开篇所提出的规律——不同的环境决定不同的艺术风格,也说明艺术来自生活,是生活给了它发展的空间。所以,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单单要有强烈的自发的,独特的情感,更需要的是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对风土民情的细微差别有着高度敏感的心。
在欧洲的诸多文明古国中,意大利算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在加上本人对这个城市的偏爱,我更喜欢谈谈我眼中的意大利。关于意大利画派的特征,其中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意大利画派轻视和忽视风景,却把人物作为主题。书中也提到过“艺术从质朴走向完满所前进的一大步,便是创造了完美的形体,这是理想的慧眼而非寻常肉眼所能发现的形体”。之所以特别提到这点,是因为想到了顾凯之提到过“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人物画也是中国画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占据着重要地位,至于山水画,直到隋唐才独立出来。两者相比,有共性,也有异性,相同的是都重视人物,不同的是对人物的偏重点却大有不同,前者表达理想的人体,后者以形写神,更注重人物的传神。关于他们之间的不同又恰巧说明了之前所提到的规律“艺术作品必然与条件完全符合”。
可想而知,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怎会与接受了文艺复习洗礼的意大利创造出同等风格的艺术作品呢?对于轻视风景,重人物的思想我也是能接受的,谁让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呢?书里也解释了意大利艺术表现人体的原因,我认为那些例子太过于黑暗,免不了背叛,仇恨和***害,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来说,尽管未曾身临其境,却仍不想多提。现在的'时代背景也有着与之相对应的产物,要想同样的艺术在世界的舞台上再度出现,除非岁月的车轮退回到有那样一种环境的年代。
此书着实令我受益颇深,只可惜我才疏学浅,无法用自己的拙笔体现丹纳艺术的灵魂深处,在今后的学习中,我定刻苦钻研,交上更令人满意的答案。
写有说话艺术的小作文【三】
对金先生这番话,笔者起初不大以为然,甚至有些愤愤然——世界上没有跟钱有仇的人,谁不爱钱?谁离开钱能活命?如果说老外艺术家不爱钱,那些天价艺术品,那些五花八门的画商、画廊、经纪人、拍卖公司……是谁发明的?如果画家都不要钱不卖画,那些画廊、拍卖公司岂不早就关门了?那些画商、经纪人岂不早就饿死了?再说了,外国即便有不爱钱的画家,也是因为他们不缺钱,别墅住着,汽车开着……中国画家爱钱,是因为我们穷怕了,穷够了。穷则思变,穷则思富,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当冷静下来再仔细咂摸金先生的“逆耳之言”时,笔者的愤怒渐渐消退了——人家批评的没错啊!罗列的现象也完全是我们美术界的事实。再细想想,其实金先生还没说全,当代某些中国书画家早已经拥有了票子、房子、车子,但仍然“疯狂地追逐金钱”,甚至不惜“流水作业”“批量生产”,丢人啊!
毋庸讳言,我们的确是穷人乍富,好不容易有了发财的机会,心态失衡可以理解,爱钱也没有错,但是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家,成为大师,确实就不应按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仅仅把攫取金钱、获得物质享受作为“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因为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追求,思想境界庸俗,人格低下,其作品必定很难达到陶冶心灵、美化生活、匡正世风、流传后世的高度和水平;而一个国家的艺术界,如果整体沉溺在追逐金钱、满足物欲、铜臭弥漫的状况里,就确实是严重的病态了,如不痛下决心根治,最终必然要遭到国际社会以及子孙后代的鄙夷、嘲笑、批判和唾弃。
一方面,艺术家也是肉身凡胎,不可能完全抵御金钱物质的诱惑;另一方面,纯粹的艺术创作又天然排斥“唯利是图”“金钱挂帅”。那么,艺术家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妥善地处理艺术与金钱的关系呢?
笔者认为,无论在何种背景、何种条件下,要求艺术家人人做到“重义轻利”或“重艺轻利”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在艺术界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提倡“重利重义”“重利重艺”,号召艺术家“爱钱不忘爱艺术”“爱钱更要爱艺术”,应该是既符合人性又切实可行的措施。
“重利重义”“重利重艺”,即是对待金钱与艺术二者并重,互不矛盾,互不排斥。具体到书画家个人,可以聪明,但不可以精明;可以经商,但不可以做商人。书画家与购藏者是特殊的买卖关系,出售的作品一定要物有所值,性价比合理,即让顾客花钱买到好东西。在这方面,许多中国古代艺术家做出了正面榜样,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他痴迷艺术,甚至弃官从艺,作书作画精益求精,水平登峰造极,但他也绝不讳言自己爱钱。在那篇著名的《润格》中,郑板桥不仅开列出真金白银的书画价码,还特别强调“要现钱”。实践证明,顾客掏钱买了郑板桥的书画,无论在当时,还是留传给子孙后代,没有一个人是吃亏上当的。
郑板桥重利,但更重义。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郑板桥毅然选择“舍利取义”——他曾郑重宣布自己的画是“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农夫乃为天地间第一等人”。普通劳动阶层的朋友虽然少钱或没钱,但如果真心喜欢他的字画,他不仅绝不再坚持“大幅×两、小幅×两”,还经常无偿赠送。
当代画家吴冠中先生是爱艺术胜过爱金钱的典型——他在物质享受面前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清高和淡泊,尽管作品价值连城,名声如日中天,却甘愿终生布衣蔬食,居旧屋陋室,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地画画、写文章,绝对堪称金兑庭先生所说的“对艺术无比虔诚敬畏”“一心一意在做自己内心里的事情”的“纯粹”艺术家。
但愿我们中国艺术界里少一些“疯狂地丢了魂一样地追逐金钱、房子、名车”的人,多一些郑板桥、吴冠中这样“爱钱更爱艺术”或“爱艺术胜过爱金钱”的艺术家。
写有说话艺术的小作文【四】
一只小猪懒洋洋地躺在猪圈里呼呼睡觉,可它被小杨小梅的背诵声吵醒,它瞄了瞄院子里的杨小梅,哼唧了一声,继续去睡。
刚闭上眼睛,那些数字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钻进它的耳朵里。它只好哼哼唧唧地站了起来烦躁的猪圈里来回走着。嘴里嘟囔着说:“你们人呀!真是麻烦,还要学习,你看我天天睡觉无忧无虑的多好。”
杨小梅见猪会说话,很奇怪,惊讶的问:“小猪你……你会说话?这……这太神奇了。不过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妈妈说读书识字是件很快乐的事,我想你是因为没有知识才会这样说的,所以我不怪你。”
“可我还是要说!学习太累了,整天背呀念呀的!多烦呀!
“喂!小猪。”杨小梅不满地说,“你太懒了,根本不知道知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快乐,哼!”
小猪听了很不服气,“什么什么?我太懒了,哼!要是我想学一定比你学的快,我们猪生下来就是天才。”
“那好!咱们来打赌,以后我把在学校学的知识教给你,你要是能学会,我就服你了,你看怎么样?”
“成交。”小猪很爽快的答应了。
从此杨小梅把学习的地点挪到了猪圈边,每天对着小猪讲她这一天学到的知识和故事,杨小梅发现小猪真的很聪明,不到半个月就学会了拼音,甚至能从头到尾地背下来,比杨小梅学的还好,而且每次她讲新知识的时候,它睁着好奇地大眼睛仔细的听着。杨小梅教完它一天的课程,出去玩时,它也不休息,嘴里唠唠叨叨的.背着拼音。
一只小鸡见它如此着魔,尖叫道:“小猪你是不是疯啦,整天就知道念abc。”小猪没听见,另一只小鸡说道:“是呀!自从小主人教它知识后,它就不像以前那么安静了,哎!其实学知识有什么用以后还不是被人吃掉……
小猪没听清两只小鸡在说什么,只是隐约间听见了它的名字,心想她们一定在赞美我的勤奋,于是它开心地说:“嗨!小鸡姐姐你们不知道,书本上那些故事充满着乐趣,可是我还不能完全认识上面的字,所以我要抓紧学习。”说完小猪陶醉地抱着书本继续学习去了。
两只小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明白小猪说的是什么,它们想这只猪一定是傻掉了,学了几天知识连自己是猪都不知道了。
很快杨小梅发现小猪在一天一天变瘦,眼珠变的发黄,脸也变长了。“小猪,”杨小梅对它说“你瘦了,快休息休息玩一会吧!不然你会生病的。”
“身体有什么要紧的,我一心想要学习,想要多认识一些字,好能读懂更多的故事。”小猪不再理会杨小梅说什么,只顾看着书里的故事入神。
这时妈妈来喂小猪吃饭,她敲着小猪的饭盆叫着它,可是它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
“小猪,你坐在那里干什么呀?快来吃饭啦!”妈妈叫着小猪说。
小猪摇晃着脑袋,微微的闭上眼睛,一副入神的样子。喃喃的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妈妈惊讶地对爸爸说:“你来看看这头猪怎么啦?最近我发现它有点反常……变得非常古怪……”
妈妈没有发现杨小梅在一边慌乱的表情,爸爸走了过来狠狠地用棍子驱赶着小猪:“赶紧去吃饭了,我可不喜欢一头猪装模作样的猪!”
小猪被主人打疼了,它气愤的站了起来,不满地看了主人一眼,它觉得主人真野蛮对待动物没有一点爱心。要知道它现在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它是一头有知识的猪。
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爸爸说:“这只猪越来越不像话了,白白的吃着粮食,却不长一点膘,这样还不如送到屠宰场去。”
“送到屠宰场去?”杨小梅惊讶地问爸爸,“为什么要把小猪卖到屠宰场去?”
“傻孩子!为了吃猪肉啊!”
杨小梅开始哭了起来,她坚持反对把小猪送到屠宰场去,可是爸爸妈妈是不会听她的话的,大人们一向如此。
杨小梅痛苦地意识到小猪将要面临的灾祸都是她一手造成的,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又是哭又是闹,两只脚不停地跺着地,于是,爸爸生气地大声说:“一个不听话的猪已经让我烦透了,难道你也想要挨巴掌吗?”
杨小梅怕了,委屈的站在一边哭了起来。
下午,小猪还是被爸爸送走了,小猪被抓上车的时候,它抓住铁笼子嘶喊着,“你们这些野蛮的家伙,不知道我是一只有知识的猪吗?你们这样***生就是犯罪……
杨小梅流着眼泪看着小猪临被拉走时那痛苦的表情,她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猪学会知识也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学的知识越多给它带来的痛苦就越大,因为它毕竟只是一头猪。
写有说话艺术的小作文【五】
写文章,我常困惑:其一是说什么,其二是怎么说。据胡适之先生的意思,这事似乎容易解决,因为只要“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和“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便好了。简言之: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叶圣陶先生主张,“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笔下就怎样写”,“语文一致”。两位大师从根本上点出说话和作文是一回的事。具体说来,人为什么要说话呢?因为心里有想法,有看法,要告诉别人。那人又为何而作文呢?卡夫卡说:“我有一种写的冲动。”试想一下,古今中外,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名著,难道他们也都是领导甚至和某部门签约后才让写的吗?人要作文,也是因为得到什么见闻,产生什么想法,要急于告诉别人一一这就是“一种写的冲动”。弗洛伊德把它归纳为潜意识,并且锁定它是创作的动力。清代诗人黄遵宪云:“我手写我口”,也道出了说话和作文的密切关系。
说和写是一回事,都是表达说话人和写作者对某一事物的印象、感受和看法。但为什么实际操作中,我们会觉得说话容易而作文难呢?这是因为,说和写是“一回事”的同时,尚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两者使用的语言形式不同,说话用的是口头语言,它有声无形,很随意,说完了就消失了,作文用的是书面语言,它有形无声,写出来可以长久留存下去,甚至让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例如《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名著,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并且它们还传遍世界各地,被搬上银幕,搬上舞台。所以,写作者更不能随意乱写,、要讲究一定的分寸,遵循一定的准则,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正如我们自家人吃饭和请客吃饭不一样,前者可以随便弄一两个菜,可以不摆桌,随意端着饭碗边散步边吃饭,唯求吃饱就行;而后者,一定要讲究饭菜的优劣,一定体面地围桌而坐,更不能随意走着吃。这都是作为社会人要承担一定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需要。正如周作人所云:“我写的文章和在讲坛里所说的同样的.负责任,决不愿误人子弟。”
说话表达清楚明白皆可,但作文除此,更求表达的艺术效果。立意高远、耐人寻味、章法巧妙、词藻优美、形象生动、言简意骇等等术语都是用来规范作文的。清代桐城派作家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也是针对作文而提的。作文比说话难就在这里,此外,尚有一种说法,是说说比写易的最根本原因,是二者练习的时间大不一样。我们没上学之前,就懂得说话,能够表达一定的意思,但究竟还不能作文。上了学,就算每学期练写作十篇,总共也就几十篇近百篇,和每日多次张嘴说话比,动笔练习的机会的确太少了。这说明,写比说难不是写的本身造成的,而是我们学习的机会太少了。因此,我们提倡精读大量名著,养成作和写的习惯,日常勤练笔,好文章是可以写得出来的。从小学生到高中生,增至大学生,经过多年的练笔,许多人不也都写出像样的文章吗?这也不正说明作文是不难学会的吗?
说与写相比,有时写还真是有其容易的一面。譬如同学聚会,每个人都要即兴演讲,你没有准备,心里慌,只说了几个字便作罢,或讲得无头无尾,没条没理,一定达不到说话的效果。怎么办呢?难道你会挽留大家,说你可以再来一遍?君子一言,岂驷马能追?讲出的话,是泼出的水,是很难原样收回的。倘若先前写好了一篇稿子,情况就不同了,写的好处就在这里。想想,完成一篇文章,我们可以列提纲,一段又一段地充实内容,可以查阅资料,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至自己满意了,再拿去请教别人;有不足之处,仍可以商量和修改。
作文这东西,越往里学越尝到甜头,也越觉得它博大精深,也越难于攻关。比如打跳棋,你为自己辟道路,可对手又处处设卡设陷阱,每走一步都不容易。突然能一棋跳到顶,甚至拿了赢局,那是多令人高兴的事。试想,若没有对手干扰,或他索性说:“算你行,我不动了,你跳吧”,那还有何意思呢?这和我们跟别人吵架时说“算你厉害了,你有理了,我输了不就行了吗”有何异呢?作文也是这个道理,困难不小,又学无止境,关键要知难而进,尽管赢不了它,但跟她“吵”到底还是有益的。
写有说话艺术的小作文【六】
一般而论,我们在实物中感到兴趣而要求艺术家摘录和表现的,无非是实物内部外部的逻辑,换句话说,是事物的结构,组织与配合。艺术家改变各个部分的关系,一定是像同一方向改变,而且是有意改变的,目的在于使对象的某一个“主要特征”,也就是艺术家对那个对象所抱的主要观念,显得特别清楚。这特征便是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本质”,所以他们说艺术的目的是表现事物的本质。
艺术家必须是生性孤独、好沉思、爱正义的人,是个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流落在萎靡与腐化的群众之间,周围尽是欺诈与压迫,专制与不义,自由与乡土都受到摧残,连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觉得活着不过是苟延残喘,既不甘屈服,只有整个儿逃避在艺术中间。
文明过度的特点是观念越来越强,形象越来越弱。日常的精神活动从此变为纯粹的推理。所谓精神状态是指一个人的观念的种类、数量、性质。但人身上还有比观念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结构,也就是他的性格,换句话说是他天生的本能,基本的嗜好,感觉的幅度,精力的强弱,总之是他内部动力的大小和方向。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一章,丹纳谈到了很多当时意大利仇***、下毒、暗***的资料,这对了解《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的背景很有帮助。(十五世纪的意大利)理论家中最深刻的一个是马基雅维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还是正派的爱国的人,有很高的天才,写了一部书叫做《论霸主》,说明奸诈和凶恶是正当的,至少是许可的。说得更正确些,他既没有许可,也没有辩护,他无所谓义愤,把良心问题搁在一边:他只用学者和洞达人情世故的专家身份来分析,解释;他提供材料,加上按语;古代生活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出于一个原因:就是非常平衡而简单的心灵。没有一组才能与倾向是损害了另一些才能与倾向而发展的,心灵没有居于主要地位,不曾因为发挥了任何特殊的作用而变质。少受过度文明的奴役,因此他更接近于本色的人。
所有这些对立地情形,归结起来只是一种全新地不假思索地文化和一种煞费经营而混乱的文化的对立。希腊人方法少,工具少,制造工业的器械少,社会的机构少,学来的字眼少,输入的观念少。遗产和行李比较单薄,更易掌握;发育是一条直线的,一个系统的,精神上没有***乱,没有不调和的成份,因此机能的活动更自由,人生观更健全,心灵与理智受到的折磨、疲劳,改头换面的变化,都比较少:这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特点,也就反映在他们的艺术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