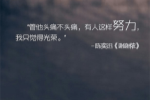栏杆初一作文600字【一】
五一假期,有幸读了梁衡先生的散文《把栏杆拍遍》。想来,读梁衡先生的文章不算早,先生以“一年一篇”的虔诚写作,给散文创作带来别样的文本,也为很多朋友带来了堪为“范本”的“工巧散文”。《把栏杆拍遍》使我沉醉,不能释手,通过此文我才真正了解辛弃疾充满豪情与苍凉的一生。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辛弃疾《水龙吟》
虽很早就知道辛弃疾,但对他的认识仅止于一位著名的词人,一位壮志未酬的爱国将领,内心却不曾为他激荡过。而先生的文章,不仅让我重新阅读了辛弃疾的词,重新感受了一次辛弃疾,从而真正认识了悲壮得让人荡气回肠,执着得让人心痛不已的辛弃疾。在先生的笔下,他,真真切切得站在了我面前,一位沙场英雄,有着“封狼居胥”的壮志,有为君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热血,然则现实却将这一切敲碎。爱国将军辛弃疾南归之后,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只剩下羊毫软笔,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他只能“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感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他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他用尽一生都在等待一个能重新征战沙场,报效国家的机会。“可谁又能懂他这个游子,实际上有着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本想以身许国,泪洒大漠,如今却空有一身力、一腔志而无处使。唯有登上危楼,痛拍栏杆。江水悠悠,似词人长叹,掩埋在历史的长河中……从词中跨越历史去体会当年稼轩的心境,这是我所不曾体验过的。毕竟,历史早已蒙上了太多的色彩和渲染,而梁衡先生用丰富的想象和深刻的理解为我打开一扇窗,让我看到了一个“积300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的,在文人中具有“唯一性”、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把栏杆拍遍的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辛弃疾。
掩卷沉思,再三咀嚼。如不是有渊博的学识,深邃博大的思想,梁衡先生怎能从中发出如此多的感悟?《把栏杆拍遍》一文中富有哲理的句子如同一泓清泉沁人心扉,笔下所绘的稼轩一颦一笑若隐若现。于是,在梁衡先生字里行间所注入的无限深情中,真切感受到先生对词人的同情和惋惜。我想如果稼轩在世,也会有当年白乐天那种“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感慨。当然,更有知音为何在千年之后出生的余恨。而我在阅读此文时,时而为其绝妙的一笔而赞叹,时而在平淡中品味生活的哲理,真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栏杆初一作文600字【二】
《园冶》是我国明代关于造园理论的一本专著。作者计成对造园艺术中的几个主要方面,如造园的指导思想,园址选择,园林布局(包括建筑、门窗、栏杆、墙垣等的构造和形式),掇山、理水、置石、择木、铺地、借景等,都有系统阐述。无论对我国造园史、建筑史的理论研究,还是对造园设计和景观艺术的实践,都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书不仅仅是谈" 园子" ,妙在融" 天人合一" 的自然观、环境观," 精而合宜" 的建筑观," 随曲和方" 的空间观为一体,言简意赅。
原文系四六文体,读起来却不涩,极富诗情韵味,朗朗上口。再配以陈植老先生多年辛勤而成的注释,确是一本环境营造学科的建筑和环境艺术的专业必读常备书。 书中多有妙言警句,如" 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 ," 巧而得体,体宜因借" ," 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不一而足。 有" 好事者" 乎?《园》中一会耳!
首先,读《园冶》,要联系中国哲理,尤其是它“无往不复”的时空互涵观念,在中国古代园林与建筑中四维时空观表现得很突出。对比一下中西园林之差别,可以反衬各自特点。中国园林与中国山水画异曲同工,中国园林之偏爱借景实源于中国画之动点透视法,也就是在时光流逝,移步换景的观赏方式中去时空流与生命流的意义。西方园林几何式布局偏爱对景与夹景,在焦点透视中体会空间的深度与时间的停顿(宛如音乐中的休止),与油画照相式的复制世界同出一辙,反映了绝对时空观。
其次,在中国文化与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命题是一个硬核。计成的《园冶》虽然通篇贯穿天人合一理想,却并不具有天人感应的迷信。“切要四时,何关八宅”,表明他是反对风水术的。所以,在他的因借体宜理论中,反复强调天然之趣,却并不让人们去盲从堪舆形势的说教。因此,中国园林在利用地形,改造自然方面,表现了相当程度的`主动性。它既不同于英国纯自然的草地牧场式的风景园,也有别于日本抽象自然的枯山水园,中国园林是对自然的浓缩与提炼,在遵从大自然的前提下实现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理念。《园冶》一书,与其说是一本造园学,不如说是一篇新离***,充满着古代***人迁客的悲壮情怀与委婉叹息,这就是计成高出张岱、文震亨、李渔、沈复的原因,也是《园冶》成为奇书的条件。计成决不是一般舞文弄墨、故弄玄虚的俗士,这一点对理解《园冶》至为紧要。从篇幅上看,全书讲了不少法式制度,画了不少图样,但重点并不在此。事实上,全书重神轻形,重意轻技的特点非常显明。所以,一开篇,就强调“能主之人”,“妙在得乎一人”,并反复露出“构园无格”的观点。他还一再强调“更入深情”,“意在笔先”,认为即使顽夯粗拙之石一旦到了高明造园家手中,也可化腐朽为神奇。中国古代有“文如其人”的箴言,他自称“性好搜奇”,“想出意外”,其人之奇决定了其书之奇。我认为,只有理解了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理解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出入儒、道、佛、玄的实质,理解了他们那种由老、庄、易、禅,诗、书、礼、乐,琴、棋、书、画,诗肠酒胆所陶冶出来的狂狷人格和无所不在的“书卷气”,我们才能理解计成和他的《园冶》。
《园冶》是讲艺术的,它凝结着中国美学、文艺学、诗品、画论的精华,强调的是虚无微妙,灵感顿悟,曲折委婉,传神写意。率性之谓道,高明的作者能创作千古绝唱,完全是纵情任性的自然结果。这里体现出更高层次的天人合一。
栏杆初一作文600字【三】
对比手法是作家们常用艺术手法之一,梁衡也不例外。他在本文中就多处运用了对比,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突出。第一处运用对比是在引用了《破阵子》之后,作者先将它与岳飞的《满江红》比较,认为只有《满江红》可以与之媲美,然后又用杜甫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卢纶的“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与之对比,认为“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像、抒发和描述”,从而突出了辛词的“凛然***气和磅礴之势”。第二处对比是将他与陶渊明、白居易的从政经历对比,他认为辛弃疾“对待政治”,“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因为“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练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第三处对比是将辛弃疾的豪放与苏东坡的豪放作比较。苏辛都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因此文学史上是将“苏辛”连称的,但梁衡却在同中见出异来,他认为:“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因为“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而“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捶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可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而辛弃疾的诗正是这样的诗。第四处对比是将辛弃疾的婉约词与柳永、李清照的婉约词作比较,他认为“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精辟之语。
栏杆初一作文600字【四】
“草船借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顾茅庐”是那么脍炙人口!而它们都跟一个人有关,他就是诸葛亮。
1800年前,诸葛亮在与曹魏的战争中去世,蜀国一时失去栋梁,霎时间,蜀国像一个没有支柱的楼摇摇欲坠,举国上下无不悲痛,在民心难违,武侯寺就这样建成了,是诸葛亮与刘备的君臣合庙,在人们心中永久的保留了下来。
想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形象仿佛跃然心中,头戴纶巾,手持羽扇。又仿佛看到了他身着八卦衣,借东风的场景,这位哲人,就这样在人们心中扎根,仿佛还能看到他为蜀国凝神沉思的情景,正如梁衡所说:“我看到了他初出茅庐羽扇轻轻一挥,80万曹军灰飞烟灭,我看到了他在斩马谡时那一滴难言的浑浊泪,我仿佛看到了他在向后主自报家产是那一颗无私的心……
1700年前,他输给了曹魏,但却赢得了从此以后所有人的心,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品质成为了我们的榜样,也许曹魏并没有那么”恶”但诸葛亮却像在眼前一般,手挥羽扇,微微笑着的那么亲切。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他便是死的重于泰山,深深的记载我的脑海里,无法忘记!
栏杆初一作文600字【五】
建筑的兴造,三分靠匠人,七分靠建筑师。因为兴造建筑首先要相地立基,然后定其开间、进深。这些尤其需要建筑师的能动性,须考虑场地的大小、形状等,如果地基偏缺则可不必拼镶整齐,屋架也不必拘泥于一般的三间或五间,在一定条件下,出现半间也是很好的。
园林的兴造,九分靠造园家,匠人只占一分。这是因为园林中的巧于因借,即因地制宜、借景取胜的精巧不是匠人可以达到的。
计成充分强调了设计师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完全体现在设计师可以因地制宜,而匠人只能拘泥于古法。正式的建筑多为三间、五间,而计成鼓励根据场地情况的特殊性,可以不完全遵守这些,亭台楼阁的建造更是自由,这种观点的论述在整本书中不断出现,体现了他的思想开明进步。
栏杆初一作文600字【六】
学过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后,我从词的字里行间中领悟诗人当时的那种壮志难酬的愤懑和对国家无限地热爱和拥护之情。今天我又阅读了梁衡的《把栏杆拍遍》一文,对辛弃疾这位诶大的词人更增添了许多敬佩之意。
文中写道:“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的,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是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的确,辛的词掺杂了太多的内心深处的情感和自己的抱负与胸襟,让我们今日重读他的文章时,仍会像作者一样,感到一种凛然***气和磅礴之势。
作者写出了辛弃疾的《破阵子》,那恢宏的气势和那其间流露出的爱国热情,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撼。
作者写道:“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它的一生大都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修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
我们为辛弃疾而叹服,为他而痴狂,但我们更要坚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栏杆初一作文600字【七】
梁衡的人物散文,写的大多是人杰鬼雄,其中大多是名垂宇宙,家喻户晓的伟人,还有文惊当世,传之百代的文人。而这些跨越千年、百年的人物却从作者的笔端一一鲜活起来。梁衡的散文情理并重,以评带传,他写的人物在千年百年中已有定论上又重新给出评价,而这种评价又是不落窠臼的。人们都承认辛弃疾是个大词人,但能从他的出身到成业的发展史上判定辛弃疾的词及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的,梁衡是第一人。作者还在文中借郭沫若评说陈毅的“将军本色是诗人”来评说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说辛弃疾是“词人”是“武人”是一般人的判断,而说辛弃疾是“政人”恐怕就是梁衡的独见了。梁衡说“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作者还将辛弃疾的为政与陶渊明、白居易的为政作了比较,表明了辛弃疾为政的投入与积极。他能从人性的深层重新来诠释一位人物,在文章最后一段,作者在分析辛弃疾走上诗词创作道路的必然性时就作了这样生动的评说:“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捶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著名作家梁晓声在谈梁衡的一本散文集时说:“我确信,作为一个勤于思想的人,梁衡对历史的反思,肯定比他写出来的以上篇章要更深邃更全面些。而他后来发表的《最后一位带罪的功臣》、《觅渡,觅渡,渡何处》、《把栏杆拍遍》,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思想一游到更远的历史中去,一与那些历史时期中的人物敞开心扉地对话,则就变得火花四溅了。文字也时而激昂;时而惋叹;时而叩问;时而调侃,姿肆张扬起来了…… ”
一般来说,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事件、人物,写其“思想”容易,写出“美感”来难。常见的通病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梁衡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使“思想和美感”达到了和谐统一。他像一位烹饪大师,非弄出个“色、香、味、形”俱佳才心满意足。他的那些评说文字完全不是抽象的概括和干瘪的教条,而是形象生动又充满美感的。像“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枝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纸笺”;像“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永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还有“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这些文字多美呀,读起来令人回肠荡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