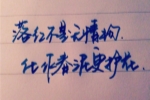向烈士说一句话作文【一】
“唉!唉!”今天晚上,我家一直传出这样的叹息声。这是谁发出的?制造者就是我。问我为什么叹息?还不是张老师布置了一个实践作业,让我们向父母说我爱你,这谈何容易?
这不,现在正烦着呢!该怎么办?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去当面表达比较好。于是,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到正在准备晚饭的妈妈面前。看到我走过来,妈妈忙不迭地问:“有什么事?肚子饿了吗?稍微等等哦,晚饭马上就来!”见妈妈这样,我有点不好意思,忸怩地说:“妈妈,我……我……”“嗯?怎么啦?”“我……我想吃饼干!”“哦,那你去拿啊,这孩子!”我手忙脚乱,把刚到嘴边的话一下子咽了下去。
我拿好饼干,急冲冲跑进了房间。等做完作业,出来吃好晚饭,正琢磨着跟妈妈说我爱你,不经意间一抬头,发现妈妈踮着脚正吃力地洗着碗。我看着看着,泪水便盈满了眼眶,思绪回到了那个中午……那天中午,妈妈去上班,而我则躺在床上,做着香甜的梦。却不知,妈妈发生了意外。晚上放学后,我听见妈妈躺在床上痛苦地***着,我一问,才知道,原来妈妈上班时下楼梯,脚一不小心别崴了,而她,为了不打扰我休息,硬是忍着剧痛,一踮一踮地去上班……想到这儿,我的泪水一下子决堤了,顷刻间喷涌而出。我哭着奔向妈妈,哽咽着。
妈妈十分奇怪,便问我是怎么了,而我,大声地说了一声:“妈妈,我爱你!”这话是发自内心的,是我最诚挚的感情。说完后,我的脸一直红到脖子根啦,很不好意思。正欲逃跑,妈妈喊了一声:“等等!”我迟疑地转过身,妈妈一把搂住我,轻轻地说:“我也很爱你哦!”
爱并不肉麻,它是人与人间的诚挚纽带,将每一个人,都栓的紧紧的。
向烈士说一句话作文【二】
我们班可谓是人才济济,强手如云。在这个班级里,我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丑小鸭”了。
我羡慕范潇龙雄辩的口才,老师刚提问他就举手;我羡慕陈燕婷娟秀的字迹;我羡慕陈瑜的文才,写起作文来一挥而就,下笔如有神;我羡慕苏亦昕流利的英语,说起英语来滔滔不决,犹如一个小老外……我羡慕别人也怨自己无能。
或许是渐渐没了信心,在班里,我几乎到了“默默无闻”的地步。有一会,一个同学借我一本书,这本书中有一句话对我深有感悟“我愿用自己的努力,编织一片片羽毛,使自己变成一只美丽的天鹅。”是啊,作者能努力使自己成天鹅,那我不能拥有自己的“闪光点”吗?
之后,我开始发现自己的长处。每天我都练习写毛笔字,有时作业一多,时间也往后移,弄得我很晚才能睡,但我始终坚持练习。每回,老师一布置预习的作业,我就在语文书上左标右写,把一本好好的书写得满满的……经过许久的努力,我的字在班上数一数二,上课,老师一提问,我就举手……我发现了自己的“闪光点”,渐渐走出了低谷,下课和同学们嬉戏,打成一片。
但我要感谢那句话,正是那句话,使我学会了争取,努力。即便我这只“丑小鸭”无法在春天变成天鹅,但我愿用自己的努力,让自己飞上蓝天。
感谢那句话,感谢那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
向烈士说一句话作文【三】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向烈士说一句话作文【四】
她从听到那句话起,就成了母亲。
阳光透过那扇已有些褪色的朱红色窗户洒在这张小床上,母亲看着床中的孩子,那如水晶般得双眸,那青里透着红的小脸,一张泛着浅红的小嘴一张一合。母亲面带着如春风般得微笑注视着这个精灵,好像在等着什么。
‘妈。。妈妈’一声娇嫩的叫声突然传来。没有一点预兆,像一场无息的暴风雨浇注在母亲身上。母亲停住了,双手搭在床边,眨眼忘记了,呼吸也悄然消逝,只有那像清晨里的第一缕阳光的目光,柔和而温暖,环绕在孩子身上。突然,她伸手抱起孩子,后退一小步,随即原地旋转起来。顿时母亲爽朗的笑充斥在整个房子。
此时,母亲像一个孩子,得到了她最为珍贵的东西。直至怀中的孩子打起了哈欠,两个小眼睛微微闭合,母亲才停了下来,缓缓走向前,两只手小心翼翼地把襁褓放回,这是她的世界,她的所有!母亲坐在床边的小凳,两只手随意地挂在床沿,一只拖鞋还在远处静静地躺着,可此刻,母亲的眼中只有那个精灵!
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一切都仿佛睡着了,只有那句话的余音和母亲柔和的目光在空中飘荡,旋转,翻腾!
孩子渐渐长大,也渐渐叛逆,也变得不爱说那句话。母亲因为孩子在学校与其他同学打架,被叫到学校。来的时候,母亲连深蓝色的工作服都没换,两个裤脚沾满了灰,一颗颗汗珠挂在母亲已有些愁纹的额头,母亲喘了喘气,‘你又。。’话还未完,就被他打断‘你来的时候就不能换件衣服吗?脏兮兮的是个什么样,来那么急干什么,有意思吗?’,母亲没有说话,看了他一眼,满身灰尘,脸上肿了一个包,旁边站了一个比他高很多的孩子,正轻蔑地瞥了他一眼。
母亲叹了口气,便向着老师走去。母亲领着他走出校门,向着与他干架的那个同学家走去,‘干啥去呀?’他不解地问。
‘给你。。讨个说法’母亲一改往日的温和,声音低沉而严厉。他知自己理亏,正想和母亲争辩,抬头而望,母亲已经走远,他只得跟上,心中有些不安。
他从未见过母亲发这么大的火,如果说母亲以前像是一湾平静的湖,而此时却像是一汪海浪咆哮,波涛汹涌的大海,母亲吵得面红耳赤,双眼不知是愤怒还是委屈留下了一行行沸腾的泪,一只手攥的发白,另一只不断的挥舞,有时重重地拍着防盗门,一时间,各种嘈杂声撞击着他的耳膜,他紧紧地抓住楼梯的铁扶手,缩在楼梯里,不住地颤抖,心脏砰砰直跳,双眼紧闭,头深深地埋在两膝之间。骂声,拍门声,喊声仿佛一张粘稠的蛛网,牢牢地绞住了他。可突然,一切都停止了。
‘他是我的儿子,我不许任何人伤害他’。只有这一声,他听清楚了。
他紧紧地跟在母亲后面,他不知自己是如何从同学家出来的,如何松开那只因恐惧而僵硬的手。但他知道最终母亲艰难地胜利了,可这疯狂的背后却只是为了讨个‘说法’!‘妈妈,我错了,我以。
以后再不惹你生气了,妈妈’他小声说道。母亲依旧向前走去,可又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猛地停了下来,也许因为泪流得太多,母亲很平静,只是把手放在孩子的头上,他突然感到了这只手的沧桑,这只手的艰辛,这只手所包含的一位母亲的辛酸。‘妈。。妈。妈,对。。对不起’他再也无法坚持住,在这黑夜中放声大哭,他紧紧地抱着母亲,在她面前,他永远只是个孩子!
他终将成熟,终将真正的长大,他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大学,母亲为此兴奋得连两鬓的白发都仿佛充满了活力。
‘妈,我说坐飞机的嘛,您看这火车多慢啊!’‘没事没事,这还不是为了省钱’母亲笑着说。一根根纹络拧成一朵朵花在母亲脸上绽放,头上的白发在阳光下闪耀着银光,像一群孩童在互相挑逗。
‘妈,你看那边,好美啊!妈,你快看啊,就要没了’
‘妈,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逗啊?’
‘妈,您吃您吃,我都吃了多少了,吃不下了’
母亲一路上都在幸福中度过,下车时倒还有些留念。站在月台,孩子拥抱着母亲,‘妈,我走了,您注意身体啊’‘诶诶,那是那是’母亲一个劲的答应,回过神来,只剩下儿子远去的一抹背影,想招呼儿子再叮嘱几句,可手举到一半,又缓缓放下,叹了叹气,朝着远方会心一笑。
黄昏夕落,秋风四起,一抹深黄勾勒出一个佝偻的影子,在晚风中轻轻摇曳着的雪白发丝中夹杂着一声又一声的叹息!
母亲听到那句话,哭了,笑了,老了。
那句话如同一个无法消除的烙印,母亲承受着。
可母亲无悔,因为那句话早已成为了母亲的一生,一辈子!
向烈士说一句话作文【五】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向烈士说一句话作文【六】
昨天下午的第三节课,张老师布置了两个回作就马上走了。当时我正在喝水,看了布置的作业我差点把嘴里含的水喷出来,作业少得可怜。一个是抄11——20的成语,一个是更强是说什么按43页的要求完成习作二的任务。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把水喷出来,还好我的“黄河”没有破堤而出。我咽下水打开语文书,我一下子笑不出来了。任务是“对爸爸(妈妈说我爱你”。看着这个任务,我脑海里涌出了许多问题,怎么办?什么时候问?怎么问?去问谁?我一下子陷入了沉思。
放学回到爷爷家,我匆匆忙忙做完作业吃了饭洗了澡,回到自己家。家中爸爸在客厅打电脑,妈妈在卫生间洗花瓶。机不可失!我马上走进卫生间,对妈妈认真地说:“妈妈,我爱你!”正在洗花瓶的妈妈先是一愣,又马上把神回了过来,放下手上的花瓶转过身来对我说:“儿子,不要这样说。妈妈对你感到很愧疚——你婴儿时我忙于工作,没时间陪你,常把你一个放在爷爷奶奶家,当你吵着要回自己家还嫌你碍事。等你长大了一点,我又去上海读书,没时间关心你的学习。现在自己身体不好,还经常对你发脾气。在你面前,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我马上说:“好了,妈妈这些事不要提了,过去的了就让它过去吧。我爱你,妈妈。”
我马上书房做作业了。做作业时,我的心里暖烘烘的,作业也快了许多。当我做好作业的最后一个字时,我看见妈妈的屋子还闪着灯光,我走了过去微笑着对妈妈说:“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