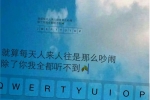我有趣的叔叔作文300字【一】
在圣玛洛号上,父亲将“福音书”撕成了碎片,像扔那牡蛎壳一般抛进了一望无际的大海。坐在船上的人不多。为了躲避暴风雨,船提前出航。
父母亲坐在甲板的一个角落,阴冷的海风吹得母亲瑟瑟发抖,父亲布满血丝的眼睛凝重地望着深黑色的大海,仿佛要把所有的不幸埋葬在大海里。
天灰沉沉的,乌云在头顶上翻滚。
我静静地坐在甲板上,没有了天空灿烂的晴明,只有眼前令人窒息的漆黑;没有了来时船上悠扬的乐曲,只有圣玛洛号气轮机的轰鸣声。海风的凄厉,波涛的汹涌,将我的五腑六脏都掏空了。父母的卧房中,昏沉的灯光,时暗时亮,母亲压抑的啜泣声和父亲沉重的叹息声使本已阴郁的空气变得凝固了一般。
我们终于没有躲过暴风雨。一声惊雷炸响了,闪电如一把利剑刺穿了厚重的天幕,天空被无情的撕开了一角,露出了血红的肌体。大海在怒吼!船被巨浪高高地抛到半空,又狠狠的掷下。惊叫声、哭喊声、呼救声、***声、祈祷声、呕吐声,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望着母亲痛苦得扭曲了的脸和父亲惊恐无措的神情,我吓呆了,瑟缩成一团。这时,一个黑影窜到我的眼前,——于勒叔叔?!我又惊又疑。只见他利索地将床单撕成宽大的布条,把父母亲扶到床上躺下,用布条将他们固定住,避免船体剧烈晃动时造成伤害。然后,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我不再发抖,一丝暖意从心底慢慢升腾,逐渐扩散到全身……
风停了,雨住了,平静的大海如羔羊般温顺,柔波低吟着,仿佛在倾诉心声。我握着于勒叔叔那双粗糙的大手,默默地站在甲板上。父母亲在另一头嘀咕着什么,还时不时地往这边瞧瞧。过了一会儿,只见父亲犹犹豫豫地走过来,他满脸通红,低垂着眼,支支吾吾地说:“我、我、我亲爱的弟弟,……多谢、多谢……
我们想请你回家、回家。”我看见叔叔那双浑浊而忧郁的眼睛里仿佛点燃了一团火,热烈而略有些潮湿,他的手在颤抖。他的嘴角动了动,但没有说什么。他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过了好一会儿,他平静地说:“谢谢哥哥,我很惭愧,没有带回钱来。在这船上,我可以干些杂役,养活自己,我过得很好。我知道你也不容易。”爸爸百感交集地一把抱住了叔叔。我抬头看看天空,湛蓝的天空如水晶般透明,恰如爸爸和叔叔的心。
我有趣的叔叔作文300字【二】
我们一家人回到家后,妈妈还是十分气愤,甚至在家中疯狂地喊着:“这个于勒,简直该死!”爸爸的脸上也露出失望的神情,好像不能接受摆在面前的事实,口中也不断地说着:“怎么会怎样!怎么会这样。”这十多年的期望,这十多年焦急的等待,在此刻都化为泡影,消失在空中。
不久之后,二姐也结了婚,因为双方家庭都没有多少钱。所以,不知情的二姐还一直等待着于勒叔叔的归来。父亲整天愁眉苦脸,好像没了精神支柱,母亲更是愈发变得暴躁。日子这样一天一天过着,一天不如一天。
直到有一天,父亲从报纸上得知,于勒叔叔在一次捕捞中,幸运的获得了一颗珍珠。父母因此欣喜若狂。母亲大声叫道:“我就知道这个于勒会发财的。”下午,母亲就做了可口的饭菜表示庆祝。
由于没有于勒叔叔的具体地址,父亲也托人在找他。
一天,一阵很有礼貌的敲门声后,父亲打开了门。“啊,于勒,是你,你终于回来了。”父亲满怀深情地说。“是的,哥哥,我回来了。”于勒叔叔激动地答到。母亲也***一句:“赶紧坐啊,都是一家人,还客气什么。”并倒了一杯水,生怕有任何怠慢。当父亲拿着手中的报纸,问到珍珠的事时,于勒叔叔垂下了头,说:“就在昨晚,它被偷了,我已经报了警,现在实在没有办法,我才来找你们的。”全家人都瘫软了,我的心里也凉飕飕的。母亲也强忍着心中的愤怒。
几个月后,警察仍毫无线索。由于我的强烈反抗,于勒叔叔留下来了。于勒叔叔的加入使我们这个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我有趣的叔叔作文300字【三】
我并不能说这是我最熟悉的一个人,但他在脑海中留下的印象总是胜过其他人。
叔叔的头是几位我熟知的亲戚中惟一谢了顶的,或许是我常看讽刺小说的缘故,每遇见他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纳粹头子“墨索里尼”抑或是莫里哀下的阿巴贡,但却又不着一副银白边框的眼镜,与那纳粹头子的脑袋又极不相称——含有几分学究的味道。
这是我初见他时给予他的几幅画像,但不想这画像都是驴唇不对马嘴的。
叔叔第一次来我家坐访,恰好我在书房练字,与我母亲说了几句话,但到底是捺不住性子坐下喝茶,迈个两三步,末敲门就蹿进我的书房,我正在抄李清照的《武陵春》,写到“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一句时,他夸道:“词好字也好!|,他又拿过字帖来仔细看一阵子,又补一句道:“李清照的《武陵春》啊,这种词摹写时,笔法清秀柔和一点就更好了。”说完他借来我的,仿着我的“闻说双溪春尚好,载不动许多愁。”写了半句,短短的五个大楷的,他却写得入了神,那笔法抑杨顿挫,那里带着一丝拘束?
叔叔在一旁微笑地自赏着自已的题书,我却只能沉默着,呆坐在椅子上,盯着那几个与我摹写毫不相***大楷,脸上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愠色——他不想自己随性地的几笔龙飞凤舞,却犯了我的大忌,练字时我很少能容忍字帖上的污渍,有时甚至不允许那怕是丁一点出现,更不用谈不相***其它行文了,不知所以然的叔叔被我不由分说地逐出书房,他却仍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刚一离开,我赶紧去涂拭那几个犯上作犯的大楷。
几日后,我再去翻看那天叔叔留下的笔迹残骸时,不禁有了几分悔恨,叔叔的专业是土木工程之类,他大概是很少题字的,那几个大楷其实相比我摹写的十多面帖字,实在是鹤立鸡群了。想到这儿我不禁有一丝愧疚,我又该如何弥补呢?我思索了很久一直没有答案。直到现在我也没见他题字了。
我有趣的叔叔作文300字【四】
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
我站在船头吹风,我可以看到母亲正阴沉着脸和父亲讨论着什么,我又想起那饱经风霜的脸,心情不禁有些压抑,我转头眺望别处,突然一群华丽衣裙的贵妇人吸引了我。
那色彩斑斓的衣裙晃动之间,我看到一个西装挺拔的模糊身影,我踮起脚正想看得清楚一点。“若瑟夫!”感觉肩膀被拍了一下,转头,原来是父亲。“你在干什么?”父亲顺着我的方向看去。“噢老天!”父亲突然尖叫,我也看到了,那个带着贵妇人走向母亲的人不正是叔叔于勒吗!“快快!”父亲连忙拉着我的手急促的走上去。
“嗨!于勒!”父亲赶上前,对着还有点没反应过母亲一个眼神,满脸讪笑的对着微笑的于勒说:“是于勒吧?这么久没回来!可想你了!”“啊哥哥,过得好吗?”于勒也满脸笑容的伸出手和父亲拥抱,母亲也谄媚的挤上,说着讨好的话。
晚上,母亲和父亲正在船舱里兴高采烈地讨论着,我在旁边坐着。
父亲说:“真是太好了!”母亲也跟着道:“我就说那个糟老头怎么可能是于勒嘛!”父亲笑了笑。我无意瞥到船舱门口的身影,我还没出声,便听到母亲继续说:“若瑟夫真是给他浪费了十个铜板,不过现在没事了!于勒有的是钱!”父亲应和一声,便说:“时间不早了,我们约好和于勒用餐呢!”
等我们豪华舱时,却不见于勒身影,只是最后于勒送来了一箱银票,附带一张纸条:虽然不知道糟老头是谁,但是我代他给若瑟夫送上回报。
我没去看父母的表情,便走出船舱。
我有趣的叔叔作文300字【五】
为了避免再次遇见我的叔叔于勒,我们家回来时改乘圣玛洛船。
我们走在碧绿的海面上,我们的船掀起的水花如同一个个海胆一样,在这海面上厌烦的跳跃着。
我和爸妈坐在船侧,而大姐、二姐和姐夫他们则在船舱。爸爸忧郁的望着船下的水花,而母亲则看着那上流社会的人们—一对穿着华丽又奢侈的小姐,绅士们,中间那位头戴高礼帽的男子似乎是被众人所尊敬的一位大佬。他十个手指每一只手指上都戴有一只硕大的黄金钻戒,又有着一根雕有眼镜蛇头的黄金拐棍,此时他正和周围的绅士小姐们谈笑风生呢。
母亲越看表情越怪异,随后扬手拍了父亲一下,说道:“咱们今天是撞了鬼了?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也特别像于勒。”父亲慢慢靠近仔细看了一会,匆匆的说到:“是有点像,我去找船长打听一下。”
父亲找到船长,问了一大堆问题,例如法国的风土人情,有合出产,土地性质怎样,等等。到后来我们搭乘的这艘“圣玛洛”号,随即谈到全船的船员。最后父亲终于说道:“我看那位穿着不凡的先生倒是很有趣。您知道他么?”
船长答道:“他曾经是个法国老流氓,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那时他已经改过自新,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人了,他在哈佛尔还有亲属,现在他正赶回去看望她们呢!并且他好像还欠了他们的钱。他叫于勒达尔芒司,—也不知还是达尔汪司,总之和这差不多的一个姓。”
父亲激动地说:“谢谢,谢谢您船长!”
他回到母亲身边,眼睛仿佛已经冒出了红光,兴奋的说:“是他,就是他!”
母亲也同样兴奋:“我一猜就是!我就知道他是不会忘恩负义的!不过还是有点不可思议。咱们来的时候不是也有一个叫于勒的么?我建议你再去问一下。”
过了一会,到午休的时间了,人们纷纷回舱休息了,趁这功夫,父亲跑到那位先生面前问道:“您是于勒达尔芒司吗?”
“您是菲利普么?”那人答道。
“苍天有眼啊!”父亲感叹道。“这真的是你么于勒?”
“我先你是认错人了,先生!”那人说道。“我是从一个几乎与我长得一个样子的老水手那里听来您的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