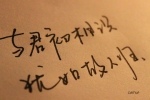以守候时光为题的作文【一】
眼前开门的女人,虽一头凌乱不堪的头发,不加修饰的面容,宽大的居家服上还沾着污渍,看起来普通到了极点,但她却一直是我心中最了不起的女人。
她,曾经是一个肤白貌美、行走于村子时尚前沿的女子。裙子尚未风行在乡村时,她就穿上了众多女孩儿羡慕的第一条裙子。染发风潮飘来时,她又成了这个素朴村庄里的一抹亮色。在庄稼地里,可以看见她劳作的样子;在进城的拖拉机上,亦可寻着她雀跃的身影。八、九十年代沉寂的乡村里,竟然跳跃着这样一个精灵般的女子,她张扬着青春的气息,行走在田埂村间。
她,曾经是一个个性洒脱、追求自由恋爱的女子。一双洁净无尘的白球鞋,一身无烟酒气的着装,一个工作于省城的男子,那双发白的球鞋,竟是她迷恋的缘由。为着这个,仅仅1900元的彩礼,她心甘情愿地嫁给了爱情,成为了人妻。
她,一直是一个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女子。青春的激荡回归平静的日常,洗衣做饭耕地顾家,她都能做到有条不紊;家庭锁细各种苦楚,她也会默默忍受。为了我们姐弟的吃穿用度,她干过小卖部,放过流行的录像带,为了照顾读高中的我周末省却奔波的路程,吃上一口家里的饭菜,她进城开过小饭馆,卖过麻辣烫……生活将她带进柴米油盐,渐渐抹拭了她的青春浪漫,却锻造了一个刚毅的母亲。
二十一世纪风卷云涌。在这个时代的浪潮中,她是一个看不见身影的中年妇女,但在生活下她又格外显眼。随着小外孙的出生,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她成了看护大军的一员。精致的烫发凌乱了,做护理的时间几乎被遗忘了,洗衣做饭,看护喂养,事事她都安置得妥妥当当。新生,满月,一岁,两岁,三岁……三年之间,一双手,两个家,上上下下,忙里忙外,一切井然有序。
她还是她,但又不是从前的她。岁月在她身上烙下了印痕,她不似往昔那样神采奕奕,面上有了倦容,身上也有了些毛病,但依旧用不甚宽阔的臂膀,给予子女最厚实的依靠!
半世间,一个普通的女人,从少女到母亲,演绎各种角色,穿梭于生活间,无怨无悔!
她,只是万千平凡母亲中的一人,却是带给我生命、为我奉献了一生的最了不起的女人!
以守候时光为题的作文【二】
老屋不老,只因其外形而称为老,八十四个春秋不仅使得她白发苍苍,也在她的心头刻上了历史的沧桑。
女人老了,开始自责自己再也不能劳动,自己成了累赘,可女人似乎忘了,就是在这老屋里,她曾养育了一个又一个儿女。
在这老屋里,曾有五个小儿女呱呱坠地。而这几个小生命都是在女人的爱抚下成长的。那时的女人很很忙,奔前跑后,可她不知疲倦,她快乐于这种工作。
儿女长大了,外出了,成家了,房子空了,女人也老了,女人认为自己不中用了,直到小儿子把这两个宝贝孩子送到老屋。
老屋又热闹了,孙子、孙女的欢声笑语一度填满了老屋的空虚,也年轻了女人的心。可是,在女人疲倦之前,孙子、孙女又要外出求学了。女人虽然不舍得,可还是乐呵呵地将要用的瓶瓶罐罐装进孩子的包里。之后,女人有些落寞了。
也许是岁月捉弄人,也许命运根本就是这样,离去的孩子带走了老人的欢欣,寂寞的心灵开始像孩子一样期盼着被关爱,女人终于开始承认自己老了,她的心只有在孩子回家看望她时才会苏醒。
老屋要拆迁,可女人不准,她说要它陪伴自己走完一生,她不接受儿女的请求,她不愿离开老屋,因为老屋曾陪伴她走过大半辈子。
可后来,女人同意搬家了,原因是孙女的话。
女人一直都在埋怨自己一辈子毫无功绩,除了拉扯大几个孩子,其余的都不沾边。可孙女却说: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作用。女人的一生都在为孩子奔波,这是女人的功绩,这是她的价值,女人做到了。一生的忙碌让自己的孩子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她的梦想实现了,现在是她安享晚年的时候了。
也许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老屋并没有拆,女人则有儿女相伴。女人是我的奶奶,这个劳碌一生的人现在可以安详地欢度晚年了。她总是对我说:“人活一次不容易,要不断努力拼搏,适当的休息也只是为了更好的努力。”
别让心跳乱了节奏,而让生活变得不自由,愿所有人努力生活,一起去解开萦绕心头的寂寞。有始有终奋斗拼搏,准备就绪进入下一个世纪。
生无所息,创造生活;生有所息,只为更好地生活。我会努力,实现老屋里那个女人的梦。
以守候时光为题的作文【三】
昨天在上网络面授课的时候,老师突然夸了我说:“你数学是学霸,也非常棒,朗诵也特厉害,会弹吉他还是乐队主唱,看来你的学习氛围很好嘛。”我听完特开心的笑了笑。但是,下一秒,眼泪就流出来了。
还记得小时候的我,很叛逆,特别野,不管妈妈说的什么话都不想听,草草敷衍了事儿。只有天快黑的时候回家,剩下的时候都是和我的好哥们儿在一起玩。那会儿学习还特别差,尤其是数学,每次一考就是不及格,我爸还看了看我的数学卷对我说:“我的理科排全县第三,怎么到你这儿一点儿也没显现出我的基因啊!”我倒也不理他,自己找同学玩去了。
就这样在小学混了五年。
20xx年12月25日姐姐接到了父母的电话。妈妈说他们昨天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发生了车祸,现在还在医院,爸爸正在拍片子,说明天下午就回去。这通电话是姐姐接的,我并不知道。等我回家的时候听见姐姐正在给同学打电话说父母的情况。我呆住了,时间似乎也都停在了这一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能听见姐姐一直在不停地和同学说,说完就一直哭。我的眼泪止不住嘀嗒嘀嗒的掉落在了地面。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心痛吗?不是。比心痛太还让我难受,我感觉快喘不过气来了。今天明明是圣诞节,昨天明明就是平安夜,怎么会发生车祸?我飞奔到楼下,在大街不停地跑,周围的景物被我抛之在脑后,跑到公园就蹲下来大哭了起来。我嘴里一直在说姐姐说的一定都是骗我的,她骗人。
可是这就是现实。
突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对我说:“姐姐,你在哭什么?你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吗?看,我爸爸在那儿,他带了手机,你要借吗?要是姐姐的爸爸找不到姐姐肯定会很难过的。”我摇了摇头,对她说了声谢谢。朝她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那是一个父亲在给他女儿买棉花糖的场景。
这个场面是那么熟悉,记得那会儿我还拉着爸爸的手舔着大大的棉花糖对他说:“我长大要开个棉花糖的厂子,让没有钱买棉花糖的小朋友都吃上棉花糖,把赚下的钱大部分捐出去,我还要挣很多很多的钱,这样就算爸爸妈妈以后老了,生病了,我还可以支付得起。”我记得爸爸那会儿哭了,他对我说:“我们一起开厂子好不好?”我用很洪亮的声音回答他说:“不可以,爸爸妈妈以后要去很多很多的地方旅游,要是跟我一起办厂子,就不可以去很多很多地方了。”回到车上上我一直看着一言不发的爸爸,我问:“爸爸,你干嘛不说话,是今天琪琪有说错什么惹得爸爸不高兴了吗?”爸爸说:“不是,是因为今天觉得琪琪懂事了很多,很高兴。”现在想想那一次跟爸爸的对话是自己小时候最懂事的`一次了吧。
小朋友跑过去抱住她的爸爸,把手下的棉花糖一下子揪成两半,把那团整齐的给了爸爸,自己吃了那团褶褶的棉花糖。嘴巴鼓鼓囊囊的,可爱极了。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心里释怀了很多。在心里说这就是现实,这并不是最糟糕的结果,还好他们还活着。我们还不是孤儿。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爸爸妈妈在圣诞节的第二天回来了,父亲的腿骨折了,叔叔断了两根肋骨,母亲没什么事儿。
我发现,我渐渐地变了。我变得不再满大街的疯跑,变得不会故意考得不好引他们生气,也变得不会故意找姐姐的茬儿了。
日子总是像从指尖流过的细沙,在不经意间悄然滑落。那些往日的忧愁和悲伤,在似水流年的荡涤下随波轻轻地逝去,而留下的欢乐和笑靥就在记忆深处历久弥新。
时光老人,我很好,谢谢你让我懂得生命的美好。
以守候时光为题的作文【四】
天,依旧蓝蓝的;山,还是那么的葱葱郁郁。泥泞的小路变成了石子路,不光只走人力车了,可以走拖拉机、小车、大点的卡车也可以。
顺着岭上的石子路向前走,就有了一片白杨树,白杨树是前些年栽的,响应号召,退耕还林,大力支持木材事业。近年来,木材厂的生意差了许多,说是速生杨做出来的木板品质差,就滞销了,浑身虫眼的白杨树变成了寂寞的林子。
白杨林的东面有石头彻成的围墙。围墙结实,院墙的钢管大门只剩下一半边,像暖阳下的一个瞌睡老人,懒洋洋地靠在围墙边,或许它知道关与不关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院门正面的一个砖砌的台墩子上长着一棵雪松,是当年学校搬走时留下的,一只癞得没毛的老黄狗伸着舌头躲在树荫下喘着气。这里的主人是后来搬来的,在雪松的后面建起了三间瓦房,瓦房只修了一层却已修了楼梯口,只待日子好些了更上一层楼。
每天太阳从东走到西,经过屋脊,路过窗前,来到门前,门口便有了一小巧的女人,小脸、小手,小脚。“咕咕咕、咕咕咕”正喂着面前的一群鸡,光着屁股的小公鸡刚刚学会吹“魔哨”,却不愿吃食,净追那些老母鸡,瞅准空子便跳到老母鸡的背上,老母鸡红着脸一晃身子,伸头一啄,小公鸡便摔了个跟头,一跳跑了。这个时候,女人便了骂起来,拿起竹竿一晃,小公鸡却飞到了雪松上,仰头便吹了一声“魔哨”,树下的女人恼了,骂着捡起一小石子砸去,一下没中,二下还是没中,三下鸡却飞了。
雪松,那年有人要买,说是到了季节来挖,忽一日没了柴禾,她便拿起柴刀把那枝繁叶茂的分枝全砍了,剩下树稍在风天里摇摇晃晃,好似那小公鸡光屁股上的一根毛。树是没人要了,倒乐坏了那群鸡,夕阳西下,树稍的小公鸡抛着媚眼,仰着血红的鸡冠对着晚霞耀。
天就快黑了,女人早已烧好了晚饭,依在半边门前,等着男人回来,女人最喜欢的是晚上,她知道,男人是带着太阳出去的,晚上带回来的一定是柔情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