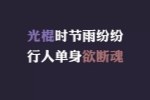挂灯笼的时候作文【一】
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女性主义的情况下,中国近期的电影却鲜少涉及这一主题。中国没有女性主义吗?《七月与安生》还有目前没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甚至《大鱼海棠》都有涉及到女性主义,但是无一例外,这些电影的女性主义视角并不突出。
所以,今晚,我们来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谈部老电影。
《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改编自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
“红灯笼”这一意向贯穿整部电影的始终,可见,其象征意义绝不简单。影片中,每当红灯笼被点亮,被挂起的时候,就意味着有新人要进入这个院子了,意味着有人要得宠了,有人可以点一份自己喜欢的菜了,同时也意味着有人要失宠了。仅仅一个红灯笼,却几乎牵扯了这个死气沉沉的大院中所有女性的神经,此时的它代表着权利,代表着地位,就是不像红灯笼。
红色给人的感觉是热烈,是激情,是情欲。影片中,只有被陈老爷点中的院子才可以点红灯笼,陈老爷的到来意味着性,而红灯笼就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性暗示。在这种暗示下,女人不得不顺从男人,因为男人决定着女人什么时间可以有性,什么条件下才可以有性,女人在这种压抑下渐渐沦为男性的玩物,而在以陈老爷为代表的男性眼中,院中女人确实只是性玩物而已,因此,雁儿活着陈老爷可以明目张胆的占她便宜,雁儿死了陈老爷连见都没见一面。对于男性来讲,薄情是生理决定的。
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就是高高挂起的性,大家心照不宣,却又无人不心知肚明。在这种直指女性的暗示下,女人在这个红灯笼下变得一丝不挂,其自尊也被一点一点燃烧殆尽。红灯笼凭借着男人的特权愈加鲜红,在这种情况下,女人只能“以色事人”,只能“你算计我,我算计你”。性压抑压抑的绝不仅仅是女人的本性,还有女人的尊严、善良。从这个角度看《甄嬛传》,后宫的争斗就更好理解了。
南唐以来,女性的另一苦难就开始了,那就是裹小脚。几千年以来,脚成了另一束缚女性的工具。电影中并没有涉及裹小脚的画面,但没出现就意味着男性不再关注女性的脚了吗?当然不是。
颂莲刚刚入府,迎接她的不是老爷,而是捶脚。捶脚那在陈府可不是小事,在他们的规矩里,脚要被精心缝制的红绸子盖好,就像盖着红盖头的新娘,外人可是不可以看见的。捶脚有专门的人服侍,有特制的工具,它会发出急急令般的声音,整个院子的\'人都听得见,可见其待遇级别之高了吧。所以,就连受过新式教育的颂莲也被其俘获了,为了捶脚,她绞尽脑汁,耍尽手段。在某些情况下,人性的恶显露无疑。可悲,可叹。而回想颂莲刚入府时,陈老爷是怎么给她解释捶脚的,他说:“女人的脚捶好了,才能伺候人。”哈,原来还是脚。
当女人的脚被一层一层裹上,女人行走甚至站立的权力就已经被剥夺了,一个不能站不能走的女人除了依附男人还有别的选择吗?而当影片中的女人越来越依赖于捶脚时,其命运也在那一声声急急令般的捶脚声中越来越无法被自己控制。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波伏娃的话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电影唯有比生活更真实,才会更有力量。
挂灯笼的时候作文【二】
苏童的《妻妾成群》读了好几遍,也一次又一次地听说《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名字,但是始终没有看,担心会失望。一个故事,凡是在文字和影像两种形式上进行转换,一向很容易叫人失望。
电影与小说存在较大差别,故事背景从江南水乡迁至西北内陆,少了濡湿的气息,多了北方的干冷,情感表达更为直白激烈,戏剧效果也更为明显。
点灯,吹灯,锤脚,泛着冷光的蓝瓦,层层叠叠的屋檐,不露天空的高墙,即使是没有对白,甚至没有人物,却一遍又一遍重复着的镜头,也能令人感受到其背后的情感。
挂灯笼的时候作文【三】
整部电影所展现的全景永远都给人一种对称的形式感,烘托了剧情本身所要表达的封建礼教对人心的禁锢。由此也可以看出张艺谋导演早期作品的严谨性,一种纯粹的表达,不惨杂多余的东西。
站在对该片感性化的分析角度,音乐是一大特色。浓厚的北方民间音乐与传统京剧相结合。无论是陈家大少爷的笛子所表现的苍凉,三太太京剧的洒脱与绝望,还是迎娶颂莲的那段欢快的曲调都给人一种化外有话的延伸感。这种延伸感也将画面烘托出压抑和讽刺两种色调。当三太太被封建礼教所迫害时,大雪漫天,颂莲闻声前去打探。一路上慢是怀疑和害怕,当她快要靠近“死人屋”时的那段音乐表现出的情绪足以让人感到窒息。片子结尾处,颂莲围着自己的院子不停地打转,给了这部电影不言而喻的含义,封建礼教是外延,而主题和内延是人心。人心就像一个没有出口的四合院,禁锢自己也***死了自己。曲调的循环往复给画面注入了时空感,将观众带入一种永无止尽的绝望当中,特别是女性观众,似乎一时还找不到精神上的解脱。这便是电影的深刻之处。
影色调纯粹明快,并随着春夏秋冬四个阶段和主角的情绪变化而转变,冷色调居多。鲜明得衬托出了大红灯笼病态的艳丽,和周围环境形成强烈的对比。看似喜庆,实际上是男权压迫的象征。此片反应了旧时代的中国特别是北方地区,男尊女卑的普遍现象,女性过着玩偶般的悲惨生活,无论学识的高低似乎都会在婚姻这门考题上"挂科",上对地位的极度渴望,导致的后果就是玩火自焚。男人本身是一个衬托,陈老爷也是从头到尾没露过脸。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在男权社会的背后,她们才是舞台上的主角,扮演各种个样的角色,正如何赛飞说的那段台词,戏演的再好也骗不了自己。然而可以说这是一个无法逾越和解决的社会现象,只有艺术这种表达形式才能正确深刻得反应它。1990年代初,该片曾在国内禁映过一段时间。这说明那时候的中国尚处在过度时期,还未真正意识到这种社会现象的严重性。
挂灯笼的时候作文【四】
一个女人,锁在一个深宅大院里,没有自由,没有爱情,没有安慰,靠什么活下去呢?
颂莲,在那个时代里,已经算作一个勇敢强悍的女人,在她的身上有一种很硬的东西,这种茂盛的生命力在巩俐一开始倔强的眼神里就显露无疑。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她如何能赢过残酷无稽的生活?
她也曾在书本里想象一个光明的不一样的未来吧,她也曾想过自己主宰生活吧,她也曾有过爱情吧,可这一切在命运面前都成了一个笑话。我说命运,是因为我不相信命运,因为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东西强大到可以承担起这份罪过。
她藏了一支笛子在箱底,拿起笛子的时候,颂莲的脸上满是忧伤的快乐。在大红灯笼也照不亮的黑暗里,总需要一点光亮来照见心里那仅剩的一点温情。可是,即使是这卑微的安慰,她也无法拥有。老爷一把火就把笛子烧了,颂莲无言,落泪……
颂莲是倔强的骄傲的不服输的,而很多时候,我都几乎把巩俐和颂莲重叠。电影没有对颂莲的过去做任何的交代,只是说,“我上了半年大学……”但一切都写在颂莲那冰冷而倔强的脸上。我喜欢这样的女人,生活给了你沉重的一击,你狠狠的瞪回去,抬起头继续生活,不认命,就是不认命。
爱情,颂莲也曾寻找过吧,那一声“飞蒲”,渴望写满脸上,那个时候如果飞蒲给她一个拥抱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那么她也不会一无所有了。20岁的生日,一个人酒醉。这是何等的凄凉,对于一个美丽的女人来说。其实,我一直在想,飞蒲的那个“谎言”,并不是谎言吧。或许他本想给颂莲一些真的温暖?如果不是意义深重,如何又能那么轻易的送出呢?最后,颂莲在屋内闹酒,飞蒲在大口往里张望,然后转身离开。我们其实都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有一个勇敢的男主角的。
颂莲无意真正伤害谁,可是两个女人都因她而死。生活在这里显得多么黑色幽默。
电影始终没有给老爷一个正面的镜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造成了颂莲,雁儿还有三太太的悲剧,但其实仔细想想,这与他又何干呢?他不过是一个 把女人当衣裳当玩物当工具的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普通男人罢了,就像《莫高窟》里的王道士一样,他太卑微,如果硬是把这种时代的罪恶安放在他的身上,只会觉得可笑。
“老爷”只是一个背景,提供一个争抢的缘由。说到争抢,我问自己,如果我是颂莲的话,会怎么样?我想,我会和颂莲一样,争宠。这和被争的宠无关,和虚荣嫉妒无关,只和自尊相关。人,总需要一点生活的意义吧,总需要那么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吧。不甘心被冷落,不甘心被打败,所以,那些妻妻妾妾们的勾心斗角争风吃醋也就能够理解了。只是,这何尝又不是另一个悲剧呢?
再说说里面的人,二太太一开始笑的那么菩萨,连我都被她骗了,只是心里住着一群群的蛇蝎。女人啊女人,实在是一种可怕的动物。笑里藏刀口蜜腹剑,这样的女人,菩萨保佑,千万不要让她们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表面嚣张跋扈的三太太对颂莲说“我知道我不是她的对手,我想,或许你可以和她斗一斗?”而笑到最后的二太太,难道真的是最后的胜利者?三太太如愿以偿的死了,年轻貌美的四太太疯了。可是,她忘了,就算漂亮的三太太死了,年轻的四太太疯了,还会有更年轻的五太太更漂亮的六太太进门来,在命运面前,在生活面前,到底谁能赢呢?
而三太太呢,美丽的戏子,她在角楼上对颂莲说,“谁不是在做戏呢?做的好的就骗别人,做的再差些就骗骗自己,再不好就只能骗鬼了。”她有美丽的嗓子和身段,曾经它或许还做过美丽的梦吧。但在日复一日的勾心斗角中也早已习惯“像猫像狗就是不像人的生活了’,最后她因何高医生的奸情而被吊死在死人屋里……其实我是高兴她和高医生在一起的,高墙大院里,寂寞女人的温情总得找个出口吧。至少,这也能给死气沉沉的生活一点新鲜的色彩。
还有雁儿,固执的做着太太的梦。这并不是一个让人讨厌的角色,其实,她的那些心眼那些冷漠倒让我有些凄凉的同情。我不相信她是真的爱什么老爷,她只是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试图和命运抗争一下?在这一点上,她和颂莲没有任何区别。跪在那堆红灯笼烧成的灰烬前面,雪地里的雁儿,让我感动。
雪,那么安静,院子里安静的有些阴森。那些黑瓦和翘起的屋角,曾经埋葬了多少人的青春和梦想啊,不过那个时代,又有几个知道青春梦想这回事呢。在最后悲凉的乐声里,我想起大太太初见颂莲时的两个字,“罪过”。罪过,这两个字给全片下了注脚。这一切到底是谁的罪?谁的过?是那个“吃人的旧社会”吗?是男尊女卑的烂思想吗?
到如今,我们再也不用被逼着给别人去当姨太太了,我们可以念书,可以自己选择爱情,可以和男人平等相处,但是,为什么还是觉得不幸福呢?为什么悲剧依然时时发生呢?我不知道。
或许我们同样是被时代被自己被我们生而为人的这个基本事实绑架了。
我们嫁给的“老爷”就是是那些我们标榜的社会现实,物质需求,肩负的各种责任,还有那个叫做个人梦想的东西。在我们美好的年华里,我们被许给了这些东西从此,便与那些一样把自己卖给现实的“姨太太们”明争暗斗……
我们都是一群姨太太,在生活面前。
挂灯笼的时候作文【五】
影片没有选择原著陈佐千老爷的大花园,于是没有绵绵的潮湿的雨,没有花和树,没有知更鸟,随着颂莲的脚步,我们一起走进的是青砖灰瓦的山西大院,四周都是高墙,镜头里始终见不到大片的天空,只在高墙之上,镜头的最边缘露出阴暗的一段来。影片也有更多的镜头展现院子的全貌,四方的,合拢的,是一座囚笼,有形无形中给人以逼咎和压迫之感。影片中大院全景镜头下,女人瘦弱的身影化作一点,竟是如此渺小与无力,于是,给人不可抗拒的宿命感。
踏过了封建家族高高的门槛,观众就和颂莲一样,再也出不去了,囚禁在冷色的砖瓦夹缝里,被锁在这阴森的深宅大院,即使踏上这座院子的最高处,也始终越不过那道院墙。
与冷色的院子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电影最典型的意象之一,红灯笼。屋檐下,桌旁,床上的天花板,红灯笼把屋子里照得亮堂堂的,那么喜庆。一盏盏的红灯笼,在大院的屋檐下堂堂正正地照耀着,散发着一团团热烈的光,增强了仪式感。这座大院需要红灯笼,夜晚才看上去没有那么可怕,然而,红灯笼高高挂起的时候,在全景的镜头中,深蓝的院落背景衬着正统的红色,却显得更加鬼魅了。
实在很难想象,一个封建家族的老爷采用皇帝对后宫三千佳丽的类似“翻牌子”的规则。甚至,这套规则还包含了点灯,锤脚,点菜等一系列具体规则。可以说,影片以一种艺术化的表达手法,将封建社会的风貌投射在陈家大院上。
红灯笼是这座封建大院的制度的象征之一。
颂莲在第一天入陈府的时候,为“点灯”的规矩而深感不习惯,窝在被子里说,“把灯关了”。后来,却也成为这深宅大院中为“大红灯笼”的明争暗斗的女人们之中的一个。想要在这座深锁的大院立足,就需要那盏明亮的火,那是束缚,也是渴望,是在这种被他人所操控的规则下的一种生存法则。
作为大院最底层的女人,雁儿的屋子里的红灯笼就是她赤裸的渴望。满屋子都被映得通红,红光照在人脸上,却更显现人脸色的苍白。与太太们被点灯的权利相比,她根本没有权利将渴望曝露。
可以被点灯,也就可以被封灯。作为太太,大院里的女人们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灯笼的命运就是她们的命运,被点亮,就成为陈家老爷床上的工具,生活的附庸;被熄灭,就沉寂,就千方百计又小心翼翼地去争取一点立足的希望;被封灯,就永久地死寂在阴森的大院里了。
颂莲被封灯之后,整间屋子都萧索了。那些青黑的袋子,像是一座座红灯笼的墓碑,在它们本来的位置,代替了它们,像是陈家大院里压抑的灵魂。
被封灯之后,颂莲的衣服颜色也发生了变化,多为青黑。影片中,颂莲的衣服颜色共发生两次变化。未入陈府时,白衣黑裙,是读过一年书的女学生装扮,入陈家之后换下了学生装束,穿上的依旧是一袭白衣。在得宠之后换上的皆是红色的华服,颇为浓丽。待到失宠后,则换上了青黑色的长衫裙,在封灯的四院里格外死气沉沉。
颂莲也曾一度从箱子里拿出那套学生时代的衣服,但是,它永远地属于过去,再也回不去了,只能和倔强的灵魂一样,锁进行李箱里,总好过,那只一把火烧了的笛子。
不过,在这院子里,没有灵魂,无力掌控命运的人,到底算什么呢。
人,到底,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