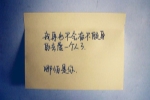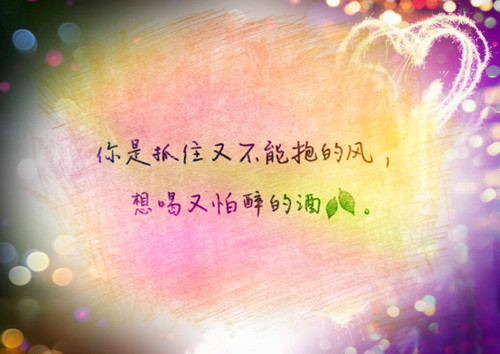
带有梅花启示的作文结尾【一】
童年有许许多多的回忆,但是有一件事,让我至今无法忘怀。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天气,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打棒球。来到场地我们分好了位置,开始了欢快的击球。刚刚开始大家玩的都很开心,可是到了我做击球手的那一球,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我的一个好朋友,将球抛给了我,而我也是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尽力将球给击打了出去,只见棒球划出了一个高高的弧线,正中一个同学的鼻梁。瞬时,鲜血从他的鼻子中流了下了。
那一瞬间我们都害怕了,我的脑子也是一片空白。而后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快跑,我们几个撒腿就跑掉了。回到家中,我慢慢地冷静了下来,决定去向同学道歉。来到同学的家中,我看到刚刚从医院回来的他,我赶快走了过去,对他说:“对不起,刚刚是我的不好,没有看到你咋那个位置,我也不该逃跑的”。同学笑了笑,安慰我说没关系。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最后还是在同学的劝解下回到了家中。
这件事过去了好久了,我还是很难忘记,以后如果遇上这种事情,我一定会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不会再逃避了。
带有梅花启示的作文结尾【二】
顾子砚去西苑那日清晨,落了一场薄雪。天色阴沉,唯有积雪映出稀薄的光。风有些大,他紧了紧领口,便突然记起了沐之湄。
他记得沐之湄是顶不喜欢下雪的。那时候他们感情正好,夫妻恩爱,相敬如宾,也算是这帝京里的佳话。每逢下雪天,她就窝在他怀里撒娇,磨得他没了半分出去的兴致。沐之湄同他提过缘由的,她说娘亲过世的那日,便是个雪天。
他恍惚想着,停下步子时方察觉已经到了西苑。顾子砚叹了口气,摒退了宫人,一个人推开了宫门。
西苑已经废置许久,纵是而今住了人,院子里也是杂草横生。一层薄雪覆着,连个脚印也没有。唯有院子左边的那株梅花,被主人打理得很用心。顾子砚叹了口气,轻不可闻。
殿内传出剧烈的咳嗽声,顾子砚几乎是控制不住步子走进殿内的,待看清殿内景象,倏然顿了呼吸。
装水的瓷碗碎成几片,沐之湄躺在床上呼吸急促,却紧闭着双眸,呜咽着哭泣。
顾子砚知道她是害怕的。沐之湄素来心肠恶毒,不怕人只怕鬼。那天他下旨的时候还同她说:“皇后不是素来怕鬼吗?那便关去西苑吧。”西苑闹鬼的事情,皇宫里人尽皆知。他很满意地看到沐之湄苍白了脸。
他一直觉得,他是恨沐之湄的。他的姊妹兄弟,多数折在这个女人手里。甚至于他未过门的妻子,也被她害死。
顾子砚没能想下去,沐之湄咳嗽得厉害。他走到床边,才发现她脸颊酡红,应是害了病。
似乎梦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沐之湄于梦里也不安稳,艰难地张开嘴,发出痛苦的声音,尔后轻轻唤了声“阿砚”。顾子砚听得分明,心下微颤,又听她继续道:“你别不要我。”
顾子砚锁了眉头。几日不见,沐之湄削瘦得厉害,原本饱满的脸颊也陷了下去。他伸出手想要抱抱她,可伸至一半又僵住。他们之间已隔了太多东西,多得他连抱抱她都不能够。
那句话沐之湄从前也同他说过。顾子砚记得,那是在他们大婚之夜,他挑起沐之湄的鸳鸯盖头,便看到她盈盈笑着的眉眼,嗔着语气同他说:“夫君,你可不能不要阿湄啊。”当时他握紧她的手,说了声:“好。”
他是真想着要同她一生一世的,可是被她亲手破坏了。
雪花落在地上静寂无声,映着窗边那株红梅愈发好看。顾子砚抱起沐之湄出了西苑,吩咐外面的宫人去传太医。
他终究舍不得她死。哪怕他恨她,他也希望她活在这世上他知道的一个地方。
顾子砚皱紧了眉头,将沐之湄放在未央宫内的软榻上后,转身出去。未看到身后的沐之湄缓缓睁开了眼,脸上的笑容苍白凄艳。
她看着未央宫内的器具摆设,忍不住悲哀地想:阿砚,我们之间,怎么就总是欺骗。
从初始到后来,她同顾子砚之间,从来没能少了谎言。
太医离开不久沐之湄便睁了眼,顾子砚捧着一卷书坐在床边,只是看着她,未发一言。
沐之湄也不说话,歪着脑袋看他。顾子砚样貌生得好,身上一股子书卷气,举手投足间意气风发。从前还在东宫时,他们也常如此。顾子砚习惯早起,她每每醒来时总能看到他专注的样子。
她总是看不够的。当年丞相府里惊鸿一瞥,她就已经把自己输得干干净净。
顾子砚伸手抚着她颊边乱发,阖上了眼睛:“阿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告诉我,那些事情究竟是不是你做的?”
沐之湄仍是看着他,半晌翻过身子背对着他:“你不是都知道了吗,是我做的。可是他们,他们……”
顾子砚忽然笑了:“沐之湄,你怎么这样恶毒?”
沐之湄张张嘴,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顾子砚摔门离开,沐之湄盯着帐顶,恍恍惚惚睡去。
前尘种种入梦来,她睡得不大安稳,迷迷糊糊梦到她初入东宫的时候。那是她这一辈子,为数不多的想要永远记住的时光。
淳化二十五年三月初三,京都的桃花开得格外好,她穿着大红喜服,忐忑地坐在花轿里,手里的喜帕被捏得皱皱巴巴。她方及笄,就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却是以姐姐的身份。
当朝太子同丞相府嫡女大婚,十里红绸挂满长街,若非姐姐生了急病,是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她的。
她这一生,生于富贵却未能长于富贵。妾室所出,母亲早逝。她的日子同府里下人无二,甚至还常常被下人欺负。有朝一日能嫁给当朝太子,她连想都不曾想过。
两年前她见过顾子砚,在丞相府的后花园。彼时也是三月,长姐走在他身侧,不知同他说了什么,逗得他温软了眉眼。当时她便想,怎么会有人生得这样好看?尔后,她便做了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她跪在陆贵妃面前,目光灼灼:“民女愿誓死追随太子。”
陆贵妃当时捏紧她的脖子问她:“若是要你的命呢?”
她睁大眸子:“我给。”
往后的两年里,她远离京都,在陆贵妃的安排下做了隐居山林的前丞相大人的关门弟子,日日读书习字。她常常想起顾子砚的样子,那人在梦里照例温软了眉眼朝她笑,她恍惚觉得,如此甚好。
两年后陆贵妃发来密函,说是皇帝赐婚太子同沐清湄,要她回去,取而代之。
沐之湄怔了许久,拿起密函细细又读一遍,才敢确定,她要做顾子砚的妻子了。纵然顾子砚不喜欢她,她也是不大在意的,只要陪在顾子砚身边的,是她沐之湄就好了。
拜堂的时候沐之湄在盖头之下几乎哭出声,她看不见顾子砚的样子,可她想,她离顾子砚这样子近,近得几乎触手可及。
夜里顾子砚掀开盖头的时候,沐之湄甚至是有些惊惶的,她颤着声音说:“夫君,你可不能不要阿湄啊。”
顾子砚看她良久,把她揽在怀里,轻轻说了声“好”。
他是真的待她好。
沐之湄幼时受了苛待,身体一直不好,那一日半夜突然犯了腹痛,往常都是硬挺过去的。可那一日不知为何,疼得厉害,她忍不住出了声,吵醒了顾子砚。
顾子砚看着她的脸色皱了眉头,喊人传太医、上热汤忙得不可开交,熬好了药又亲自喂她。等到吃完了药,又帮她揉着肚子。沐之湄半扬着脸:“夫君,你待我真好。”
过世的娘亲她已经记不大清楚,那这世上待她最好的,便是顾子砚了。
再醒来时已是第二日正午,废皇后被皇上从冷宫里亲自抱出来的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前朝后宫里引起轩然大波,沐之湄不知道,而顾子砚,似是不大在意。
沐之湄挣扎着身子坐起来,发现身上的衣服已被换成新的里衣,有些宽大,应是顾子砚的。未央宫里烧着地热,她赤脚踏在地上也不觉着冷。倒是顾子砚听见动静,快步跑了过来,皱着眉头将她拦腰抱起,轻声斥责:“胡闹些什么?”
沐之湄看着顾子砚的眼睛,极缓慢地伸手揽住了他的脖子。顾子砚僵了身子,终究没有推开她。
他们许久未能这样亲近,两个人之间,生生隔了血海深仇。顾子砚一直知道生在皇家,许多事情都身不由己,也难能像平常百姓家里,兄友弟恭。可那总是他的手足啊,一个一个都被他爱的人***死。每每他问起,沐之湄总是看着他,明明都要哭出来,却还是不肯说一个字。他甚至偶尔骗自己,沐之湄是有苦衷的。可他骗不过啊。
他最小的弟弟顾子清,过世的时候只有十三岁。
那时他已经登上皇位,父皇子息本就单薄,兄弟姊妹一共不过六个。到了天光元年,只剩下了他和子清。
顾子砚幼时便被封为太子,同弟兄们其实不大亲近,唯有子清黏他,得了好东西也总记得过来送他一些。他受了父皇责罚在未央宫外长跪的`时候,也只有他的小弟弟去哭着恳求父皇。因而顾子砚继承大典之后,对子清,格外厚待。
只是沐之湄啊,连他的幼弟也不肯放过。
顾子砚记得那日也下了雪,他正在宫里批折子,听得宫外一阵吵嚷。推了门出去,便见伺候子清的太监扑通跪在他面前:“皇上,小王爷……小王爷他……去了。”
这消息太突然,以至于他一时之间竟不知做何反应,他的幼弟子清毫无征兆地,去了。
他几乎是疾奔过去的。冬日天冷,虽然宫中供暖得当,待他赶到清风殿的时候,子清的身子已经凉透。
太医跪在他面前战战兢兢,说子清是中了毒,毒性太猛,太医甚至都来不及施针。那太监说,王爷今日,只吃了皇后送来的糕点。
站在沐之湄面前的时候顾子砚有些失神,沐之湄踮着脚尖拂去他发上的雪花,嗔怪道:“怎么这会儿来了?”
他捏着沐之湄的手腕倏然用力道:“是你***了子清吗?沐之湄!”
沐之湄脸色骤变,忽然又笑了:“阿砚,你心里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不待顾子砚接话,又接着道,“是我做的。顾子砚,祥王、睿王、永乐公主、永夜公主都是我***的,我也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应该是沐清湄,我的长姐。可是我想嫁给你啊,我想做皇后,所以,我把她也***了。”
她说着说着突然就哭出了声:“阿砚,我从来没有想骗你,只要你来问我,我都告诉你。”
一年前父皇病重,顾子砚常在未央宫伺候,连东宫也不常回。只记得那年他失去了许多亲人,却没有想到,罪魁祸首,竟是他的枕边人。
顾子砚想,他这辈子,最爱的人不过沐之湄,最恨的人亦不过沐之湄。
他看着沐之湄看了很久,蜡烛泪尽,晨光熹微。他方开了口:“带皇后,去西苑吧。”
他终究,舍不得***她。
沐之湄在他耳边幽幽开了口:“阿砚,你恨我吗?”
顾子砚拥着她单薄的身子,心里涩得发疼发胀。他想说他是爱她的,可他张了张嘴,终究发不出声。
两个人分明拥着彼此,却又好像,隔了亘古光年。
沐之湄便在未央宫里住下,顾子砚那日终究没能回答她。两个人似是突然之间有了默契,都不再提。每日夜里相拥而眠,像在东宫时一样。
第五日清晨,陆太后宫里来了人。
顾子砚去上早朝,沐之湄正倚着软塌看书,那人恭敬跪下:“听闻娘娘又得了宠,太后差小的来请娘娘过去一叙。”
沐之湄闻言,右手轻颤:“我知道了,稍后便去。”
未央宫距离太后所居宁乐宫其实并不算远,沐之湄却觉得,每一步走下去,都分外艰难。雪后的风景其实很不错,积雪压着树枝,仿若一夜之间,梨花陡开。沐之湄未乘凤轿,地上未清干净的积雪化成水濡进鞋里,沐之湄并不在意,她只是觉得,她同顾子砚之间,好不容易缓和的关系,恐怕要结束了。
沐之湄屈膝跪下,竭力平复着心情:“参见太后。”
陆太后端着仪态坐在凤椅上,并不叫她起来:“皇后多久没来过哀家这儿了?”
“太后说笑了,年前皇上已经废了奴婢。”
陆太后起身下来,停在沐之湄面前:“记得便好,哀家还以为,你这两天得了皇上宠爱,都忘干净了呢。”
沐之湄不答话,顿了些许忽然直起腰身,对着太后行了个大礼,叩首道:“太后,从我跟着您那年,到现在,已经六年了。”
“是啊,已经六年了。”陆太后忽而轻轻叹了口气,“这六年里,你一直做得很好,可是,你不能忘了当日你说过的话。子砚,他是一国之君。”
沐之湄终是没能忍住,大滴眼泪落在地上。她怎么能忘了,阿砚是帝王。他有他的家国天下,有他的黎民百姓。可是她也记得啊,她只有顾子砚了。她只有,偷来的顾子砚了。
太后又开了口:“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了,往后哀家都不会再要你做什么了。这一次之后,哀家同你的约定,也结束了。”
沐之湄怔愣着抬头,太后又道:“你***了哀家吧。”
沐之湄瞪大眼睛摇头:“不行的,不行的……”
“陆家如今势力大了,有人心野了。哀家如今老了,治不了他们。子砚是个好皇帝,可败在心慈手软。哀家舍不得儿子,可也舍不得母家,若是哀家死了,我哥哥定然不敢轻举妄动。便是出了乱子,哀家也看不见了。哀家有些怕疼,你的刀子,记得快些。”
那一年,太后也是这样同她讲的。沐之湄记得那天是个大晴天,荷花池中红莲白莲争相斗艳,陆贵妃倚着栏杆皱紧眉头:“现下皇上病重,京中势力难以控制。子砚心软,可这宫中虎狼之地,哪里容得他手软!他既然狠不下心,只能你来替他狠心了。”
她跪在荷花池边,身上出的冷汗把衫子都打湿了。良久,她叩了头,声音轻而坚定:“好。”
太后把一把镶了宝石的贵重匕首塞进她的手里,朝她微笑:“沐之湄,我不能容忍我的儿子有任何危险,沐丞相虽然败落,可难保以后。子砚喜欢你,是对他最大的威胁,我的儿子,要活到寿终正寝。”
话音未落,便撞上了匕首。沐之湄尖叫一声,突然扔下匕首,蹲下身子抱着脑袋瑟瑟发抖,口里喃喃道:“阿砚会讨厌我的,阿砚会恨我的。”
顾子砚得到消息赶来宁乐宫时,陆太后的尸身已被简单清理过了。沐之湄仍蹲在原地抖着身子,衣服上沾了血。顾子砚疾奔过去抓住陆太后的手,哑着嗓子喊了声“母后”,半晌才颤着手为陆太后阖了眼。
然后起身,走到沐之湄面前,反手一个耳光打得沐之湄跌坐在地:“我怎么能忘了,你沐之湄向来心肠狠毒啊,***了我的姊妹弟兄,又***了我母后,下一个,就轮到我了吗?”
“你回去西苑吧,往后,朕再也不想见你。”短短的一句话,费尽了他所有的力气。
沐之湄被宫人拖着往西苑去,不吵不闹。顾子砚看她离开,终于脱力一般跌在了地上。这天下之大,他的血亲,一个也没有了。他爱的人,怎么狠得下心伤他至此啊。
西苑自闹鬼之后,已有二十多年无人造访。沐之湄不过几个月,却来了两次。头一次,因她***了顾子清,顾子砚废了她的后位;这一次,因她***了陆太后,顾子砚再也不想见到她。
夜风从破败的窗户里灌入,吹得沐之湄一个激灵。天色已经黑透,西苑里却连根蜡烛都没有。她以为在西苑的三个月里,她已经习惯。可是顾子砚把她接走,又把她扔了回来。她怕得要哭,她想抱抱顾子砚,哪怕顾子砚对她不好,打她骂她,她都愿意。可是啊,顾子砚再也不会来了。
她突然觉得有些悲哀,顾子砚知道她怕鬼,却不知道,她为何怕鬼。顾子砚不知道,她沐之湄怕鬼是因为***孽太重,***孽太重是为了他能活着。
当年沐之湄得了陆贵妃的旨意,却并没有轻举妄动。她不算是个坏人,便是当初在丞相府里受尽侮辱,她也从没想过要***了谁。
直到那次顾子砚自苏州回来,在路上遇到刺客,九死一生。沐之湄看着浑身是血的顾子砚才终于明白,若不***人,便只有被***。
那个夜里顾子砚一直昏迷,她在床边一遍一遍帮他擦去身上渗出的血。太医说顾子砚伤得太重,若是熬不过今晚,恐怕凶险。沐之湄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害怕过,她看着顾子砚,连眼睛都不敢眨。唯恐一眨眼的工夫,就和顾子砚天人永隔。
所幸后半夜的时候,顾子砚睁了眼,哑着嗓子喊了声“阿湄”,沐之湄看着他苍白的脸颊便落了泪。她想,她不能让顾子砚死,就算她百年之后堕入十八层地狱,她也要护得顾子砚一生安稳。
沐之湄***的第一个人,是祥王顾子苓。陆贵妃后来说过,刺***顾子砚的人使的是江州杜家的暗器,而杜家素来同祥王交好。
跟着师父的那两年里,她学过***人。可她没想过,有朝一日,能用手里的武器保护顾子砚。剑尖指着顾子苓喉咙的时候,她想,阿砚,我能保护你了。
凡事起了头往后总归不难,再有伤及顾子砚的人,她一个都没放过。
而顾子清,她本不想***的。那是顾子砚最疼爱的幼弟,她怎会不知道。可是,顾子砚不知道,他最小的弟弟,***了他未出世的孩子。
那时候顾子砚初登帝位,江南水涝,灾情严重,不得已下江南视察。顾子清一直住在皇宫里,年纪不大的孩子,没事便喜欢瞎跑。沐之湄没有弟弟,同姐姐也不大亲厚,因而对顾子清也十分疼爱。那日顾子清离开后,沐之湄便觉得腹痛难忍,她初始不大在意,以为又犯了老毛病,可是过来的侍女突然一声尖叫,沐之湄低头一看,衣服下摆都染了血。
那是她同顾子砚的第一个孩子,在她还不知道他存在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她。太医看着她,几度欲言又止。等得陆太后来时才开了口:“娘娘身子不好,摄取麝香的量又太大,往后,往后怕是再不能有孕了。”
沐之湄怔了半晌都没能反应过来。她再也不能当娘了?她再也不能有顾子砚的孩子了?
陆太后带来的人从她的长乐宫里搜罗出不少含有麝香的东西,且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顾子清。
陆太后说:“看到了吗,这就是皇宫,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善类。”
这件事,她没有告诉顾子砚。
那日沐之湄去了清风殿,把带来的糕点一样一样摆在了顾子清面前,她笑着问顾子清:“你知道嫂嫂今日来做什么吗?”
清俊的少年扬着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她:“皇嫂是来找我讨债的,我***了皇嫂的孩子,所以,皇嫂来***我。”
沐之湄又问:“你怎么狠得下心呢?他还那么小。”
顾子清笑得流了泪:“那皇嫂***我哥哥姐姐的时候,怎么狠得下心呢?就算我不动手,嫂嫂你会放过我吗?”
沐之湄一怔,顾子清已将那糕点咽进了肚里,看着沐之湄道:“皇嫂,对不起。”
沐之湄起身,摇摇晃晃地出了清风殿。夕阳西下,染得云霞血似的嫣红,沐之湄安静地闭上了眼。
六月荷花开的时候,皇宫里传出了顾子砚新封的梅嫔有孕的消息。沐之湄听送饭的公公提起,手下一松,碗碟掉在地上,碎成几片。
那公公叫得阴阳怪气:“哎哟,您这是干吗呢,摔了碗碟皇上也记不得您了。”
沐之湄不语,拿着一个碎片走到左窗下的那棵梅树下,恨恨地划在了树干上。耳边恍恍惚惚想起那年顾子砚说:“阿湄,这些梅花好看吗?”
他曾亲手为她栽下一园梅花树,可是如今,他顾子砚把另一个女人封了梅嫔。沐之湄记起来东宫里那一园影影绰绰的红白梅花,手下用力更甚。手掌被划烂,鲜血顺着手腕滑下。沐之湄想,她终于连最后的念想都没有了。
日头高高挂在空中,毒辣得厉害。沐之湄委顿在地,身上都被冷汗浸透。
沐之湄并没想过,梅嫔会来找她。
她们俩不该有交集的。一个遭了嫌弃的废后,一个圣眷正隆的宠妃。梅嫔带着宫人太监进来西苑的时候,沐之湄以为,梅嫔是来笑话她的。
沐之湄看着她并未施礼,她盯着梅嫔的脸看得很仔细。梅嫔穿着云纱制的单衣,发髻高绾。眉梢挑着,颇显傲气。
梅嫔摒退了宫人,伸手抚着尚未隆起的小腹,冷笑了一声:“沐之湄,你猜本宫今日来这儿,所为何事?”
沐之湄垂着眼睑,听梅嫔又道:“你晓不晓得,本宫并不姓梅,本宫名字里也没有梅字。可是那日皇上看到本宫,连名字都没问,便把本宫封了梅嫔。”
梅嫔眼神愈发怨毒:“宫人都说,本宫生得一副好样貌,不偏不倚,正像了前皇后你。皇上待本宫很好,可是他每每喊着本宫的时候,都叫本宫心焦,他虽一声一声喊着“阿梅,阿梅”,可是本宫知道,他喊的是谁。所有人都以为你失了宠,再不会有翻身的机会。可是本宫放不下心,沐之湄,本宫容不下你。”
梅嫔径自倒了杯茶水,从袖子里掏出一个药包,打开洒进了杯子里,幽幽叹了口气:“这杯子里的,是堕胎药。本宫听闻你***了皇上许多血亲,如今再加上一个孩子,不算过分吧。”
沐之湄没有反应,梅嫔仰头喝下一半。腹中疼痛难忍的时候,她听到沐之湄说:“我不过是个将死之人,你们一个个的,怎么就不肯放过我呢?子清***了我的孩子,太后逼着我***了她,现在,你也来逼我。我对你做过什么?为什么连你,都不能放过我?”
梅嫔弄出的动静终于惊动了宫人,沐之湄坐在椅子上,目光幽幽地越过窗外,却又不知落在何处。直到顾子砚的身影出现。
顾子砚顿了步子,两个人隔窗相望,却无言。
沐之湄眼泪滑过眼角的时候,顾子砚终于回过神来,大步进了屋子,将倒在地上的梅嫔拦腰抱起。要离开时,沐之湄轻轻叫住了他:“阿砚,你爱我吗?”
她终究是想求一个答案的,太后说顾子砚爱她,可她不敢确定。她一辈子折在一个情爱上,她想知道,她沐之湄所爱之人,是不是也爱她。
顾子砚僵着身子,怀里的梅嫔虚弱地抓住他的衣襟。他闭上眼睛,背对着沐之湄说:“不爱。朕爱的阿湄,已经离开很久了。”
他抬步离开,未看到身后的沐之湄泪如雨下。
那是顾子砚同沐之湄的最后一面。
第二日清晨,往西苑送膳的宫人叫了许多遍也没人应,探了鼻息,沐之湄竟去了。
淳化二十三年,沐之湄追随陆贵妃的那一日起,便服了毒药。陆贵妃说,她最多,只有十年可活。沐之湄是愿意的,她用她未知的一生去同陆贵妃做了交易,只求一个跟在顾子砚身边的机会。
疯狂这般,不过一个心甘情愿。
这些年来她腹痛难忍,不过是毒药作祟。在西苑的那次重病,是沐之湄故意的。她晓得自己活不长了,她想要陪着子砚,在仅剩的这些时间里。
只是陆太后,没有给她这样的机会。
她穿好衣服躺在床上等死的时候想,现在她便是死了,顾子砚也不会难过吧。毕竟,他那样恨她。
沐之湄又觉得难过,这些年来,她明明那样喜欢顾子砚,却好像都没来得及同他说一句喜欢。
时光蹉跎,岁月成歌。她和顾子砚之间,便是长恨歌。
长恨造化弄人世事坎坷,长恨变故迭生君心非昨。
顾子砚知道消息的时候,怔了许久,墨点子大落地滴在宣纸上,晕开了一片。而后他起身,去了东宫。
这些年里他没有子嗣,东宫一直空着。陈设都未变,他没有犹豫地走到了梅园。他突然有些后悔,为什么沐之湄问他的时候,他没有说爱她。
年轻的帝王终究倚着梅树落了泪。弦月东起时,顾子砚吩咐宫人拿来蜡烛,亲手烧了梅园。
这浩浩天下,即便如诗如画,可是,只有他一个人了。
带有梅花启示的作文结尾【三】
Dear teacher:
Let me introduce one of my friends to you.
His name is Liming . He graduated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and major in English. He started learning English since 12 years old. His parents have a lot of American friends. That’s why he has no problem communicating with Americans or others by speaking English.In his spare time, He like to do anything relating to English such as listening to English songs, watching English movies or TV programs, or even attending the activities held by some English clubs or institutes. He used to go abroad for a short- term English study. During that time, He learned a lot of daily life English and saw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Now he is my best friends .We often communicate in English .I can learn some fresh things from him.
Yours
带有梅花启示的作文结尾【四】
冬带着怒气冲冲的西北风和调皮可爱的雪花娃娃,浩浩荡荡地“***”了过来。眨眼功夫,天地间一片寒冷。暴躁的西北风“呼呼”地吹着,似乎还觉得不够,又撒了一把雪花,继续气势汹汹地怒吼着。漫天飞舞的雪花,调皮极了,一会儿飞到东,一会儿飞到西,它给这儿的大地盖上了毛毯;又给那儿的大山戴个帽子;还为冷冰冰的铁栅栏织了条围巾。
西北风还在怒吼,它得意地看着人们拉紧衣裳。树木被冻得瑟瑟发抖,可还有一个小东西仍傲然挺立在那儿,不屑一顾它的攻击,这,就是梅花。无论风怎么吹,雪怎么下,梅花还是不屈不挠地挺立在那儿。终于,风退缩了。它灰溜溜地从梅花身旁绕过,无可奈何地走了。梅花打开了花瓣,散发出它那独特的清香。路人纷纷止步欣赏,无不一一感叹:“真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呀!”
在这百花凋零的季节里,只有梅花绽放了。它,也得到了生命的真谛!
带有梅花启示的作文结尾【五】
我过了许多有趣的节日,可今年的端午节是我最快乐,最难忘的。 端午节那天,我和妈妈早上去菜场买了一些棕叶、糯米。回到家里妈妈把一个盆子里装了水,把棕叶放在里面,我很纳闷就问妈妈“妈妈,为什么要把棕叶泡在水里?”妈妈说“棕叶泡在水里才不会发干变硬,这样我们才好包呀!”噢,原来如此。妈妈洗好米,也将米泡在水里,我连忙对妈妈说“妈妈,米泡在水里,也是和棕叶一样的道理吧!”妈妈点点头说“是的。” 终于开始包棕子了,只见妈妈将两片棕叶重叠在一起,将大的一头圈成一个漏斗的样子,然后放入米,再把多余的叶子顺着漏斗包裹起来,最后将绳子横在三个角中间,绑好两个角,这样一个棕子就诞生了。 我也学着妈妈的样子包,可是我的棕子真是漏斗,一不小心,米就一粒一粒的往下落,妈妈告诉我在卷成漏斗形状时要注意不能有缝,那样就真成了漏斗了,米在放进去的时候也要按紧了这样煮出来的米才结实。我小心翼翼的包着,终于我成功了,我特意将我包的棕子用绳子系好,这是我的劳动成果,我要留作纪念。 我很高兴,我学会了包棕子,所以我忘不了今年的端午节。
带有梅花启示的作文结尾【六】
小吧!所以不明白其中的深刻道理,妈妈耐心的给我讲到会了为止。然而,现在我却明白了那里蕴含着深刻的做人的道理。
后来我听见了是这样的:一只猫咪叫迷迷,有一天它上游乐场去玩,在两面镜子前停住了。哦,原来是哈哈镜,它在镜中看见了自己。第一面镜子中浮现了自己,是一个如此高大,看“我”的肌肉比别的猫多的多,但它又说“瞧,我可以和动物园中的老虎媲美了,”说完便哈哈大笑;可是到第二面镜子前,便支支吾吾说不出声了,因为它看到了自己说的只剩下一副皮包骨了,它到家便开始不吃不喝,饿的'瘦骨嶙峋,仿佛不是它了!它的朋友听说了,便去看它对它说:“你找的是哈哈镜,不是平面镜。”它恍然大悟,又恢复了气色。
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了,人生何尝又不是这样呢?有时像第一面镜子让我们迷失了真正的自己,但又会多了自己对自己的奉承与偏见;然而照另一面镜子时,随之而来的便是迷失自己时的悲伤过度,使自己真正成了个心情失落的人。
所以无论在书上或在生活中,我们都要保持平常的心态来面对每一件事,生活也是如此。
再告诉你们一句话:美不美不是在外表上看的出来,而是他的内心!
带有梅花启示的作文结尾【七】
位临长江南边一座不太高的小山上,依山耸立着一排排整齐的教学楼,在教学楼后面紧挨着一座小山,看上去,比教学楼就矮那么一点点,有幸坐在靠近教室窗边上课,每天都可直观亲切感受到小生灵喜怒哀乐,教室窗外看似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包,但当你身临其景现实感受一番后,你会异常兴奋的发现,这就是虫子们的后花圆。每每到了晚上,正值学生晚自习时,那些漂亮的,艳丽的,狡猾的,调皮的,可爱的虫子们便不约而同的从后山上出发,有的爬的稳稳当当;有的嫌太慢,展翅飞起来;还有恐高的,一蹦一蹦的也赶来了,来陪伴这些浸泡在书山题海苦读中的学生。有的人惧怕它们,便紧闭纱窗,任那些虫儿在纱窗外趴着苦苦期盼;有的人却不顾这些,忍不住打开门窗,让虫子们与学生共享光明。于是乎,教室里便呈现一派美丽迷人的风景线:纱窗上,灰蛾扮作雪花粘在上面,草蛉给人的视野带来一丝绿色,肥肥的蜘蛛织起网来,想捞点油水,看它那笨拙的身手,不觉得好笑起来。有几只漂亮的凤蝶会时不时的飞进来,饶着灯翩翩起舞,吸引不少关注的眼球;油油的蛐蛐儿会钻进角落里时不时的演奏两段经典名曲;骷髅会在你不注意时从你耳边掠过,停在你正奋笔疾书的笔上或纸上,若无其事的理理胡须,抖抖翅膀,待你要教训教训它时,它却一弹,跳开了;还有那头黑胸黄的小甲虫可厉害,在你身上爬过之处,便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从手臂传遍全身......
这些生灵是后山派来的使者,使寒窗下苦读的学生在不自觉之中感受一丝大自然的慰藉,使人们不得不对后山的另一面产生好奇,真想瞧瞧,在山的另一头,定会有什么宝贝。假如人有来生,不仿试着做一条可爱的虫儿,趁着夜,顺着光,从这后山上出发,去看看当年陪读同学们的真实情景,想必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吧。看来,后花圆这番景遇和情怀注定是终生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