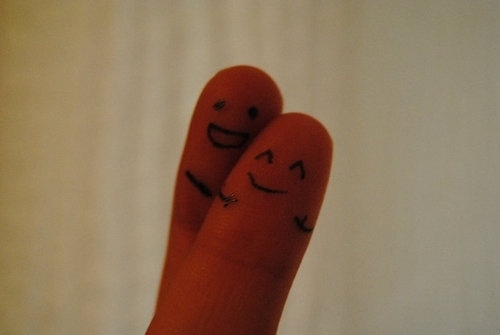
高高的瘦瘦的老师作文【一】
雁儿——渴望
她过早的成熟了。她的纯真过早的衰竭。
看到颂莲挽起袖子洗手时,她觉得这个新来的女孩与自己如此的相似。同样年轻。似乎同样的家境。在一瞬间她们甚至有成为朋友的可能。
可是当“四太太”的喊声响起的时候,她几乎自卫的把她隔绝在外。
她很可怜。她觉得她的命运是这一个又一个新来的太太造成的。像《上阳白发人》中的女子,把一生未见君容归咎为杨妃之过。
她的幻想一次又一次的被这些新来的太太打破。
她觉得这个新来的太太和她如此相似。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能代替她。
她最鲜明的标签是渴望。
她的渴望如此直白。跟老爷偷欢的时候看到颂莲进屋,她眼睛里甚至没有恐惧。直入人心的目光好像在做一件大义凛然的事。
她的渴望如此真实,即使是因为点灯被当众处置,她仍毫无悔意,她倔强的跪在雪地里,始终不肯认错。
她渴望。没有任何羞愧,因为她觉得她的渴望是正当的,几乎像一种理想。
自己点灯笼,想象捶脚的感觉。当太太们的捶脚声响在院子里的时候,她陶醉的想象自己。
她真的还太年轻,所以轻易地被卓云拉拢,并作为牺牲品。
她因为渴望而不得将愤恨转嫁于颂莲。
她至死不知道她该怪的是谁。如果真要怪,怪的是“府上多年的老规矩”;她至死也不明白,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颂莲——徘徊
颂莲刚出现的时候,还是两只粗粗的大麻花辫儿。脸上带着烈女的表情。她是个心里有成算的人。也是在乎爱情的人。她的话仿佛是说,她想嫁一个她爱的人,可是如果不能嫁一个她爱的人,就干脆嫁一个有钱人。哪怕当小老婆。这是种宁缺的态度。为了保住爱情的纯度。
她嫁入一所大宅。气派端方。
她走进大宅的时候,眼角全是自尊和不屑。可是镜头中她被挤压在墙根。又的确太渺小了。
她甚至避开了去接她的花轿。也不让管家帮她提东西。她反感这一切。
她各色。她还那么年轻。
大宅幽深。端庄森严。不见人影。一路走来只有脚步声。
她在其中穿过一扇又一扇的门。这些是她要走一辈子的路。
进入之初,甚至不知如何融入。
抬灯入院,点火,燃灯,悬挂,一干人等面无表情,空荡的院子响着每一个动作的回音。几个女人走进来,进屋说“照府上的规矩”。
洗脚,捶脚,梳头,更衣。这是一个完整的仪式。未见男主人,只见男主人的红灯笼。她脸上带着惶恐。
院落的幽兰色,其中有灯笼的红。像一个暗藏***机的洞穴。
她觉得老爷很温柔,不管是问捶脚是不是舒服还是要她过来仔细看看都是温声细语,只有聪明人能窥视背后的***机,把一个人慢慢磨蚀掉棱角的力道,而她尚年轻,相比这大宅。
她仿佛看见了她长长的寂寞,像镜子里自己的泪,只有灯笼陪自己欣赏。
空间和人都是这样封闭。即使读过书,那些学问在这里也是用不上的,聪明和学问不成正比。她以为自己很聪明,却不知道自己不通世故,只是凭直觉先入为主的接受卓云排斥梅姗,在受挫时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她无法洞悉这里的哲学,她只知道自己忽然成了太太,似乎应该是主人,起码应该高过一个丫鬟,却不知道她的地位远远没有稳定,随时可能坍塌;她也无法接受老爷和雁儿的偷欢,她还在徘徊中,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她不知道既然能够有四位太太,那么和一个丫头偷欢并不是不能容忍的大错。
直到捶脚的声音如筛子般响在大院里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她开始需要这件东西。
她甚至发现,不能点灯吃不到想吃的东西。她终于有些明白。于是当有人再问起为什么大学没有读完的时候,颂莲的回答已经不再是家父病了供不起,而是念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老爷身上的一件衣裳。而当她发现布偶上自己的名字时,并且是卓云的字,她终于知道她的生存是如此的需要争斗。她慢慢开始蜕变。
假孕。这是她并不高明的手段。可当长明灯点起来的时候,她还是自我欣赏的迷醉其中。她终于开始欣赏这种争斗。
这种不高明的手段终于了解了她的徘徊。
她在不知不觉中葬送了雁儿和梅姗的生命。
她并不像卓云那样暗喜。她悲伤。她的不扯定性决定了她即使没有被封灯,也始终处于徘徊的境地。
梅姗——抗争
梅姗是陈府的一颗痣,长在最敏感的部位。
这种抗争并不是卓云式的用尽手段,而是不屈就于一个封建姨太太的位置。
梅姗历经了颂莲式的徘徊,以独有的方式坚强的在陈府中存活,不管是自我沉迷的在院子里自唱自赏,还是和高医生偷情,她都像她身上一件件色彩艳丽的衣服一样,张扬凌厉,棱角分明。
因为她尚存资本,老爷仍然保持着对她较强的兴趣,因此她不用像卓云那样因为惧怕失去而费劲心机;她漂亮,嘴角暧昧的笑带着隐晦的性欲味道;她有自己的生活;她为陈府生有一子,这是她基本的保障;她聪明,是对陈府的规矩和本相最知根知底的一个,正因为此,她不会耗尽力气去抗争;她也尽可能多的保留了她的真纯:她的真诚和刻薄都露在外面,她的抗争太肤浅,她在梅姗的新婚之夜把老爷叫走,在叫不走的时候在清晨的院落大声的唱戏,
在不想客气的时候毫不掩饰,连招呼也懒怠打,也不会在饭桌上像大太太和卓云都在老爷面前给颂莲夹菜,在点灯的时候,不会像卓云那样殷勤的笑。
她不爱老爷,她也不缺少爱。她的抗争并非自己的需要,只是成了她在陈府中的一种必要习惯。
她毫不掩饰她的寂寞,也毫不掩饰她惊人的美丽。
她是大院里最真实的人,在空旷的楼台上唱戏,不会因为颂莲上来挑衅停住,铿锵嘹亮,神采飞扬。戏唱完了,脸上的哀怨无奈也一并裸露;她不会客气的停下说话,戏也是如此。
“你想听,可我不想唱了。”这是她的生活态度。
这就是梅姗,她在和她自己的定位抗争,她还有力气。
她在规矩之中,又在规矩之外。她不是规矩的恪守者,只是在沿着规矩的边缘小心翼翼的走。
她看得最清楚,戏做得好能骗别人,做得不好只能骗自己,连自己都骗不了的时候就只能骗鬼了。
她原来想一直能骗别人,至少也能骗自己,但最后真的连鬼也骗不了,抗争的结果是,香消玉殒。
卓云——臣服
她的***很大,她一直在挣扎中,可这种积极的挣扎实际上就是一种臣服,对自己姨太太身份的臣服,她沉湎与其中不能自拔,这是她毕生的.事业。
和大太太比起来,她更像一个当家太太。
她懂得这个院子的处事哲学,笼络新人,孤立排挤。
她活在外面的是一张假面。
只有她一个人,在点别院灯的时候知道谦和的对笑。但只有她一人,心里真正的难受。
她是最真心在乎老爷的人,她会在老爷面前给颂莲夹菜,因为老爷说大家要好好照顾她;她会带着一点炫耀去找颂莲剪头发,因为老爷说头发短了会显得年轻。
但在乎并不意味着她爱。她并不懂得爱。是她需要。她除此以外一无所有。但是她懂得,哪院点灯哪院就可以点菜,点灯的太太连下人都会高看一眼,点灯就意味着能在陈府中得到真正的地位。
她是最锲而不舍的一个人。她臣服于作为男人衣服的定位,并把一切努力当成理想。她不但像大太太那样保全自己,还要争取更多。
她默不作声的解决了所有的障碍。
到底谁真正的聪明呢?颂莲?梅姗?如果论争斗的技术,只有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
只是她不知道,她马上就要垂垂老去,无论她怎么挣扎,她最好的结果,不过是成为大太太。
大太太——心死
她甚至没有名字。眼睛里没有光彩。她是唯一一个听到哪院点灯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丝毫没有变化的太太。
因为她知道不可能是她。
她毫发无伤的在陈府活到那么大年纪,早已经被磨砺出坚硬的心。
还有,没有人知道她有多大年纪,是真的垂垂老暮之人,还是因为丧失了希望。
她脸上的皱纹更多的只能依稀让人想到老爷的岁数。
话很少。表情很少。她最为深切的反应,也不过是承认自己早就是老古董了,预言陈家早晚败在这一代手里。
有意思的是,在她一字一句缓缓慢慢与颂莲对话时,背景中的两个丫头也缓缓慢慢的擦拭着房间里的物件,虽是年轻的女孩,却像是慢动作。
有意思的还有….身份确认,字里行间的话,大太太更像是一个母亲。
在这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浓缩院落,大太太艰辛的母仪天下。这时我们想想,其实为什么皇后总那样尊严神圣,是因为她屏蔽了人的正常***。
她从颂莲式的徘徊,进入梅姗式的抗争,经过卓云式的臣服,***已经磨蚀。
当她不能占有自己的丈夫时,最好的心态莫若把他当作儿子。这时***消失。她得以保全自己。
当颂莲厌恶她的老气时,她并不知道,在这个院子里,最好的生存法宝就是,心死。
五太太
如同春夏秋冬又一春。
从渴望到进入,从徘徊与抗争到臣服与心死。又是新的轮回。
高高的瘦瘦的老师作文【二】
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女性主义的情况下,中国近期的电影却鲜少涉及这一主题。中国没有女性主义吗?《七月与安生》还有目前没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甚至《大鱼海棠》都有涉及到女性主义,但是无一例外,这些电影的女性主义视角并不突出。
所以,今晚,我们来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谈部老电影。
《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改编自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
“红灯笼”这一意向贯穿整部电影的始终,可见,其象征意义绝不简单。影片中,每当红灯笼被点亮,被挂起的时候,就意味着有新人要进入这个院子了,意味着有人要得宠了,有人可以点一份自己喜欢的菜了,同时也意味着有人要失宠了。仅仅一个红灯笼,却几乎牵扯了这个死气沉沉的大院中所有女性的神经,此时的它代表着权利,代表着地位,就是不像红灯笼。
红色给人的感觉是热烈,是激情,是情欲。影片中,只有被陈老爷点中的院子才可以点红灯笼,陈老爷的到来意味着性,而红灯笼就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性暗示。在这种暗示下,女人不得不顺从男人,因为男人决定着女人什么时间可以有性,什么条件下才可以有性,女人在这种压抑下渐渐沦为男性的玩物,而在以陈老爷为代表的男性眼中,院中女人确实只是性玩物而已,因此,雁儿活着陈老爷可以明目张胆的占她便宜,雁儿死了陈老爷连见都没见一面。对于男性来讲,薄情是生理决定的。
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就是高高挂起的性,大家心照不宣,却又无人不心知肚明。在这种直指女性的暗示下,女人在这个红灯笼下变得一丝不挂,其自尊也被一点一点燃烧殆尽。红灯笼凭借着男人的特权愈加鲜红,在这种情况下,女人只能“以色事人”,只能“你算计我,我算计你”。性压抑压抑的绝不仅仅是女人的本性,还有女人的尊严、善良。从这个角度看《甄嬛传》,后宫的争斗就更好理解了。
南唐以来,女性的另一苦难就开始了,那就是裹小脚。几千年以来,脚成了另一束缚女性的工具。电影中并没有涉及裹小脚的画面,但没出现就意味着男性不再关注女性的脚了吗?当然不是。
颂莲刚刚入府,迎接她的不是老爷,而是捶脚。捶脚那在陈府可不是小事,在他们的规矩里,脚要被精心缝制的红绸子盖好,就像盖着红盖头的新娘,外人可是不可以看见的。捶脚有专门的人服侍,有特制的工具,它会发出急急令般的声音,整个院子的'人都听得见,可见其待遇级别之高了吧。所以,就连受过新式教育的颂莲也被其俘获了,为了捶脚,她绞尽脑汁,耍尽手段。在某些情况下,人性的恶显露无疑。可悲,可叹。而回想颂莲刚入府时,陈老爷是怎么给她解释捶脚的,他说:“女人的脚捶好了,才能伺候人。”哈,原来还是脚。
当女人的脚被一层一层裹上,女人行走甚至站立的权力就已经被剥夺了,一个不能站不能走的女人除了依附男人还有别的选择吗?而当影片中的女人越来越依赖于捶脚时,其命运也在那一声声急急令般的捶脚声中越来越无法被自己控制。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波伏娃的话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电影唯有比生活更真实,才会更有力量。
高高的瘦瘦的老师作文【三】
有人说张艺谋是个不会讲故事的导演。他前期最优秀的那些作品,都依靠着强大原著文本的力量。而那些曾经被他改编过作品的作家,包括余华、苏童、莫言、毕飞宇等,几乎可以列出那一代中国文坛的黄金阵容。
但每每离开原著小说的支撑,张氏作品便很容易陷入形式大于内容的窠臼。从原创剧本的《英雄》和《十面埋伏》,到翻拍自经典话剧和电影的《黄金甲》与《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将自己的美学理念发挥到淋漓尽致,也一手将华语电影带入到了大片时代,但在叙事上,却一再饱受诟病。简单而缺少内涵的故事、脸谱化的角色设置让一出出弘大的场景沦为加长版MV,“国师”的头衔越来越成为网民调侃的对象。虽然近来与严歌苓的两次合作尚算及格,但无论如何,80至90年代之间的那个用影像记录着这片古老而苦难大地的,充满着锐意、新意和进取心的张艺谋,终究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再去回味他创作黄金期的作品,更能感受到当年的他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性格的深入思考,和与内容主题更加契合的形式表达。特别是张艺谋导演生涯之初的“红色三部曲”,更是以其日后蜚声国际的色彩、构图等极具个人风格的形式特点,留下了足够让人在品鉴中思考、在反思中回味的佳作。
从《红高粱》到《菊豆》,再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张的三部曲虽然都聚焦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女性身上,但主题和格调却越来越冰冷。而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成为了其中最为绝望、悲凉的一部作品。
张艺谋很会拍女人,从他一手捧红了两位国际巨星便可见端倪。但如同他的故乡,他最擅长表达的女人,也是充满着浓浓黄土气息的那种。所以,他将故事的背景由原著小说的江南水乡移至北方大院,不失为避重就轻的讨巧之举。
无论从面相还是身形上看,山东女人巩俐都不是小家碧玉,而她所饰演的经典角色,哪怕是为妾为婢,哪怕是社会最底层,都透着一股子倔强和不屈。但我以为,恰恰是打破了这个惯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才是她不可多得的最佳表演。
辍学女大学生颂莲在一开始的时候,无疑是一个非常具有独立人格的新时代女性。她拒绝迎亲的花轿,一个人走进大宅门,这是对命运的一种无声反抗。而后,她却在不自觉间,陷入为主为奴的双重环境之中,逐渐迷失了自己,成为陈府这座吃人宅院的又一个牺牲品。
导演在描绘颂莲人格变化的时候,很巧妙的在全片以中远景为主的镜头组合中加入了少量特写镜头,精准的捕捉到女主角表情的细微变化,从而反映出一个花季女子一步步在礼教和规矩的压制下沉沦。
第一次特写,是开篇与继母的对话。颂莲面无表情,眼神中透露出倔强。通过这次特写,观众不难接受导演的`意图,即旧社会女性的际遇沉浮,绝大多数时候都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即使像颂莲这样受过西式教育的女子,仍然逃不过不由自主的命运。
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特写,则呈现一组明显的对比。从第一次被服侍捶腿时的不知所措,到渐渐习以为常,再到从中意淫出一种类似性高潮般的快感。与其说颂莲忘记了初心,毋宁说她习惯了陈府中的游戏规则并慢慢乐在其中,彻底完成了从学生到“四太太”的心理转变。而这种游戏规则,正是以男权或者说夫权的高高在上为基础的。
你可以将这部电影视作小型版的宫斗剧来看,因为其中照样不乏相互嫉妒、猜疑、陷害、争宠,甚至这座深深的宅院,也像极了一座小皇宫。有高高在上的主子,有流言蜚语的仆从。但陈府却更像一个小监狱,每个人都被困在了这里,无从逃脱。失败者如同梅珊与颂莲,一个死掉,一个疯去。而成功者如卓云,也不过是一次次看着比自己年轻美貌的新人走进门楣,最终不是像大太太般看破红尘,便是重蹈三太太、四太太的覆辙,怎么说得起一个胜字?
哪怕是高高在上的陈老爷,也一样是这大宅院的犯人。君不见,导演常常给出鸟瞰视角的堆成构图,让宅院呈现出一个“口”字。而人在口中,不是“囚”又是什么?
整部电影里,陈老爷从未以近景出现,观众几乎无法看清他的脸。这种安排也是颇为评论界所称道的点睛之笔——陈老爷由此被抽象成一个意向,一种规矩的象征。他着力维护旧的统治秩序,哪怕需要为此抹***掉活色生香的爱妾。而所有女人存在的价值,无非是带给他欢愉,并为他传宗接代,延续着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礼教传统,如同这个苍老、一成不变的中国。
比起原著,电影版最大的亮点便是小说中原本不存在的灯笼和捶腿。点灯的过程繁琐而费力,却带来了一种肃穆而庄重的仪式感,加之全片的对称构图、长镜头和静止画面等视听语言的应用,大大加强了沉闷压抑的氛围,为人性沉沦的主题铸造了完美的舞台。特别是夜晚冷色调下的斑驳宅院,像极了宋词中的那一句“庭院深深深几许”。
陈府像一头噬人的猛兽,只有走进去的人,没有走出来的魂,即便是枉死,灵魂也要被困囹圄,无法超脱。
片中以四季轮回作为分段式的时间轴,却独独落下了春天。春是万物生长、是播种未来、是希望萌生。而在陈府中,或许什么都不缺,却唯独缺了希望、缺了未来。
作为本片拍摄地的山西晋中的乔家大院,很多年后还诞生过一部经典的电视剧。虽然居中不乏与机敏,但每每在电视上看到那雕梁画壁、高墙大院,我仍然不寒而栗的想起,那个绝望到让人心死的故事。
高高的瘦瘦的老师作文【四】
很多年前还小的时候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除了鲜艳的蓝红色彩之外,根本不记得什么了。而现在再看,却觉得能把一个除了女人还是女人的电影拍得这么厌女,也的确是张艺谋和苏童的本事。
这也是我对最近几乎所有宫斗剧清宫剧穿越剧的最大反感。的确,这些电视剧和电影无一例外都在突出表现几个坚强,聪明,有能力,有手段的女人的斗争,但是,这些女人斗争的对象是其他女人,而这些女人斗争的最终目标是获得男人的认可。男人在这类片子里超越了女人之间的小打小闹茶杯风波,他们是有最终决定权的法官,同时也是从旁观看这些女人斗争取乐的观众。颂莲,梅珊和卓云的斗争,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完全体现在那些屋前挂起来的红灯笼上。老爷上你,你就是个人;老爷不上你,你就是连狗都不如。男人认可一个女人,那么她才有价值。而女人本身的抗争,对自我的实现也最终只能通过男人对她的承认才能获得。
你也可以说,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批判现实主义就是要揭露问题啊。但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本质在于“批判”,批判要高于现实。而大红灯笼高高挂,可以说连”现实“都没有做到。比如说女主人公颂莲,我们知道她是个学生,没念完书就因为家里经济情况不好不得不来做个姨太太。颂莲到了夫家之后,就完全陷入芝麻蒜皮的斗心眼。她的价值从电影一开始,就是由红灯笼决定的。那么颂莲本人到底是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她有什么爱好?她念过书,那喜欢看什么书呢?她在没嫁到这家之前,作为一个女人,有没有自己的梦想?她脱离了“老爷”,到底是个什么人?我们完全不知道。
你把一个女人的价值完全建立在男人的肯定上,这就是厌女症的最根本表现。把几个女人的价值不但建立在男人的肯定上,而且让他们为了这个肯定,为了这种自我实现而互相之间仇恨嫉妒陷害,这么写不但否认女人的价值,更否认他们的人性。大太太不闻不问,二太太口蜜腹剑,三太太仗势欺人,四太太虚伪冷酷。。。最终三太太被吊死,四太太发疯,说到底,全都只能算是他们自作自受。这个大院里,简直是洪洞县内无好人,而最终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群卑微的女人像摇尾乞怜的狗一样,在争夺男人掉在的残羹剩饭而已。
苏童和张艺谋很明显的是把男人放在一个局外人调停者执法者的地位上,居高临下的来看这些女人们像迷宫里的小白鼠一样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在撕斗。挂灯笼的系统,简直就是一个incentive program, 比大公司员工鼓励计划的设计还巧妙还邪恶。但是,电影本身却从来不以任何人的立场来质问这个系统。人物完全没有能够超越他们自己的地位而获得升华,也并没有达到“批判”的目的。就好比说狂人只停留在“满纸仁义道德”的层面,却没有看出“字里行间的吃人二字”。
中国人对于女性,是带着一种渗入骨髓的厌女症。20多年前的电影就是一群女人为了一个男人争宠,搞得死的死,疯的疯。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旧在乐此不疲的看一群女人为了争宠而宫斗。喜剧和悲剧唯一的不同就是女主有没有最终获得男人的承认而实现自我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