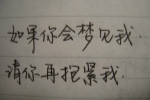酝酿一个人的思绪作文【一】
当绿油油的草坪上,间或着错乱的枯叶,我被那份零落的美触动了心弦。 在那怦然心动的片刻,我停住了脚步。很想用我的角度拍出心中的那份感受。可无法描述 也没法捕捉,那个秋近渐凋零的景象。
很想分享当时的`那份心情,发了两张给一个朋友,很快收到了个“秋?”的回复,其实这不是我想要表达的。带着那个阳光下,芳草萋萋落叶点亮心情的景致,一路走回。思绪有点乱飞,短短的几分钟路程,我想起一个人说过:吃甜食的人运气不会太差。转而想到了自己吃甜食,运气也没那么太好的过往。看着一个散学归来的高中生,想起了我的高中时光,曾经有那么一段情犊初开的情怀。又想起千年元旦晚会被牵出的片段。莫名笑起来。曾经成长中青涩的、迟钝的、还有开心的许多,终究都是未曾开始就已结束。留给现在的就都是曾经那么傻。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思绪,因落叶起舞。
我一直觉着,叶子的离开是叶的自由。和风,和树,既不能相触在云端,也不能紧握在土里。所以离开,或落叶翩翩,或零落成泥,或化为标本,各种呈现都带着不同的美。
我依然心动着那片绿油油的草地,些许枯叶零落带给我的美。依然执着那么第一眼,心弦轻轻一动。如某件事、某个人。
酝酿一个人的思绪作文【二】
如今,一个冷冷的冬季,走在这条小路上,尽管天空没有飘雪,但那挥之不去的的感觉让我伸出双手,把雪花一片片接住。
幼芽已经长成大树,满树的银花,犹如走过你的窗前,那抛来的脉脉的笑意。
爱没有错,季节没有错,只是忧郁的歌声使我想到夕阳。在季节的栅栏边,你的`灵魂是冬天的肢体,上面落着美丽的雪片。长久谛听的人,属于流雪,生命和谐而神圣。雪,冬天的雪,纯洁的雪,淌过高山,跨国山谷,灿烂的阳光亲吻着你透明和不透明的肢体。种籽在根须间蜕变,季节在凝眸,天空在变换着色彩,慢慢的雪流泪而去,但永恒的视野无比惆帐起来。
酝酿一个人的思绪作文【三】
??晚中飘飞的思绪作文夜空黑沉沉的,夜风冷飕飕的,星星点点的夜雨零零落落,屋外昏黄的灯光淡淡地透进她租住的小屋。今夜,躺在床上的她在想些什么呢?
新年的第二天傍晚,她早早地做好和吃好晚饭后,打算去和也在此租房住的老姐妹老邻居们聊聊天。她一向节俭,关了电灯,准备出门时,只觉头晕晕的,身子也轻飘飘的,仿佛一个喝醉了的人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地方,在晕玄中她摔倒在地上,潜意识中她想呼喊,却吐不出半个字,她昏倒在冰凉的地上再无知觉。
是什么东西在刺痛她的心,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刺激她的眼晴,她不知道。雪白的墙壁,好像在她眼前浮现,她努力地睁开眼晴,却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她的眼晴在动呢。”“她有感觉了。”她听到有人在说话,在说谁呢,她不知道。她终于睁开眼,她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旁边是一张陌生的脸庞,那人正在本子上记着什么。“老人家,感觉怎样?”有人在问她。“我在哪啊?”她问,声音柔弱如丝。“老人家,这是医院,你是昨天晚上来的。”有人回答。这一刻,她终于清醒了,昨夜摔倒的.事也一并记起来了。刚才和她说话的是她的管床医生。“老人家可以离开重症监护室了,去叫她儿子过来一起送去病房。”“好的,李医生。”有人答应着出去了。十五分钟之后,她住进了普遍病房,而此时已经是次日下午一点钟了。
这是一间普通病房,住着四个病人,她是其中一个。她的床头卡上写着她的姓名、年龄和病因。此刻,老姐妹老邻居们正围坐在她的床前,看到她转危为安,大家都很高兴。她看上去还很虚弱,大家呆了一会后就告辞了,并嘱咐她好好休息,把病养好。人们走了,病房里安静了许多。她也累了,闭上眼晴睡了。
她不知道,昨儿晚上她昏迷之后发生的一切。昨晚八点过钟,一位老姐妹曾来她家门前喊她去串门,她没有应声。到了九点过钟,老邻居再次去叫她,仍然无人应答。老邻居问旁边人都说不知道她去哪了,大家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她从来沒有过这种反常现象。老邻居拉开她小屋的窗户,借着外面的灯光,看到有东西倒在地上,老邻居吓坏了,赶紧大声呼喊众人前来,去推她的门原来是虚掩的,用电筒一照地上,竟然是她。大家都很紧张,有人立即拨打120,房东也立刻报了警。还有邻居打电话给她的两个儿子,但是他们都沒有及时赶到,因为他们住的都很远。于是,人们又拨通了村里干部的电话,十五分钟后,各路人马都到齐了。人们叫刚刚赶到的她的大儿子立刻背她去120车上,大儿子却死活不愿。他说,怕他妈妈万一死在他背上,他没法向弟弟交待。一位村干部低沉有力地说,这是***呀,你以为她是谁?!这老大在众人的劝说和帮助才背着她上了救护车。
到了医院,她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小儿子也赶到了医院。老母亲生病住院,儿子应该掏钱治病。医生叫家属去交钱,好给病人进行救治,这哥俩异口同声说沒带钱。无奈,一名村干部垫付了住院费用。医生要求家属签字,这哥俩互相推诿不愿签字。村干部们无奈,叫哥俩开会,竟然开会到夜里两点才有结果:小儿子答应承担老母亲一切费用,大儿子概不负责,他说母亲名下的财产全部归弟弟所有,母亲理应由弟弟负责,何况他自己已经安葬了父亲。
她不知道,村干部们叫哥俩接她同住好照顾她,老大说自己租的房子太窄沒办法,小儿子说自己住的也不宽廠。村干部无奈,众人也无言。多亏了老邻居,她才从鬼门关逃了回来,可这哥俩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也许,老母亲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负担一个累赘,死不足惜。他们可真是一对好哥俩。
今天,八十三岁高龄的她出院了,一个人从医院走回租住的小屋,沒有谁去接她送她陪她。
今夜,这位老母亲在想些什么呢?
酝酿一个人的思绪作文【四】
带着积存许久的烦躁、不安与无聊,我又一次从家离开,去一些地方。
也许我想去的地方永远也找不到,也许等找到了才知道一切都是无奈。
我走着,用一颗不完整的心,带着一双充满疑惑的眼神,走着……
我会走到路的尽头吗?
剩下的路还有多远?
是遵从命运的安排,还是向生活做出无为的反抗?
……
这一切的一切,都像一个巨大的\'雾团笼罩着我、吞噬着我……
前方是一片森林。我穿过了,用去了七分之一的力气。
前方又是一片森林。我穿过了,用去了七分之一的力气。
前方还是一片森林。我穿过了,又用去了七分之一的力气。
……
前方是一片森林。我又一次穿过了,用去了七分之一的力气。
前方是一片森林。我第七次穿过了,用去了最后七分之一的力气。
……
终于,前方不再有森林。
我遇到了沼泽,在我消耗了所有的力气之后。
“诗人与狗不得入内
——XXX宣”
我看到了这样一个牌子,就挂在那片沼泽的边缘的一棵枯树上。也许那不是一棵枯树,很像挂牌人为了立此警示顺手插的一根枯枝。旁边地上还有一只鞋,鞋的大部分伸进了沼泽里。可以断定:曾经有一位眼睛高度近视的同志为了看牌子不得不留下了它。至于另一只鞋和人去了哪里,就无从考证了。
身后是一片片森林,眼前是一片沼泽。
透过沼泽,依稀可以看到城市的烟火。
我犹豫了。时间在一点一点融化着我的生命。我不敢回头,也没有力气回头,更缺乏向前走的勇气。
就这样,我与自己僵持着。
过了许久。我的身体在恢复,眼前也比许久前清晰了好多。
是的,我开始向前走。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这片沼泽的路程要比身后的路程近好多。而且我也不是诗人。至于是不是狗,我就不知道了。很显然,标准不一样,答案也是不一样的。
我向前走着,踩着别人与别狗留下的脚印和爪印。我也开始后悔——我不该选择向前,我低估了向前的困难和危险。泥泞不堪的沼泽地需要我付出比回头更多的力气。我知道是人的贱性和惰性害了我。我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喘很粗的气。
此时此刻,我只能向前走。周围都是沼泽,还有人和狗的尸体。
西山上,那随时都可能消失的如血的残阳,让我感到了恐惧。四周没有一点生气。
我向前走着,踩着别人与别狗的尸体。我也开始疑惑——我看到了叶塞宁、顾成、海子……几乎所有的诗人,还有一只只啸天犬。我的身体开始发凉,冰冷的就像一具尸体。我继续走着,麻木的走着。
此时此刻,我只能向前走。周围都是尸体,还有灵魂和沼泽。
西山上,那已经消逝的残阳,惨白惨白的,让我感到了绝望。空气里没有了一点血色。
走着,走着,
……
眼前一片漆黑。
城里的教堂里传来了叔本华的***:
“人生是痛苦的!”
酝酿一个人的思绪作文【五】
起风了呢。我悄悄地想。
姥姥在不远处散着步,调皮的风划过她的身侧,吹起那下垂的衣摆。一旁的妈妈一手扶着姥姥,一手拎着包,侧着头,和姥姥聊着生活中的.琐事。年幼的弟弟天真无邪,无所顾忌,不管不顾脚下坑坑洼洼的土地,一会儿向前跑去,一会儿又跑了回来。随手摘下一颗蒲公英,风一吹,蒲公英种子潇洒地散在空中,抬手去捉,却只得来一手虚无。
我感受着吹起的风,风吹得很长,长到天际,长到我看不见的地方。风吹得很久,久到过了几个世纪,穿过了弟弟烂漫的笑容,穿过了姥姥深深的皱纹,穿过了我整个生命。
那边年老的是我的姥姥,那边成长的是我的弟弟,风穿过人群,与我们相遇,风穿过万古千愁,与我们举杯饮酒。我们在风的陪伴中成长,我们在风的陪伴中老去。我们在风的离歌中思念,我们在风的疯狂中疯狂。
突然,弟弟大叫一声:“我抓到了。”
思绪拽回,我微微一笑,起风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