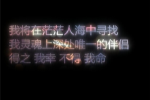作文家的摇篮【一】
那天,已经退休的哥打来电话,估计喝了点酒,声音有几分悲怆:我给你说,妈说有一天从椅子上站起来,晕病又犯了,两眼一黑,屋顶子乱转,倒在火塘旁,叫不见人,好久好久才爬起来,幸好没有烫着……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母亲八十九岁了。当我出生的时候,她已人到中年。我没能走过母亲的青春,我一长大,她就老了。我竟然连她的中年也不能守住!不管我多么想,我总是握不住满手的时光沙子,只能无奈地任它沙沙而去,而我却像一片落叶,在这细微却清晰的沙沙声里越飘越远。
妻在一旁黯然抹泪。我不禁哽咽,不住地对着电话絮喃:想办法,想办法。
摇摇晃晃的母亲
细心的二哥从武当山买回一根拐杖的时候,我们兄弟才突然间发现,母亲走路的姿势已经不似先前那般矫健了。母亲自己也是一个激灵,说:嗨,买这个做什么?给我放到门后面去吧!
母亲对我们的发现有几分恼火,也有几分慌张。她开始故意大声地说话:老二,你把这些茄子广椒带走,还带一口袋洋芋;老五,我去给你取一块腊肉烧了带上;老幺,你喜欢吃炕洋芋,这些小洋芋你就带走,一个也不留……,语气坚定,不容商量。她故意地加快脚步走路,缠过几天足的步子分明有些蹒跚,有时甚至会有个迾蹶,但她总会尽量地保持住重心,一边平稳住一边很不耐烦地挡开我们惊慌的手臂。逢年过节,她号召其实就是强令地把大家召集到一起,顽固地坚持为一大家子人安排生活,媳妇儿几妯娌们只好挤在她那并不宽敞的灶台周围帮忙拾掇,互相间窃窃私笑。那根拐杖,更是被她打入冷宫,我们有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没有看到它。
我知道,母亲这是在恼恨着不听使唤的光阴,如同当年恼火调皮捣蛋的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加以提醒一样。她凭着一生柴米油盐的经验,已经准确地嗅到了这光阴里有些发霉的味道,必须折腾着晒它一晒,才能装进生命的口袋里更好地贮存。
母亲生养了六个儿子,因为没有养一个女儿遗憾了一辈子。慢慢地,她的思想里,在身边结婚、分家、独立的三个儿子才是儿子,在外工作生活的儿子其实就是女儿。我们每次回家,母亲就以老家惯用的迎接女儿回娘家的极高规格温暖我们,让我们觉得很是对不起老家的三兄弟。无论怎样,那三兄弟,特别是同屋就里的老四,才是真正能够在风雨里第一个出现在母亲面前的人。只要我们不回避,她会絮絮叨叨地讲上一宿一宿地贴心话儿,都是些她满意或不满意的一些人和事,我们不需要附和评论,只需在一旁偶尔答应一声就行。因为我们不常在她身边,十分遗憾地无法像她温暖我们长大那样温暖她步入年老的路程,等我们突然发现她走路有些摇摇晃晃的时候,我们吓了一跳,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
终于有一年春节,我们几弟兄再无可忍,聚在一起商量如何确保母亲安全养老的问题。母亲发现了我们的图谋,晃晃悠悠地踱到跟前,沉吟良久,开出了条件:一不进城,二不跟哪个儿子一起过。她曾经在我工作过的县城家里玩了一个月,那里没有菜园子伺弄,也没有柴火灶表现,就很慌张和茫然,甚至双腿闲得发肿,最后逼着我送她回去,从此对城没有好印象。我一个人开烟火,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我们知道,智慧的母亲又在为孩子们着想,有什么事能瞒得过母亲呢?我们妥协,但坚持要在老四的正屋旁做一偏屋,就一个屋檐。随后她就近钦定了一方园田,一块柴山,老四家屋顶就升起了又一柱炊烟。
亲情流淌的艰难岁月
在那段亲情流淌的艰难岁月里,我们的父亲因病离开了我们。我们弟兄六个,还有三个尚未成年。弥留之际,父亲把我们兄弟六个叫到一起,对母亲说:这三个小的,由三个大的一个人负责养活一个,你要把自己照顾好罗,我不行了,我要走了……兄弟们呜咽成一团,母亲更是几近晕厥。
我深刻地记得,在父亲临走的那天,他把我叫到床前拉到床上,在他怀里喂我吃他最后希望吃到食物——糯米米酒。在那个缺衣少吃的年代,被那个时代不怎么待见的四类分子的老婆也就是我母亲,为生病的父亲弄到一口纯粹的糯米米酒是相当不容易的。那时的我刚记事不懂事,吃完了父亲的糯米米酒,他搂抱了我好一会儿,说:你玩去吧,莫跑远了,叫你的妈来。我就真的一溜烟的去了……等人把我唤回来的时候,我被母亲的悲天怆地吓得傻愣愣的哭,看得帮忙的乡里乡亲一个一个地掩面叹息。
坚强的母亲埋了父亲,送走了帮忙、慰问的最后一批亲朋。她再也没哭,带领我们兄弟将房屋院落清扫得焕然一新。多年以后我总在想,当时的母亲一定是不想让孩子们悲悲戚戚,惶惶终日,形势不允许她过多的悲伤,她要带领我们继续过日子,而且要过上好日子。在后来的日子里,母亲没有遵循父亲的遗言让三个大的孩子每人抚养一个小的,而是独自扛起了家的责任。是啊,十指连心,怎堪分离,我可亲可敬、可歌可泣的母亲!
一九八八年,我考取了省城的大学,母亲颤抖着双手清理出她卖木瓜攒下的毛角钱装进我的衣袋,那时的木瓜不值钱,一共才两块。在她背转身去抹眼泪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她的背有些佝偻了,她的头发已星雪斑驳了。四哥在猪圈里往田里出肥,也是一耙一声叹息。彼时已经成家的'大哥三哥正是拖儿带女的时候,在县城居住的二哥情况稍好,但也有自家难念的经。周围相邻伸出了援助的双手,你一块他两块地帮凑了四十多块。我到县城后,二哥给我做了两套衣服,并另外给了50元现金,我就独自搭上了去省城的班车。自此,母亲那双拿着两块毛角钱的皮肤皲裂的手,和她佝偻着转身抹泪的身影,一路温暖激励了我人生几十年。
我们家的生活状况在母亲的带领、坚持和努力下,终于一天一天地好转起来。只是岁月无情,韶华难留。就在孩子们在她的灶台烟火间一个一个长大,成家,独立,昂首而去的时候,母亲的窈窕身躯却慢慢地,慢慢地匍匐到了一根拐杖的身上……
她拄起了拐杖
当我们惊讶地发现她双手拄杖的时候,是她在夕阳下的道场边望我们归来。记得那个冬日的阳光很薄,她的身子佝偻得几乎是匍匐在紧握拐杖的双手上,白发在光影里闪着金光。看见我们的车子驶来,她似乎有些紧张,踌躇着往前挪了几步,脸上漾着孩童般天真讨好的笑容。哥问:拐杖还好使吧?母亲嗫嚅着:好,蛮好。像个犯了错的孩子。我发现,这时候的母亲,眼神居然清澈了许多,目光 里充满了一些感受得到却又不好猜透的期盼,笑容里甚至有了几分羞涩和慌张。
今年的年饭我就不弄了,母亲说。但是你们得叫她们几妯娌在我的灶上生火,烘我的肉,煮我的米,小菜我园子里都有,酒在后面墙根下,喝多少提多少……。嗨!瞧你们说得轻巧!那怎么行?这么多东西留这儿,我一个人怎么消受得完?不吃就抛撒(浪费)哒,大家伙儿帮忙捧着吃……。这个事儿就不多说了,就在我这儿弄,可以端到老四堂屋里吃,叫他们几家都来,团了这个年她们几妯娌好各走各的娘屋去。再不能往下说了,再说恐怕她就要委屈得生气了,我们慌忙应允,督促老四媳妇儿把取下来的腊肉又挂回去。
老幺啊,我这身子骨儿不皮实了,走不了多远的地,晴天就在周围磨一磨,要是天阴下雨,这椅子坐得我屁股疼。我就搂着她,摸她背上的皮肉。她很听话,笑着闹:痒死了,痒死了!我眼眶一热。她瘦了,已摸不见多少肉,只有一把温热的皮肤在她的骨架子和我的手指间缓缓游动。妻说我们到宜昌看看吧,看能不能买一个正好一放有软垫子的椅子。终于买回一件,母亲高兴地坐上去,说:好像你家家(外婆)当年那个木桶椅啊,真好,真好。我外婆家曾有一把椅子,是用一整根木材雕挖而成的,铺上一层薄棉絮,柔软温馨。外婆在的时候我还小,要是去了她家就一准儿霸占了她的宝座。母亲由此就思念起了她的母亲,给我讲一些她小时候和家家的一些日常事儿,我才知道,家家那把木桶椅不仅仅是零散着我儿时的一些淘气片段,更是盛装了母亲整个的青春岁月和无限思念。倘或那把椅子还在,我一定会为她寻回来。
后来她又说:老幺啊,我这身子越发懒得动了,坐在这里很屈人,看不见外面,站起来走动吧,又有些头晕,大白天的也不能总睡觉,要是有一把椅子放在门口那儿,新鲜的时候可以坐,倦了躺一觉就蛮好了。我又和妻回了一趟宜昌,到家私城买了一把藤制躺椅,朋友热心,比着尺寸帮忙做了棉絮的垫子和盖被,一并送回去。母亲躺上去,唠叨:我老了,什么事也做不了啦,尽享你们的干福。我就用双手摩挲着她的手,默默地用我的体温安慰和温暖她,直到她沉沉睡去。她的手腕处有一块骨头畸形的崛起。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她想给我炒一碗油盐饭,在楼梁上割肉的时候凳子失去平衡摔了的缘故。出事的时候,我还没放学,我大嫂说母亲在医生来之前恸嚎了半天。那时的医疗条件有限,母亲的手腕也就长成了这块崛起的畸形的骨头。
母亲怎么变得这么乖巧了?这还是我那个叱咤风云、遮天避雨的母亲么?现在,母亲的每一个愿望都很小很小,可要说出来她自己却觉得很大很大,生怕一不小心就吓着了她的孩子们。我在和她的交流中发现,她的世界其实已经很简单很简单,简单到只要自己还能做一口饭,还能和孩子们说一句话,还能自己起床穿衣关灯睡觉,还能在那把躺椅上看外面的春风细雨、秋风落叶……。
你怎可轻易老去
我们不能让母亲就此灰暗下去,她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她往后的生活,不能随随便便地简化为一段时光,而要保持一种静水深流的姿势,在平静的水面下,有幽幽暗流,有鱼虾跃动。只要有些微的波动,这团水就会光阴温婉,岁月有痕。我相信我的母亲,她一定能行。
你想想,母亲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把我们一个一个养育成人:带领老大、老三、老四修了三幢大瓦房,接了三房的媳妇儿;撵着我们上学读书,让老二、老五、老幺也就是我走出山寨,谋到了体面地生计。而今,她有嫡亲孙辈十个,嫡亲重孙辈也已有了七个。这样一个功底深厚的母亲,怎么会轻易地老去?我们决心鼓励她,帮助她守住她的优秀,激活她自动掩藏的能量,让她的身子尽量活泛起来,让她的脑子更好的运转起来,一起拽住那沙沙流逝的光阴。
她的屋子很小,只有两间。前面一间稍大,是做饭的厨房,并置一火塘取暖;后面一间稍小,是她的寝室。老五给她牵了电线,在门口、灶台、火塘、床头安了电灯。母亲过去从来都是点油灯,为此她很高兴,就是为了分不清楚土墙上一排四个灯闸而常开错灯有些烦恼。特别是床头灯的手闸和外面墙上的拉闸串联着,经常忘了究竟是哪个开了哪个没开,反复捣鼓就是亮不了灯。当然,这都是我们不仔细,没有提醒老五同志的后果。有很多次,我发现母亲有事没事地盯着那一排闸阀看着,时而扯扯这根拉线,啪嗒一声,看一看灯泡;时而又扯一扯那根拉线,啪嗒一声,再看一看灯泡。最后她终于找到床头灯那根拉线,拉开了将之束之高处,从此干脆直接到寝室开手闸。母亲很兴奋,将这事儿作为一项重大成绩向我们汇报,并当着我们的面准确地拉亮每一颗灯泡。
时光推移,母亲胳臂的力量越来越小,生火做饭慢慢有了些困难。我们一商量,给她买了个电磁炉回去。母亲不识字,盯着电磁炉上那一排触摸按钮就发懵。她说:你们还是拿回去吧,这个东西我怎么会用?我故意激她:这个东西千把块钱,您要不用,我拿回去也没用,那就送人呗。您看给谁好?千把块钱?!母亲显然被唬住了,她摩挲这个宝贝物件儿,连连说:你教我试试!饭前,我和妻反反复复地叫她死记哪些按钮,一顿饭后,她又搞混了。她看着我,怯怯地笑,我忍俊不禁,遂又叫她数遍。一盏茶后,她又搞混了,我抱抱她,再教数遍。我们回江城后,起初打电话询问,说她还是在柴火做饭,不会用那个电磁炉,我好不郁闷。突然有一天,她在电话里告诉我:那个电炉子真的方便,一按,就可以炒菜;再一按,就可以煮饭;又一按,就可以烧水,真是太好使了。她在电话那头眉飞色舞,我在电话这头心花怒放。晚间自斟自饮,半天才得意地告诉丈二摸不着头脑的妻这件畅快事儿。
简简单单的母亲可以有学习,也会有进步,更需要表扬。农耕里成长并老去的母亲,在电子社会里生存,在我们看来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儿,于她而言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一门学问。我很开心母亲在她的新进步里沾沾自喜,她终于又有了走远一点距离和他人分享喜悦的勇气和力量。
鉴证又一个轮回
快点,快点,快点拿来我穿上。母亲急促地说。不急,不急,还早呢。我说。妻在一旁帮她拾掇衣服。都这时候了,我都听见戏班子唱歌了。那也不急,这走过去也要不了多久。
侄子结婚,我作为长辈,理所当然要回去享受坐上席的尊荣。我电话母亲,问她需要些啥。其实这是例行公事,每次问她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什么都不差,你们回来就行。可这次太阳打西边出了,她居然说:你给我买一个新帽子,一件新上衣吧,颜色一定要亮一些。我一下子懵了,母亲有多久没有主动给我们提过要求啦?而且颜色还要亮一些。人就是这样,惯式思维突然被打破,一下子总是难以回神。我很好奇,我家的老顽童这是要整哪一出啊?妻说:我懂了,这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包老娘满意。
在母亲的催促下,我们一起手脚慌乱的帮她收拾停当。我把随身的包斜挎在背后,对妻指手画脚道:你赶紧喝口水吧,该准备些什么就准备些什么,妈急了。她腿脚不便,我们一起搀扶她,真走到还得要一会。妻只顾好笑,示意我转身。我了个天!母亲直奔车子去了。我叫唤:妈,妈,你慢点儿,小心摔着,您的拐杖忘啦!我又阻止:妈,我们还是走吧,不急,您千万莫坐车,这坐一回我们得伺候几个星期。
那天,妻上街转悠了一晚上,拎回一大口袋。一顶老年款式的暗红色帽子,一件带有暗花的老红对襟毛线外套,一条泥黄色裤子,一双微红面子的步鞋。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不是要把我的母亲打扮成老妖精么?妻说你不懂。问我:你回去干啥?我回去参加侄子的婚礼啊。你侄子是你老娘的什么人?是她的孙子啊。这不就结了?!我猛然惊醒,母亲这是要非常隆重地去出席她孙子的婚礼!好久好久,母亲都没有走出门口那一块道场的志向了,她常年在她的三尺天地里,从床上到座椅上,从座椅上到躺椅上,最多也就从躺椅上起身,拄着拐杖顺着屋子周边走走。这次,她居然决定重出江湖了。
我看着母亲在前面人丛里坐着,那一身恰到好处的红把她衬托出了几分娇艳。她乐呵呵地接受着周围人们“老祖宗真有福气”的赞美和祝福,兴致盎然地看着台子上的大戏。那份走过千山万水后的沉稳和坐定江山后的满足,是因为她隆重地鉴证了孙子接过了儿子手里的接力棒。她神定气闲地看到,她的生命又有了一次鲜活的轮回。
这次她居然没晕车。她的最小的孙女守在旁边,替她拿着她的拐杖。
后记
在这个思念绵长的秋天,我远方的母亲,突然地就发了晕病,就倒在了火塘边,过了好久好久她才爬起来。
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忧伤和无奈的人生轮回啊!当初,我们在母亲的希望里来到她的摇篮,一天一天变得强大,母亲听我们拔节的声音就如听一首美妙天籁;即或是在那 些老井干渴得余水掩不住枯裂泥土的灾荒岁月,她依然能够在锅碗瓢盆的交响里撑起一家人消瘦的幸福;而今,母亲已经只能在我们的摇篮里辗转,可无论我们怎样小心呵护,她却像一片秋天的叶子,在枝头晃晃悠悠,那么让人揪心。
想办法,想办法。突然地思绪卡壳让我不能组织更多的语言,我反反复复地重复着这简单的词汇,安慰着我的老哥哥。是的,必须想办法。人到中年,回到家老远就可以叫一声母亲,老远就可以听一声母亲的答应,是多么温馨幸福的事情?可我却因为工作,不得不离她越来越远,想想我又十分的遗憾和伤心。
我知道,母亲是不会进城的,这是她的原则和信念,人已中年的我是能够理解她的。那朝夕相守、一草一木已融入她的灵魂的故土,早就是她的一根精神拐杖。丢掉了手里的拐杖,她或者还可以爬起来;倘或丢掉了精神的拐杖,她往后的日子就只不过会是一个投入巷道深处的影子,里面一定会空无一物,那样,母亲和我们都会更加惶然和忧伤。
我想起了一个好友,一个我在乡下工作时结交的朋友。我曾在家乡的一个高山乡镇工作,那里有一种冬天取暖的火炉,柴火生在炉膛内,外面不见明火。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帮我订做一个……外面要用刨得光园润滑的木头做个花栏格的框子罩着,保证炉身烫不到人……框子帮忙用厚布缠一缠……。
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拿起电话:喂,伙计,深秋了,你要快点儿啊……好了就给我电话……拜托……!
作文家的摇篮【二】
“睡吧——宝宝!睡吧——宝宝!快睡吧——我的宝宝!”今年,我9岁了,当我每天上床睡觉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妈妈唱的这首摇篮曲。
妈妈给了我生命和无尽的爱,我由衷的感谢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教会我读书写字。使我在知识的海洋里,像小鱼一样遨游。在智慧的天空中,像小鸟一样飞翔。她教育我要诚实,要有爱心。我爱妈妈胜过一切。
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浑身难受,爸爸还出差不在家,妈妈对我百般关爱,嘘寒问暖。整夜守候在我身边,用酒精给我擦身体降温。那时正是三伏天,妈妈忙得满头大汗,我心痛的对妈妈说:“妈妈,你睡一会吧!我好多了。”妈妈毫不在乎的说:“我不困,宝宝只要你快些好,妈妈累点苦点都没关系。“我感激地望着妈妈说:“妈妈我难受了。你还是休息一会吧。”妈妈笑着对我说:“太好了,我们终于战胜了病魔。睡觉吧。”妈妈轻抚着我的头,为我唱起摇篮曲,我甜甜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看到妈妈面容憔悴,疲惫不堪地样子我好心痛。
妈妈,我爱您,我一定好好读书不辜负您的爱,我庆幸有你这样的好妈妈!
作文家的摇篮【三】
一首催眠曲: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题记
早上6点,不知怎么的,自然地睁开了双眼。扭头向窗户望去,清晨柔和淡淡的雾轻轻地贴在窗户上,自然得让人不忍心擦掉,雨滴不规律地与雾气融在一起,好似一副美丽的工艺画。“下雨了?”我站起身,离开温暖的被窝,向窗前走去。
小心翼翼地打开窗户,终究被雨的机灵所打败,它淘气地钻了进来,一滴,两滴,三滴像跳着华尔兹一样“滴滴答答”地落在我的头上,手上,脖子上。我仰面朝上,闭着眼品味着这一滴滴来自大自然的甘露,顿时,仿佛觉得自己在雨水的滋润下有成长了许多。我仰头睁开眼,欣赏着这雨中的天空,不必再为阳光刺眼而担心。天是灰灰的,却因雾的蔓延着的轻纱遮住了天空忧伤的灰色,它变白了,白得模糊,令人仿佛觉得天不再是天,而是包裹着城市的雾。雨点互相牵手,不留一丝空隙,像一张大网伴随着乐曲立在我的眼前。雨“啪啪”地落在大楼上,顺着楼层,像正在坐滑梯的孩子一样,极速地欢乐。比建筑矮了许多的树木,此时在我的视线里被雨洗后绿得模糊,模糊得优雅。人们撑着花花绿绿的伞,在被建筑隔开的街道间,像一条条流动的彩虹,穿梭在这个小城。
大网开始稀疏起来,半小时后,雨停了,雾也收场了,天空便白得那么清晰,一尘不染。像小时候图画本上用蜡笔画的被加工又很自然的白色天空。建筑不再被雾保护着,笔直、清晰地展现它的轮廓。雨滴正在一点一点地减少,但之前落在树叶和树枝的水滴再也按捺不住,开始跳到地面,一个顽皮的孩子似乎很讨厌雨天,便一脚踢在树木上。霎时间,雨滴全齐刷刷地落下来,在下一场属于它自己的小雨,行人间的彩虹消失了,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收了伞,各做各的事,一切又恢复了从前那样。
在天恢复金色,城市变回喧闹之前,我笑着走回床边,倒在床上,享受着这片短暂的宁静,安心地闭上眼。伴随着那场雨给我的风景催眠曲进入梦乡,吮吸着雨后泥土的清香,睡得很熟,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