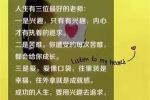美好生活满分作文400字【一】
茂盛的树阴下,知了在欢快地唱着歌,我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切,感觉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的美好生活。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乡下,什么都不知道的我,到了那里,竟然被一种自然的景色吸引住了,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了什么是一种自然的美。
一个个小草房虽然简单,破陋,但它却是温暖的,因为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纯朴的,善良的。
一块块四季翠绿的菜园,是农民用劳苦换来的,金黄的油菜花谢了,结出了密密的嫩荚;黑白相间的蚕豆花谢了,长出了小指头似的豆荚;雪白的萝卜花谢了,结出了一蓬蓬的种子。这一块块菜地有了农民们的关爱,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是一片诱人的翠绿。展示着一种自然的和谐之美。
每当太阳落下山后,在微风中,一缕红霞照耀着乡村的时候,农民就会把饭菜搬到门前,天高地阔地吃起来,有说有笑。一幅其乐融融的样子。
吃过晚饭,他们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即使空中的鸟儿从他们头顶上飞过,这些善良的村民也不会伤害它们。
到了晚上,大自然有音乐家——蝉就会唱起一首美妙的歌,那歌声清脆悦耳,胜过摇篮曲,让那些忙了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
茂盛的树阴投下一片片暗绿。那只知了可能也没有原本活泼,但是它在我心中永远最活泼、可爱。因为它让我回忆起了去乡下时的快乐时光。我爱它。
美好生活满分作文400字【二】
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农户人家行乞,女主人叫他先将门前的一堆砖搬到院子后。
乞丐生气地对女主人说:“你明明看到我只有一只手,却让我搬砖头,这不是存心捉弄人吗?”
没想到女主人自己蹲下来,故意用一只手搬起砖头,来回走了一趟,然后对乞丐说:“我一只手能搬,你一只手为什么就不能搬?”
乞丐无言以对,硬着头皮用他那一只手慢慢搬,整整干了两个小时才搬完,累得满头大汗。
农妇递给他一条白毛巾,乞丐擦完脸和脖子后,白毛巾变成黑毛巾。
农妇又给他二十元钱,乞丐接过钱连声道谢。
农妇说:“你不用谢我,这是你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工钱。”
乞丐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请你把这条毛巾留给我作纪念。”
过了若干年后,这位乞丐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再次来到这家农户,见到年迈的女主人动情地说:
“我从前是乞丐,现在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是你帮助我找回失去的尊严,重建生活的`信心,如果没有你,我也许还在四处流浪。”
农妇说:“这造你自己干出来的。”
独臂董事长提出送一幢楼给农妇,农妇碗言谢绝。
董事长对此不解,农妇笑着说:“因为我全家人都有一双手。”
人要活得有尊严,尊重自己、尊严我们认识的人,还要尊重我们不认识的人。
从自己的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
做自己喜欢的事,虽则赚钱不多,但比起很多有钱却心灵失落人,更值得敬佩。
美好生活满分作文400字【三】
没有蓝天的旷远,可以有白云的飘逸;没有江海的奔腾,可以有溪流的秀美;没有红花的耀眼,可以有绿叶的`悠然。
选择壮阔?选择显贵?选择平静?或是选择隐退?不如选择诗意地生活。
诗意地生活,是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篷蒿人”的桀骜,是王维既知“都护来燕然”,还有心品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旷达,还是听凭“云卷云舒”的闲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诗人一样记录美好的生活,但每个人都有权诗意地生活。
黑暗选择了她,她却选择诗意地生活,她用心体验大自然赋予她的一切,她用情为自己黑暗的世界画上太阳,画上彩虹,更用毅力充实着自己的智慧,完善着自己的人生,她甚至还可以笑着写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她诗意地生活着,享受着,更收获着,她的名字叫海伦凯勒。
财富选择了他,他却选择诗意地生活,他总是穿着古补的中山装,提着文具袋徜徉于燕园,他所追求的只是学术,功名利禄与他无关,富贵荣华也不能吸引他,他只爱看看北大的花花草草,爱看看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他是文学界的“常青树”,他的名字叫季羡林。
“丑陋”选择了她,她却选择了诗意地生活,她的脸是一张“奇怪”的脸,眼睛小得只是道缝,鼻子塌得仿佛容不下空气,而且是张“倒瓜子”,她乐观对自己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她乐观地欣赏着自己的独特,用内涵完美自己的人生,活在当下,她的名字叫吕燕。
诗意地生活,让人们体验自由,无拘无束地遨游于纷繁的世界。
诗意地生活,是对自己的肯定,是看遍人生的大起大落,处变不惊的淡定与从容。
诗意地生活,是对自己
诗意地生活,是对自己的褒奖,是在疲劳的奔波后,选择悠闲的方式体验轻松与自在。
诗意地生活,更是勇敢的体现,不为利禄所羁绊,只为寻得心灵的享受,超然世外。
选择诗意地生活,选择精彩的人生。
美好生活满分作文400字【四】
日子长长短短,一晃竟过了十数年。而那些温婉静好的时光,却在记忆里如初盛开,不谢朝暮,让我懂得往事并不如烟,旧日的风筝不曾断线。
那些好时光,你我曾共度,共享,共徜徉。
尚记得好时光里,戴着花料肚兜,连走路都是一摇三晃似的,我却依然乐此不疲地甘心做你的跟屁虫;蝴蝶、花草和吵闹的街市在眼前晃过,我却只顾寻觅你日渐苍蚀的背影;三岁时父母把我寄养在你家一个暑假,待他们来接我时,我却骄傲地躲进你的怀抱,扯着你的衣角向啼笑皆非的父母介绍:“这是我姥爷。”
五岁时,你让我住在你家,雕花大木桌如你的手掌般结实有力,老电视机旁的水仙长势喜人,温和而多情。在我作为一个孩童的记忆里,印象里你总是起得很早,等我睡眼朦胧从床上爬起,撒着葱末的豆腐脑和酥脆的油条已然在桌上撒发着幽微的热气,而你心满意足地坐在沙发上看报,待我故意攀到你的膝盖上把你陷入报纸的兴致打断时,你便用双手托起我,让我感到兴奋与高处的晕眩,再乐呵呵地把我放下,看我像小猫一样溜走;你总是充满暖意,陪我乐此不疲地玩些幼稚的把戏,我咯咯地笑,你也幸福地眉眼弯弯;你也总是那么稳妥,长时间不发一语,有种不经意的深沉,我却愿意时时缠着你,抚摸挂在床边的你买的地图,懵懂而认真地听你讲福建和台湾,你捧着我站在窗台,不厌其烦地教我指认这两个地名,当我有些迷茫却终于肯记读下来,你便高兴地向家人宣布这个“令人十足振奋的消息”,手舞足蹈像个孩子。
或者说,在那段去而不返的好时光里,你陪我,又成了一回孩子。
如若好时光如石砾般俯拾皆是,怀念或许便不会那么意味深长。年华白驹过隙,我还在愿与你共度好时光的甜梦里,你却终于在我的年华里缺席。
八岁那年,你病倒,近麦的肤色愈发黝黑,我在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依旧不知实情的傻玩,以为那白色肃穆的地方只是你暂留的场所,以为大人脸上充满哀愁的神情只是烟火一现过往云烟,以为我依旧可以挽着你的`手,走过长长的巷子与街市……
而终究还是我错了。过往的不是伤痛而是你的生命,当母亲哽咽着告诉我你已不在,我依然没有理解其中悲恸的意义——不在,既永别。
年华岁岁更迭,转眼你已离开十一年,而与那段好时光一起消失在时间深处的,还有我侬软细语地称呼“姥爷”的资格。我终于知道了那个手掌宽阔,温和安详的你不会再推开家门唤我的乳名,我终于了解了我们血液里包含着怎样一种亲近;而你虽未等到我的青春年月,却在你生命的尾音、我人生的序曲谱下最强乐音;你,虽化作一颗天边的远星,却时时照亮我,让我懂得“好时光”的定义,留给我余生去回味、思量。
好时光,亲情长,与你同在。
美好生活满分作文400字【五】
——题记
蚂蚁,一种很微小的生物。
蚂蚁真的很小。与我们这些庞然大物般的人类相比,它们真的很小很小。那些我们一口气就能吹好远的食物屑,可能很多蚂蚁才能搬走,那些对于我们都不够塞牙缝的食物,可能是一群蚂蚁很长时间的粮食。
蚂蚁,一群强大的生物。
蚂蚁,能搬动相当于本身几十倍的食物,若我们以自身重量相比搬动物体重量的话,蚂蚁绝对是大力士。
蚂蚁,能搬动相当于本身几十倍的食物。若我们以自身重量相比搬动物体重量的话,蚂蚁绝对是大力士。
蚂蚁,一群分工明确的生物。
在蚂蚁社会中,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制度:蚁后只负责产卵,享受着最好待遇,雄蚁承担着很少的工作,享受着较次于蚁后的'待遇;工蚁每天辛勤工作,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待遇却是最差的,很不公平,但不由得不说分工真的是很明确,每只蚂蚁对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份及其所承担的责任。
蚂蚁,一群无私奉献的生物。
在野外,当一群蚂蚁遇到火灾的时候,他们会很迅速地围成一个球:蚁后在中心,雄蚁则在蚁后四周,外面那黑压压的全是工蚁!在组成球后,它们会迅速做出判断,从火势最小的地方迅速突围,突围后落在水上的“蚁球”仍保持原来的形状,多的是那水面升起的阵阵水汽。
……
蚂蚁虽然很渺小,“天生我才,先别怨沧桑,弱水身躯斗志顽强,坚持也许能滴水石穿”看到自己的价值,顽强地、坚忍的挺过困难,美好的生活也许就在不远处向你招手。
“强者强在执著梦想”,即使拼尽全力,也要为梦想迈进,就像工蚁奋不顾身保护同类那样,蚂蚁般地生活吧,那会让你的生活更加清彩,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