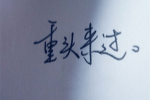秋天思念人的作文【一】
落叶迎着秋风慢慢飘落,是那么的缓慢,那么的宁静,犹如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只有那片落叶,那份对亲人的思念,在空中飞舞,在空中盘旋。
记得前两年,外公因一些事情,离开我,回到了外婆家,虽然外婆家不远,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但因为平时上课,周末还有一堆的兴趣班和作业,所以每次都只能爸爸妈妈回去,再带去一些我想送给外公外婆的东西,但却见不到他们一眼。
每一次看到外公的照片,看到他那带着岁月痕迹的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我就不经想起了那些年快乐的时光。记得那时我才幼儿园,整天拉着外公的大手向公园走去,嚷着要吃棒棒糖,每当外公从背后魔法般地变出一颗棒棒糖,我都高兴的扑向外公的`怀里,拿着棒棒糖,说道:“外公最好了!”
说完就一蹦一跳地跑到了秋千上,外公从后面轻轻一推,我就感觉自己像在飞一样,带着外公一起飞向那遥远的地方,一个无人荒岛,快乐地嬉戏、玩耍。纯真的我,并没有想到过终有一天,外公将离我而去。
上了小学,外公每天站在校门口等我放学,不论刮风下雨,都是那么的准时,从不晚来,每次一到听写的时候,我就叫到:“外公,外公,听写,外公,听写,”外公都会拖着他那老态龙钟的身躯,走过来说:“遵命,长官”然后一同哈哈大笑。
晚上,因为屋子太黑,风从窗口吹了进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最后我都会抱着我的玩偶,边哭边喊着外公,跑到外公的房间,最后在外公温暖的怀抱中安心的睡去。
现在,外公走了,在外公走的那天,正下着大雨,站在学校门前的我,看着外公迟迟不来,心里既害怕又着急,最后,妈妈把我接回了家,当听到妈妈说:“外公走了。”我犹如晴天霹雳,跳下车,看着外公的车在我的眼前慢慢消失,突然我嚎啕大哭,最后趴在外公的床上慢慢睡着了。
以后,每当我遇到要听写的作业,会不由自主的叫一声:“外公,听写。”可房间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回答。来到外公的房间一看,在也没有那张我熟悉的脸。
岁月如梭:一晃眼两年过去了,但我对外公的思念还是没有淡化,就像落叶一样,在空中久久盘旋,在我脑海深处不停地徘徊,久久不能忘怀……
秋天思念人的作文【二】
“曾祖母,曾祖母,你起来,你起来带我去摘槐花、挖红薯,你起来呀!”
曾记得,每年初夏时,我来到您家,缠着您带我去摘槐花。我带个小草帽,拉着您的手,走在纵横交错的羊肠小径,望着两边被风吹抚的绿色麦浪,问“曾祖母,槐树在哪呢?”“在太阳下面。”您爱怜地看着我,微笑着说。我松开您的手,蹦蹦跳跳地向着太阳跑。突然,我看见一大株如女孩一样亭立,如嘴唇一样红艳的花朵,我不由地喜欢上了,我站在原地不走了。您看着我一直望着那些花,便放下小皮篮,蹒跚地走到河边,用手慢慢地勾来一根花枝,小心翼翼地摘了两朵花,轻轻地将花插在我的小草帽上。“成了花丫头!”您用瘦弱的手轻抚我的头,笑着说,“真好看!”那时,您的银发在风中飞舞。
终于看见了槐树,我迅速地爬上了大树,您站在树下,不停地叮嘱:“慢慢地,慢慢地。”我爬到哪,您的手就接到哪,原来我以为您是在接槐花,当我看见满地落花您却一个也没拣时,我才知道您接的是我!
秋天来了,梧桐叶一片又一片地落了下来,我骑着自行车,“噔噔”跑到您家,“曾祖母,我来了。”“哎呦,小宝贝来了,走,我们一起去挖红薯去!”您拿着铲子,我拿着麻袋边走边“呀呀”唱着不着调的歌,您哼起童谣:“小胖孩,煮干饭,小狗吃,小猫看,急的老鼠啃锅沿。”微风一吹,树叶也赶来听歌谣。来到地里,我扯红薯秧,您挖红薯,“一个,两个……哇!曾祖母,这个好大呀!今天我就吃它!”“好,好,你去把红薯装进袋子里,我们就回家烧红薯!”傍晚,火红的夕阳下,谷物飘香,伴着鸟儿归巢,一位老人背上背着一小袋红薯,手里牵着一个顽皮的孩童,构成了一副美丽的乡村晚景图。
燕子南飞,树叶飘零。秋天又到了,却没有了您与我的欢笑,只有我的哭泣,望着一片片飘飞的落叶,我不禁想问:“叶子呀叶子,你是在陪着我曾祖母去旅行吗?我相信每一个跟曾祖母在一起的人都是最幸福的人!”
秋天思念人的作文【三】
和东四的孙大姐通电话。孙大姐是居委会的,在编本地的一本志书,希望用我的一篇稿子。孙大姐这人我没见过,但话里听得出来,一提几号院,那里头装着几口子人,一百年内有过什么有趣的事儿,都在人家脑子里装着呢。聊起来,就好像回了一趟家,不知不觉,聊了将近一个钟头,话题早已经离开了稿子,转到了东四的贝勒爷、石头狮子上头。结束的时候还有些意犹未尽,跟孙大姐说,回北京的时候,看您去。
挂电话的时候,听见那边屋里其他的人在说笑,有一个清脆的女声笑得很张扬地说:“你就贫吧你。”
电话挂上了,那句话的影子,仿佛还在耳边呢。不是地道的胡同北京人。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闭上眼睛,这话音儿好熟,说这话的多半是当年胡同里我称作姐姐的那些北京女孩子们。
那时候自来水还没有装进各家,早晨起来,大伙儿得拿着各式洗脸盆子上院子中央水龙头前头排队等着去,经常看见不耐烦的女孩子,把洗脸盆放在脚边,当着人面大喇喇拿面小镜子就开始梳头。前些日子看篇文章里有说法,说有教养的女孩子绝不当着男人的面儿补妆。要照这个说法,我们胡同的姐姐们大概没一个能算淑女了,可她们的头发多半又长又亮。
这时候,往往就有自做潇洒的GG想方设法地凑过去聊天,中间不知道说了什么风话,便听见这样清脆的女声咯咯笑着来一句——“你就贫吧你。”
有多少粗线条的鸳鸯红线,就是这么串上的呢?只怕胡同里嫁了人的JJ们自己也记不得了。
在胡同里,街坊,是个很说不清的词儿。邻里吵架骂街的时候,二大爷瞪着斗鸡眼,那模样简直可以吃了四大妈,可是每天他还得照样和四大妈对门,闻四大妈家韭黄炒鸡蛋的香味抽鼻子,昕四大妈家电匣子里“坐宫”唱到精彩处要关灯睡觉喊一嗓子:“四姐您让我听完这段儿成不?”
街坊之间没有秘密。你们家还有几棵葱邻居比你还清楚,谁家的小家伙拉屎了一院儿的人都得跟着闻味儿。晚上睡不着觉,略一凝神能听见后院那谁家的新媳妇和新郎官也没睡呢,两口子叽叽喳喳能聊到半夜,当然声音都是压低了的你绝听不清两口子的'悄悄话。只偶尔那新媳妇会咕的一笑,不自觉放大了声音让你听到一句——“你就贫吧你。”
多少年后,忽然觉得,那一句略带娇嗔的话里面,不知道有多少旖旎风光呢。
更多的时候,是夏天热了,看见某个院门里面几个黑影靠着门框磕牙,间或有下夜班的回来,推着自行车从几个人中间穿过进院,还得低低地说一声——对不住。
这就是乘凉呢。哥们儿姐们儿聊着天,还能看看马路上的风景——马路上有什么好看的?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大伙儿都那么着,谁也没觉得不正常。
几乎无例外的是每个人手里都抓着一把瓜子,一边聊,一边噼噼啪啪嗑得热闹。有时候,就听见嘎嘎大笑,不知道谁说了什么笑话,便有很不淑女的对着那讲笑话的男生肩膀上猛推一把。半戏虐地说:“你就贫吧你。”
那种笑声消散在胡同里,就像草叶上的露珠一样自然。
一瞬间,仿佛胡同里头的国槐已经在了眼前,耳边还是那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清脆地笑着的声音——“你就贫吧你”,还有故都那淡淡的煤烟味儿。
电话里听来的一句话,就让人想家,还写了这么多,我这是怎么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