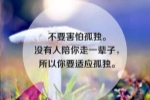大学生返乡高潮作文【一】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大学生返乡高潮作文【二】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我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久别的故乡。仍然是那一望无垠的农田,仍然是那朴素古色的碉楼,仍然是那姹紫嫣红的花丛,仍然是那绿柳轻拂的湖畔……一切都显得熟悉,一切都生机盎然,一切都散发着农村自然的魅力。看哪!那红装嫣态的杜鹃花,正在与飞舞着的白蝴蝶玩耍呢;那枝叶繁茂的榕树,好像一位久经沧桑的老人,此刻,他静静地聆听着枝头上的小鸟的趣闻,时而榕须拂动,仿佛是被小鸟的话逗乐了;清清的河水上,鸭子们悠闲地划着掌,抖抖毛,发出“嘎嘎”的声音,真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也许它们是在向人们报告春天到来的喜庆吧;田地里,牛儿勤劳地工作着,可能它也明白“一年之计在于春”的道理吧……一切都是那么可爱,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感到快慰
大学生返乡高潮作文【三】
“郭斌!”表姐在前院大声地叫我。
“有啥事?”
“咱们一起去摸爬叉把?”
“啥!啥!啥!”我边喊边带着好奇心跑到了前院,“你刚才说什么?”
“去摸爬叉呀!”表姐平淡地说
“爬叉,咱家乡有那么多的新玩意,叉子也会爬?啊,太不可思议了。”
“我说的是一种虫子,而不是会爬的叉子。”姐姐慢慢的给我解释。
“竟然有叫叉子的虫子。不可思议。”我小声的嘟囔了着。
表姐把我带到了一个长满梧桐的地方,这里阴森森的,树叶被风刮的哗哗响,树梢上云雾缭绕。这时,表姐指着树干上的黑东西,笑着对我说:“看,那就是爬叉!”表姐把它捏起来,我仔细一看。哎!原来的知了,未脱壳的幼虫呀!“许蕾,你抓几勺了?”一个一起抓知了的人问表姐。我更加疑惑了,怎么又成几勺了?“刚来,一勺还没抓够。”
“怎么又几勺.一勺了?不明白,不明白。”我自言自语道。
“几勺,哎!就是几十只。他在问我抓了几勺爬叉了。”不知什么时候,表姐走到了我的'面前。天黑透了,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回到了家。刚一坐下,奶奶就从外面气喘吁吁的回来了。只见奶奶花白的头发被汗湿透了,奶奶真累呀!“奶奶,我给你擦擦汗吧!毛巾在哪?”
“你的左枪就有毛巾,用它就可以了。”
“哦,奶奶,这边没有枪,再说,枪上怎么会有毛巾呢?”我很是奇怪。
“左枪有毛巾。”
“奶奶,这没有枪。”
“不是枪,是左枪。”奶奶有些急了,可我还是不明白奶奶在说什么。
奶奶看我一脸茫然之色,于是,就站起来,走到我的左边,从上面的绳子上取下毛巾。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左枪”就是左边的意思呀。
方言在我和家乡.亲人之间是个很大的障碍。如果人人都讲方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又如何进步.发展呢?普通话,是我们社会进步的阶梯,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是我们心灵交汇的渠道。让普通话带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和飞腾,成为社会交接的天桥吧!
大学生返乡高潮作文【四】
跟大哥、细哥到二郎庙水库捕鱼。(细哥承包的这座小水库只有三十亩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纯净,可直接饮用,鱼放在里面长得非常慢,一年下来甚至还要瘦。每年腊月底或者年初,细哥就要从外面进鱼秧,虽说是鱼秧,其实有三斤多一条——这种鱼是在平原地带的池塘里用饲料喂养的,进价是两块多,但是鱼在纯净水里清洗了一年之后,肉味大大改善,可以卖到五块多一斤。
一个拉砖的师傅把车停在坝上。我们问他,从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钱。他骂了一句话粗话,然后说:“两百块,划不来!”又说,就是这样的生意,也越来越少了。山里的楼房基本都做完了,没有做的也都在县城里买了房。大哥说:“在县城买房又么样,到时住在那里做什么呢?”司机说:“只要是人,总有个生存的法子。”又来了一个人,是细哥的同学,他的摩托车上带着老婆和还在读初中的儿子。得知他在这山里做了楼房,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细哥问:“你要买那么多房做么事!”他叹了一口气:“我们这时代不叫人过的时代!没办法!”“做了一栋楼,买了一套房,还叫没办法!明年还去打工吗?”“不去打工,在家里做么事?”而这座水库上头的两个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这里做了一栋楼,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其间来了一人,开小车,戴墨镜,手腕上戴着很粗的黄金链子。老远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网的细哥,问有鱼没有。细哥正划着独木船,一只手划,一只手下网,笑着答:“你又不买,问着做么事!”同我们说话时,他的墨镜始终没有摘下来,神气得不得了。墨镜又对细哥喊:“别扑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里就沉了,帮不了你。”说完就独自哈哈地笑。他同我们说起晚上要陪开挖机的斗地主。说是挖山种天麻,规模很大,已经买了十五万斤树。从言谈中得知,他平时在县城住。细哥的同学也说,他准备将家里几面山的树都卖了——分田到户后交了几十年的税,没有沾过任何光。后来听细哥讲,墨镜小学没读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讨债,拿斧头砍人,就这样起家的。
一会儿又来了母女三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她们是来买鱼的。跟墨镜是亲戚。墨镜却不认识那个年纪最小的女孩。“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呀!”墨镜说,“在哪里打工?”她说在温州。“属什么?”“属鸡。(刚满20” 墨镜说:“还没有说人家吧?我帮你介绍个。”女孩的母亲说:“她回来这几天,已经有好几个人来介绍。”“某某某正为儿子找媳妇急得哼,我把你说到他家。”(说,替人说亲的意思女孩母亲连忙说:“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县城里。”墨镜说:“他家在县城有套房子。那男孩的娘脾气不好,但你们又不跟她过,你们到县里住,做点小生意。他家也有钱,你叫他们现在拿个四五十万,轻而易举就拿出来了。”墨镜走的时候,表示过两天,要带那男孩上门相亲。
(2013年腊月25
(3车子。近些年来,对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对一种东西的渴求,可能比对房子和妻子更为强烈,那就是车子。车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万,八万,二十万,各种档次的都有。老百姓不认识车子的牌子,不知道车子的价位,只知道这些车叫“小车”。不管什么小车,关键是要有!
在农村,房子是一个媒介,车子更是一个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动,车子却可以四处招摇,表示衣锦还乡。很多二代、三代农民工,当下最大的期待就是买一个车子。尤其对那些好些年没回家的人来说,他再次回家,必须要有辆车,否则他怎么证明自己?
春节的县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这些车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回来的,与此同步的情况是:物价飞涨。
大学生返乡高潮作文【五】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3葬礼。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过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其实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中央的政策,谴责干部的腐败……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守丧完毕,大家集体出力,将他抬到山上,让他入土为安。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大学生返乡高潮作文【六】
春节将至,我随着爸爸妈妈回到了老家,陪爷爷一起过年。其实爸爸妈妈是不用回老家的,回到老家,定会有很多繁琐之事,而且严冬还会过去,凛冽的寒风定会又一次袭击我?不禁风的身体,我每每一想,心中就变得发抖,那种凉意,直通我的心坎。但是爸爸认为爷爷一人在家,甚是孤独,做儿女的必须要尽到孝道。我明白爸爸这样做,是为了在我们这些孩子面前树立榜样,做一个感恩之人,回报那些为你无私付出的人,不仅是父母,更多的是社会吧!于是,就这样,我们踏上了返乡之旅。
当我们开着车,与爷爷还有近一百米时,看到爷爷在驻足张望着什么,车离爷爷越来越近,我不知道是爷爷再向我们走来,还是那一刻名画面就定格在那。我当时想起自从中秋,好久未看爷爷,那份想念纵然使我大步跨去,与爷爷相拥。那一瞬间,爷爷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嘴里喃喃着:“回来了,就好。”那一瞬间,见证了幸福如此的简单却又更加的平凡;一个电话的问候,一次团聚的快乐……
展望这个时代,金钱利益的'社会,老一辈人的辛苦付出又换来了什么?人们常说父母对于我们的爱是十分,而我们回报的却极少。是啊!我们也该醒悟了,人不应该忘根。
伴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一家人在享受着团圆的欢乐,欢饮达旦共同祝福新年。过去的一年正在悄悄的在我们的欢声笑语中载入过去的史册……。而这个年,教育了我太多学校没有的知识—每个人都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将爱在子子孙孙中传递下去。幸福如花,而在感恩中所建立的幸福会永远不会凋谢、残败。因为这朵花瓣中寄托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满含着“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丝丝眷恋。
人世间没有不觉的风暴,感恩有其不老的风情。幸福之花开在感恩枝头,那一丝血肉亲情如阳光般耀眼,灼灼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