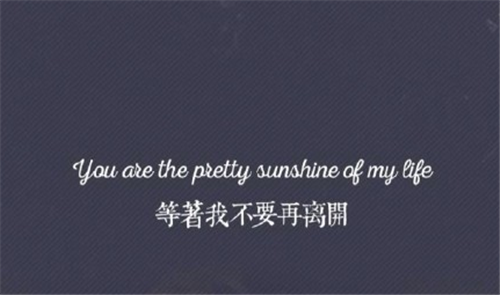
母亲说作文【一】
雨说,我来了,我来了就不再回去
当你们自由地笑了,我就快乐地安息
有一天,你们吃着苹果擦着嘴
要记着,你们嘴里的那份甜呀,就是我祝福的心意
母亲说作文【二】
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从村子里的民办小学转到了乡政府所在地的中心小学去上学。离家十几里远,得住校读书。学习条件是好多了,老师也是从地区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公办老师。再不像村里上学,下学后还得回家帮助下地干活去的父母挑水、做饭,这些倒是次要的;那时候的农村没有电灯,家里仅有的一盏煤油灯,夜里妈妈还要给我和弟妹们做针线活使用。为这,我便用墨水瓶、薄铁皮卷成的细管和棉花捻子,做成了一个简易的煤油灯,在夜里看一小会儿语文书。
在中心小学,校长特意给我们高年级的小学生开设了一节晚自习课。时间不长,虽只有一个小时,却可以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我的视力至今仍能够保持在4.0度左右,几十年过去了,心下常常感激那位慈祥的老校长。
每逢周末下午,从各村返回学校的同学们都要从家里带来充饥的“好饭菜”。那时候实在是太饥饿了,尽管年龄很小,肚子却能盛很多食物——那种清汤寡水式的淡饭。父母心疼孩子,有的把一盆烩菜装进饭盒里给小孩带上,有的煎几张葱花饼给小孩包上,家里条件稍好一点的蒸几个馒头炕干了给小孩拿上,还有的装一瓶猪油煎辣子给小孩拿上,真的是拿什么的都有。
这时候,铝制饭盒便成了那时候我们学校最最流行的盛饭用具。现在想想,且不说铝制饭盒容易褪色,常常把两手弄得乌黑乌黑的,单就它对人体的毒害性一点:比如铝对人脑的损害、铝对人骨的损害、铝对人的肾脏的损害以及它对人体造成的贫血等,都十分后怕。
好在年轻就是资本,对新事物就是敢于大胆尝试,虽山中有虎,仍不惧山高虎凶。庆幸那一方小小的铝制饭盒没有给我们造成发育上的致命伤害!
长大后,有幸成为保家卫国的武警战士。每当部队进行武装越野、野外生存训练或者长途拉练时,那一方小小的军用水壶便会叮叮咣咣地在我的左胁下、胯骨上敲打,体能的消耗加上水壶击打的疼痛,使我十分厌恶它。
等到同志们到达目的地解下装备、就地修整时,胁下挎着的小小的橄榄绿军用水壶便发挥出了它应有的作用:急切地拧开壶盖,及时地补充水分便成了我们每一个战士此刻的急需。等到炊事班造好饭,炊事班长大勺一挥,军用水壶的外套——饭盒,又发挥上了它的作用——供战士们盛饭用。“嘿嘿,老伙计,你真是俺的`救命宝贝!”
从军五千多个日日夜夜,水壶可谓是常伴左右之一。
岁月倏忽流逝,生命变化无常。“月亮走我也走”。月亮走了还会照样回来,而我却把生命走成了青春不再。这也许就是造化中人与物之区别所在。好在人之极致不怕造化弄人,犹可“人定胜天!”
母亲早已不再是我儿时记忆中的模样,青丝染上了霜花、腰身不再挺拔、腿脚变得迟缓,过度的操劳使她浑身落下了许多疾病。坚强的母亲把那些头疼脑热、腿脚不适和胸闷心慌默默地忍受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如堤之蚁穴,不能固本。老人家还是极不情愿地住进了医院。
下班后,我到超市里买了一个多功能饭盒,给母亲买来医生禁忌外的饭菜,摆在母亲病床前的小柜上,供她享用。后来,二妹也从她家里拿来饭盒,给母亲装着家里做好的饭菜;再后来,妻从家里包好饺子、熬好小米稀饭,装进我家的饭盒里,最后还不忘把自制的泡菜盛在饭盒的套盘里,给母亲送到病床前。
饭盒来来回回地顶替着,许是感动了上苍?母亲的病在医生的精心诊治下日渐好转。
我在想,一个小小的饭盒为何能在不同的岁月和不同的环境下发挥出如救命般的大作用?是我人为般的刻意强加,还是本身之作用使然?抑或之外的纽带关联?
虽不得而知,我看就不得而知罢。
母亲说作文【三】
四月天,珠玉尽碎百花倦。
听见雨的声音:四月已在大地上等待久了······
等待着,等待着雨的滋润。干渴的牧场,零星的枯黄的牧草,如一头乱发般披散着;田里灰蒙蒙的土地,扬起阵阵黄烟,它们在期盼雨的洗礼。鱼塘中只留着浅浅的一滩寒水,鱼儿无力的挣扎,溪流中裸露着鹅卵石,嘶哑着嗓子唱不出动人的歌。地下,睡着的种子,那希望已困了一冬,等谁来解开封印。听见雨的声音:我来了,探访四月的大地。
雨,踮着脚,悄无声息,在天地间织起一张冰繑似的水幕,那是她静美的身影。雷电不会来,风也不愿在这份宁静中呼啸。
雨来了,她呼唤着孩子们:出来吧,不要躲闪,扬起鲜花一样的脸来迎接我,喝着雨点的节拍,去瞧瞧大地的新妆。
田圃贪婪的吮吸着甘霖,泥土黑亮,似乎能淌出油来。牧场中忍耐一冬的生命不再沉睡,希望从地下探出头来。池塘水涨,鱼儿欢快的甩尾,漾起漪涟。溪水漫过干涩的石子,轻盈地跳跃,唱出婉转的旋律,清脆美妙。
听见雨的声音:我的家,在遥远的地方,群山整日与我嬉戏,白云将我环抱。
孩子们,要勇敢的笑啊!我来了,大地的万物都笑了。你们笑了,大地的希望就有了。
雨,来了,就不再走,永远安息,她留在笑声中。当你吃着甜脆的苹果,要记得,那是雨最后的祝福。
母亲说作文【四】
-----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
郑愁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