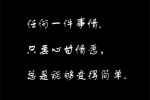美学类作文【一】
世界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一个对象化了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或无数个世界-没有两个人的思维是相同的,因而对于世界的印象也是不同的,于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美丽心灵》中的纳什就活在自己的心灵世界中。这可能是唯心主义,然而人确是凭自己的感觉去认知世界的。
许多个夜晚在《东风破》(流行歌曲 周杰伦作曲)的旋律里入睡,悠扬的二胡声每每将我带入未知的又似曾相识的世界,引动无尽的夹杂着哀愁与温暖的回忆与追思。“一个造出新节奏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情感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18页)如果一首新歌的新曲也算新节奏,那作曲家就是“高明的人”。这种新节奏也得符合人的审美心理-至少是部分人。没有人的心绪和思维是相同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刹那”的心绪和思维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有无数的“新节奏”等着人们去创造,去发现,来满足这无数的心绪和思维,以应和它的节奏,引起它的共鸣和感触。这种共鸣和感触很多时候是由“回忆”引起的。当节奏与某一时候的心境相吻合,回忆便复苏,人便彷佛进入未知的又似曾相识的世界。“我们一般地能够较为容易地生动地回忆‘动作’,超过单纯的形式或色彩,所以魅惑力较之‘美’在同等的比例中对我们的作用要更强烈些。” (10页)那么对于音乐的“节奏”的“回忆”效果也说明了“节奏”所具有的“魅惑力”不亚于文学和绘画,甚至超过它们的影响力。人的心灵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世界。
关于“美从何处寻”,我认为“美感”是人的心理现象。当我们说某样事物是“美”的时候,其实是将自己的心理感受对象化到事物上去了,也就是“移情”,进而以为“美”是事物本身具有的属性了。事物是否“美”,取决于它在人心里引起的感受,没有绝对相同的感受,也就没有绝对相同的“美”和“美感”。
事物(世界)是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存在于每个人的主观世界里的对外在世界的印象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东西,但它存在于心理世界中,是“美”所由产生的主观(心理)基础。而真实的事物(有形或无形,可感或不可感)-没有任何人为色彩的-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它构成我们感知“美”的客观(物质)基础。“美感”(心理感受)存在于人的心理世界中。
美学类作文【二】
《美学散步》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他在书中展示了一个美的人生和宇宙,充满了亲切感和家园感。他从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宇宙是无尽的生命”,也发现了它是“平整的世界,圆满的和谐”。英国诗人勃莱克的“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就是这种描述的最景致的诗句。没有一种以天地为庐而又悠悠自足的博大情怀,没有一种能澄情以观道的空明澄澈,是不可能发现这种生动与清和的美的统一。而他似乎轻而易举地领悟到了美的神韵,如在拈花微笑间顿悟了一切声光,色彩和形象中微妙精深的律动和气韵。
中国人讲“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思想,“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从而获得对于“道”的体悟,“唯道集虚”。这在传统的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中国古代的绘画,提倡“留白”、“布白”,用空白来表现丰富多彩的想象空间和广博深广的人生意味,体现了包纳万物、吞吐一切的胸襟和情怀。宗白华用翔实丰富的例子,提出了中国诗画、书法所表现的虚空要素以及从此形成的宇宙意识,他认为“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中国艺术最后的理想和最高的成就。他在我们面前舒展开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带我们去玩味古代名画的内蕴,画家所写的自然生命,集中在一片虚空之上。空中则荡漾着“视而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在这片虚空上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一山一水,都负载着无尽的深意。《美学散步》让我们体悟到中国画的“气韵生动,迁得妙想”之精髓。前者是说一幅画要涌动着宇宙万物的“气”的节奏、和谐,给人一种音乐感;而“迁得妙想”则是通往“气韵生动”的途径。所谓迁得妙想,就是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用本心去体味外物的内在精神,把自己的想象迁入内部,经过一番曲折,才可把握对象的真正特质和精神。
这种对“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清新淡雅之美”的追求,体现了宗白华内心深沉孤寂之感。在现代文明高度高度发达下,人们的传统文化和生命精神日益失落,徘徊于这种矛盾的忧郁和苦痛的边缘,宗百华悲怆地喊出“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他反复提醒国人要意识到现代精神的颓废问题,这正是他作为一个孤独的灵魂对生命发出的呐喊与召唤,他把他的这种孤独的探索和冷静的思考引入了美学范畴,个体生命的孤独和落寞,在理想的自由艺术之境中完全可以转化为对生命的歌颂和追求。通过艺术对人性本真的追寻,他的孤独落寞得到了彻底地发泄,只有在这样的境界中,人才能真正找到精神的家园,返回精神的故乡,抚平内心的伤痛,慰藉平日孤寂的灵魂。
《美学散步》让我得到了一种生活情趣和审美方式,伴着笔墨的清香,细细体味,宗白华那自由孤寂的灵魂,高尚清真的人格魅力,在寻求美的道路上指引着我,让我抛弃浮躁的世俗,向美学丛林的深处迈进。合上书,闭上眼,书的余香犹存,而我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缀叶如雨”的冲淡清幽境界。
美学类作文【三】
山川草木,泥墙黛瓦。究竟是什么在梦境里时隐时现?是自然的造化还是本心的感受让我看见落照里白帆点点的月夜的海,听闻那海潮如诉衷曲的絮语。
行走在中国的文化檐廊里,天空的白云貌似永久飘逸,覆成桥畔的垂柳给人无限的遐思。月总是出现在诗人的心腑里,“坐久浑忘身世外,僧窗冻月夜深明”,静穆的月夜不禁让人寒意顿起。“今夜月明入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又被描摹成念乡的使者。诗人对月的无尽感怀使月的姿态丰富多彩,美渗透在诗人的笔下。朝阳下无意瞥见一枝带露的花,感觉着它生命的新鲜,生意的无尽,自由而无所挂碍,便产生了无穷的不可言说之美。美还在同情里,美在同疏林透射的斜阳共舞中,美在同蓝天闪闪的星光合奏中,美在同黄昏初现的冷月齐颤中。无限的同情对于星天云月,鸟语泉鸣,死生离合,喜笑悲啼。同情是一种情感的交融与共振,亦是美之所蕴含。罗素曾说:“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止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而又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他从对人类的同情中获得幸福的动力,但是同情更是可以移至山川草木,亭台瓦楼乃至万事万物,就像是虽然走进原野,发现花能解语,鸟亦知情,亦觉得山水云树,月色星光是我们有知觉,有感情的姊妹同胞。这样,美就漫步在纯洁的同情之中。
再转阁游行于文学艺术境界之中,恍惚如乘上一叶小舟游荡在山水诗画中观摩亭岸垂柳,飞鸟掠痕。方士庶在《天墉庵随笔》里说“山水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或率意挥洒,亦皆炼金成液,弃滓存精,曲尽蹈虚揖影之妙。”美,美在意境里。元代汤采真说:“山水之为物,禀造化之秀,阴阳晦冥,晴雨寒暑,朝昏昼夜,随形改步,有无穷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汪洋洋,如万顷波,未易摹写。”山水成了书写情思的媒介,美虽在意境里但也要寄托在实物下,而也只有大自然的全幅生动的山川草木,云烟明晦,才足以表象我们胸襟里蓬勃无尽的灵感气韵。意境的抒挥使美得以具化而又闪透着一种朦胧的色彩,就好比赞赏那树的苍翠遒劲,美被加于树之上,但意境里却闪透着一种基于树却高于树的朦胧之美。意境里所渲染的生命化,传神化,妙悟的体验才是给人心灵美感撞击的三大源泉。草之灵悟,花之妩艳,木之坚韧无不见诸于诗人构筑的意境之下,使得描摹的物象愈发鲜明活泼。
最后徜徉在艺术宝库的大殿里,美更是难以胜收。韩愈曾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与心,必以草书发之。”不难看出,张旭的书法不但书法自己的感情,也表达出自然界各种变动的形象。这些形象在他的书法里不是事物的刻画,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像中国画,又似音乐,似舞蹈,又似优雅的建筑。书法家的一撇一捺,一转折一弯钩,都能再现其书写时的心境,比如某个弯钩出现裂点,颜色偏深,那想必是书法家心绪不宁,或为外物所扰,或为心内波澜;而有时笔画顺畅,一气呵成,遒劲有力,又能窥见其行云流水,舒畅感怀的闲境。再转至音乐节律,无不辐射出幻境之美,音乐使听者心中幻现出自然景象,因而丰富了音乐感受的内涵。虽未至心却已至,身不行而能梦绕山川,这都是“一草一木栖神明”的启示。其至微至妙难以名状,不亦是无穷无尽,清谷空幽的美吗?再之于园林建筑,横亘了设计者的笔法,承载了建筑者的希冀。或空间的空灵幽远之美,或内部装饰飞动奇玄之美。窗匾檐栏,山石水木遍布空间的精心布置,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无不蕴含着美的感受。
美的散步绝不是要飞到奇景妙物处参看,许多时候就是自己的一片内心,一点空灵的创造也会展现出奇绝的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