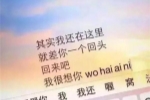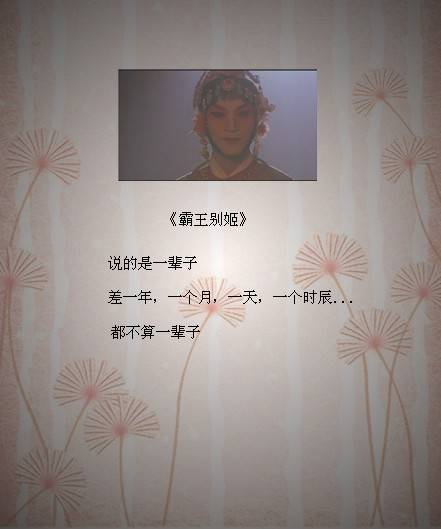
生命面前无大事作文【一】
??月面前无壮士我第一次经历死亡是在18岁的时候,不是我亲身感受,而是它发生在我身边,近得只有一张老藤椅的距离。
那是一个阳光热烈的午后,窗外冷风彻骨,屋内却非常温暖,人浸泡在阳光里,好像浸在一汪热水里,舒服极了。我陪爷爷在阳台上晒太阳,给他读积攒了一个星期的报纸。棉花被里的爷爷身体缩得小小的,脸上很多平静的皱纹。小土狗趴在我们脚边,非常温顺。煤炉上炖着排骨萝卜,升起袅袅白烟。奶奶在厨房里给我们做桂花圆子汤。我觉得那一刻,很好很好,那一刻内心的温柔平静,余生也没有复现。
奶奶端着的青花瓷碗砸在地砖上,很尖利的一声响,我觉得很美妙的那一刻就倏忽过去了。像感应到什么一样,我扭头看爷爷,静得像一块泥塑。我伸手去探他的鼻息,早就没有了。可是身体还被阳光浸泡得很暖和、很蓬松,我握着爷爷粗糙干硬的手,眼泪一滴滴落下来。
奶奶比我想象中平静得多,她只是红着眼眶握着爷爷的手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帮他理了理毛线帽和围巾,像话家常一样对他抱怨道:“老头子,你就等不及了。喝碗桂花圆子汤,再喝碗萝卜汤,热乎乎地上路多好。你要走了也不说一声。你真是一辈子没有良心哦。”小土狗在地上呜咽了一声,大概感受到了什么。
爷爷年事已高,谁都知道死亡一定会在哪个路口等他。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他说走就走了,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爷爷的后事办完,奶奶懒了很多,不爱出门也不爱进厨房了,整天坐在爷爷从前晒太阳的地方,发着呆。这样晒了一整个冬天的太阳,一直到来年的春天,她才回转过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把,进厨房给我们做好吃的。
我想奶奶是在心里熬过来了,她比我们多活了几十年,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世情是本最丰富的书,她一定都明白了。我们生命中的大部分人和事,不会有真正的告别仪式,而是说没有,就没有了。
有一天,奶奶说:“世道残酷着哩,有啥法子呢?只能坚强啊,咬咬牙就过去了。”
奶奶这话是在参加她一个老姐妹80岁的寿宴后回来说的。那个阿婆年轻的时候插队到贵州的山区,一直都没有得到回来的机会,慢慢就死了心,在那里安了家,把异乡当成故乡。阿婆每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匆匆忙忙赶回来看看娘家人、吃顿团圆饭。我还记得小的时候,陪奶奶去镇上唯一的公交车站送阿婆。中国人大概都是不擅长拥抱的,这对感情深厚的老姐妹只是你的手捏着我的手,身影都是瘦小而单薄。她们穿着陈旧而整洁的衣服,阳光迷蒙,风吹乱了她们的白发,奶奶帮阿婆理了理,8路车尘土飞扬地驶来了,奶奶推着她上车,说:“大妹子,上车吧。照顾好自个儿啊。”
这一别就是十几年,老之将至了。奶奶说起寿宴上的场景,流露出很凄凉的况味。那老姐妹和她的母亲都健在,只是脑子不大清楚了。各自穿着一身簇新的衣服,恍恍惚惚地坐在那里,周围热热闹闹的,可是好像完全不关她们的事,她们专注地进入了老人的世界,像那些我们小时候弄丢的铅笔、橡皮、日记本等,它们在岁月里待着的一个黑咕隆咚的地方。
奶奶的老姐妹发着她的'呆,偶尔痴痴地笑,子孙们把她们母女俩搀到一起,历经沧桑的两人却是幽幽地对看了一眼,又无动于衷地把浑浊的眼珠子转向了别处。她们就这么互不认识了,没有一次告别,没有机会再说一句:“妈,你好好看看我,趁你还记得我的时候再看看我。”
老姐妹在酒席散场的时候好像清醒了一些,拉着奶奶的手说:“妹子,大兄弟走了,以后就剩下我们两个老姐妹了。”奶奶一阵心酸,正要跟她多说一些话,她突然就又糊涂了,刚才的清醒好像昙花一现。
奶奶回家以后,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阳台上,我忽然觉得奶奶的身影比从前更加凄凉,她们那个时代的人一个个都走了,就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个世界上。
奶奶如果读过书,会知道有一个诗人叫苏东坡,他写过几句词是这样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奶奶不识字,无法美化她的苦难,她说这都是命。
时间像火车一样轰隆隆地往前走,并不会因为那是一个衰老的人而将它的步伐变缓、变柔和。奶奶在这白花花流走的时间里以她的速度一点点衰老着。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人在老到一定岁数时会暂停衰老,五十岁和六十岁没有多大区别,却又突然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如山倒轰隆隆地老了。
奶奶在70岁的时候成了一个被岁月风***老人,雪白的头发胡乱地散在衣服领子上。为了方便行动,她搬到了底楼由车库改造而成的屋子里。于是一整个秋天到冬天,从日出到日落,她都坐在门口的藤条椅子里晒太阳,像一个深色的球,身上是层层叠叠的衣服,露出花花绿绿的边。我上班前去看她,她问我有没有吃早饭,又说她吃了一碗泡饭,问我要不要来一碗。我下班回来去看她时,她又问了我同样的问题,很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屋里喝一碗泡饭。我倚着门沿站着,打量着她这毫无隐私可言的方寸之地,望着她似懂非懂的脸,一阵心酸。
我的奶奶也糊涂了。也许是一天天慢慢糊涂的,可由于我们的疏忽,察觉到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大多数人。
生命面前无大事作文【二】
张某收养了20多只猫,最后,寝室里却空荡荡的,连动物生活过的痕迹也没有,不免使人怀疑,在这的被后,到底是什么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他的同学去了他的寝室,正好有一只小猫,雪白的`毛上粘有一些血迹,猫眯转过头,同学们惊呆了,小猫竟被挖去了眼睛,正在往下淌血。
那是一种怎样的痛。
原来,张某在人际关系上处的不好,就买来小猫,用来发泄,起初,只是用竹鞭抽它,小猫发出惨叫,最后,他抓起小猫的后腿,用剪刀戳猫的眼睛,直到它成为一的血窟窿。
触目惊心,无论张某再怎样狡辩,再事实面前,都是那么苍白无力。
我们无法理解。
自然创造了万物,生命面前,一切平等。
我们无法剥夺他们的生命。
没有权利,
永远,
永远...
生命面前无大事作文【三】
老宋,就等你了,来来,快过来,我们开始吧。老师一把将老宋从门口拉到房间中央。说来也怪,整个房子灯都关着,乌漆吗黑的,只有中央摆着张桌子,上面铺着洁白的餐布,一束聚光灯打下来。老宋被晃得有点睁不开眼睛,他往四周瞄了瞄,好家伙,暗地里围了不少人啊,不过看不太清楚,只见了一双双眼睛,发着绿光,像一群狼崽子,老宋有点害怕,问:老师,不是说请我吃饭吗?现在整得哪出?
老师没搭理老宋,自顾对着黑暗中的人说:欢迎参加饕餮之夜。然后从桌子里拿出一个杯子来,里面放了一个大石头,差不多和杯子一样大,老师问大家:杯子满了吗?
黑暗中传出一个粗粗的声音:没满,房地产至少还可以涨十年!房子本来就不是给穷鬼修的,买不起房子是他们没钱,富人会越来越富。老师你可以倒点沙子啊,你说是不是啊老宋?
老宋不知道是谁问他的`,他有点不好意思,虽然平常穿得比较光鲜,其实兜里也没啥钱,也算个穷鬼。
老师表扬性地笑了笑,倒进了沙子,又问:现在满了没?
传来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别介啊!你们倒是捞饱了,可咱国际热钱还才刚进来,连腥都还没尝着,大家连手好发财嘛,老师你可是主流经济学家,你得好好开导开导老宋,别太保守啊。快倒水,还能倒水呢,别逼急我弄个鱼死网破。
老师很镇定笑了笑:放心,大家发财。遂又倒满了水。
这时一个不阴不阳的声音说:你们倒好,分完了蛋糕,可咱家吃啥啊,咱贪了那么多钱,总不能让它们贬值吧,你看这物价涨的,哎呀,谁要让咱家过不好,那谁都别想有好日子过!
老师慌了起来:啊,怎能把您忘了呢。赶紧把杯子的东西全倒出来。重分重分,咱们合计合计再分一次。
分了半响
老宋在旁边看不太明白,就心里嘀咕,分个东西啥的,把我叫来干啥啊?
老师终于分好了,各方面还算满意,他自己也挺得意的:来,大伙儿搭各手,把老宋按住,把这杯东西给他灌下去。
一堆黑手按死了老宋,眼看一杯泥沙石头就要灌下来,老宋这时才慌了:要死人了,要死人了,老师你咋害我呢!
生命面前无大事作文【四】
今天要收物理研究性学习作业,本来我上周就写完了,只是封面没有弄好,等我匆匆忙活完了,成了班里最后一个交上的,被老师一顿狂批。我冤,我郁闷…
上周布置完作业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了。我是个不肯让问题过夜的人,什么事情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质量倒是退而求其次了。本着一贯原则,我匆匆上阵,查资料,写论文,用了两天时间,终于把小论文写完了,心中大喜。由于当时没有封面的格式,想着也不是什么大事,等收的时候临时写上就OK了。于是放下心来,踏实地做别的事情。
今天老师忽然说收小论文,我本来也没怎么慌,可后来找不着放在哪儿了,翻箱倒柜,从一摞草纸中找了出来。抓紧时间写封皮,可格式让别的同学拿去了,好不容易找来了,写好了,装订好了就可以交了,谁知舍友的'订书机没钉了,我不禁大呼郁闷。各宿舍串了个遍,找到钉订上了,便匆忙向办公室跑去,结果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还有一件事,也令我耿耿于怀。大概是上周五下午吧,语文老师布置写练笔,许多同学认真地用笔记着。我有点不屑,不就几个题目吗?那么毕恭毕敬,至于吗?由于我没往心里去,回家后先忙着玩,直到星期日下午,才想起周记还没完成。赶一下不就完了,可写什么内容呢?老师布置的内容全忘记了,这下可抓了瞎。看来,只好打电话咨询了。自然不敢问语文老师,只能问同学。可电话号码呢?朋友本来就不多,怎么也找不到,还不是平时对此太“不屑”造的孽?不管他,蒙着写点应付一下,结果又遭到一顿痛批。回想起来,如果当时就记下周记内容,如果保存好朋友的电话号码,会自找麻烦吗?
一件小事,在所谓的大事做得很好的前提下做错了,完全变了味。生活中的一切何尝不是如此呢?好些事情失败了,并没有认真去总结,主观地认为自己能力不够,便安下心来做另一件事,重复以往的失败而不自知!有多少事是因为小事的失误而导致了整件事情的失败呢?我没细数过,但我相信有很多,如果不碰到今天的事,我可能仍然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既然意识到了,是不是就应该换个思路去考虑问题了?
我们往往能征服远方的高山,却被鞋里的沙子弄得不知所措。当我们决定整装前行时,缺少的不是勇气,不是能力,而是对待身边小事的态度。事无巨细,如果小事都能做好,目标不就越来越近吗?
上路了,莫忘清理干净鞋里的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