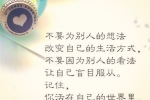关于乌鸦兄弟作文【一】
著名作家余华的新著《兄弟》看完让人非常困惑,很难将这本韩国影片一样装祯的小说和余华这个名字联系起来。至少我作为一名读者,实在想不到这本书居然是余华写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余华不能写这样的书,只是这样的做法实在太过浪费。
如果世界上必须有那么一本书,它的头两章需要围绕的女人的屁股浪费掉几万字,那么我希望这书的作者不是余华。因为这种事情只需要一个具有初小文化程度的人,怀着对女厕所的一定热忱就能在半天内干完。是什么让余华在《兄弟》一书里执意要亲自动手,不厌其烦地描写屁股,实在是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谜。看完《兄弟》(上)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告诉我全文和头两章有什么关系。如果《兄弟》一书直接从第三章看起,可能效果要好得多——-避免了看到一个著名作家的病态行为,并且不在这种病态上面浪费太多时间。
如果世界上必须有那么一本书,它讲述故事的时候总让你有种脱帽致敬的冲动,那么我希望这书的作者不是余华。如果余华失去了他鲜明的个人特色*,失去了他讲故事的能力,我希望他还能保持体面的沉默,而不是继续不知疲倦的说下去。《兄弟》(上)的前半部里,我不得不向王朔起立致敬,为了他的那本《看上去很美》,我现在看到余华版的了。在下半部里,我不得不向意大利导演贝里尼起立致意,为了他的《美丽人生》,我现在看到中国版的了。我的问题是:余华干了点什么?
《兄弟》据说是余华从百万字的家族史中转型而来的结精,按照他的话来说,是从一条小路出发,最终却见得了一个宽广的世界。恕我直言,我实在看不出什么世界来,这本书是彻头彻尾地在试图愚弄读者。
它就是一本通俗小说,通俗且恶俗。如果不是想钱想疯了,就不会把这么一本通俗小说写到40万字,而且分上、下册分别出版。这给人的感觉是余华突然想去挑战海岩,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所以,《兄弟》里才出现了香艳的臀部、小朋友的性*冲动和类似电影《美丽人生》一样的煽情故事。它的目的是满足从中学生到离休干部所有的需求,因此怎么看怎么像是一锅杂烩。
如此空洞无物的作品居然出自一名严肃作家之手,简直是对这个职业的侮辱。通篇对文字的炫耀,毫无创意的故事情节,甚至是对电影剧本的直接模仿,居然也敢于把这种杂烩端到桌上,当做年度大餐提供给读者?谁给予了作者和出版商这种勇气?让读者去分辨大餐和猪食?端出这么一份东西,作者难道不感到羞愧吗?这写的都是什么啊?
作为职业作家,我觉得对读者最起码的诚实和最基本的专业素养是应该有的。《兄弟》这种似驴非马的东西不应该出自一位成名的严肃作家笔下,尤其不应该出自余华的笔下。职业作家写出那么业余的东西来,值得自己反思一下。
关于乌鸦兄弟作文【二】
“今生不欠来生债,新年不欠旧年薪。”这句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孙水林和孙东林付出的代价无与伦比啊!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孙水林为了能够在年前给务工的老乡们发工钱,带着一家人驱车回家,不幸遭遇车祸,一家四口全部遇难,工钱也丢了六七万。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东拼西凑凑齐了老乡们的工钱。年迈的.父母为了让孙水林一路走好,没有牵挂,在自己的家里给工友们发放工钱。这种场景,谁不伤心?谁不掉泪?孙水林毫无牵挂地走了,他坚守的信念却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孙水林是多好的一个人呀!敢于坚持正义,对工友热情帮助,想方设法讨要工钱,时时刻刻为别人着想,宁愿自己忍受委屈,也要按时给工友发放工钱。他不顾道路积雪往家赶,不就是早一点给老乡们发工钱吗?可让我难以想象的是:几个工友不相信孙水林,还说出令人发指的话语。他们不但不理解,不同情,反而冷言冷语,这让我感受我们的生活里太需要理解了。
春天是疾病的多发期,这不,我外婆生病住院了,妈妈在医院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又是安慰外婆放宽心,又是倒水洗水果,忙得不可开交。外婆没有食欲,妈妈想方设法给外婆做她最爱吃的饭菜,并时常改善着生活。在妈妈的精心照顾下,外婆的病情有了好转。可有一天,我看见妈妈站在医院的一个角落里咳嗽得厉害,我忙跑过劝妈妈歇一歇,妈妈对我说:“孩子,我没事,只是小病,不碍事,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免得外婆担心。”“妈妈,你都咳嗽得这么厉害,该看看病了。”我不忍心看着妈妈虚弱的身体,而且知道妈妈总是不把自己的病当做一回事。妈妈说得轻巧,可我心里总不是滋味。从那以后,我一有空,就帮助妈妈,妈妈高兴得笑了,不断夸赞我。我心知肚明,因为我理解了妈妈。
理解是一种很高的爱,愿我们用心去体会吧!
关于乌鸦兄弟作文【三】
读《兄弟》的感觉犹如观看一幕舞台剧,《上部》(关于文革)是悲剧,《下部》(改革开放到现在)是喜剧;《上部》是悲剧中有喜剧,《下部》是喜剧中有悲剧;极度夸张的表演,极度粗鲁滑稽的语言,使得悲喜剧看起来都更似闹剧;舞台上的喧哗与***动,让人对故事本身压根不想去信,而待沉静下来,对故事背后的现实却又不由不深信。
《兄弟》发表后,畅销的同时也遭遇了国内批评界无情的批评,国外的一些评论大概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兄弟》自始至终都非常有趣。中国的批评家们不满于余华故事的荒诞和形式的粗糙,他们更愤怒的是余华对当代中国生活坚持不懈的批评。《兄弟》……充满了对整个社会辛辣与深刻的嘲讽(美国《洛杉矶时报》20xx年2月1日);余华笔下的中国***动不安,沉重压抑,畸形发展(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对这个世界余华根本不存希望(法国《读书》杂志)。
《兄弟》中描述的两个时代,用余华自己的话来概括,一个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命运惨淡的时代(文革)”,另一个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现在)”,从《兄弟<后记>》不难看出,余华在写作中国的遭遇时品味着欧洲的历史,而我在这本书中读到文革时不由自主想到了不久前英国的暴*,想到了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之死。英国暴*中参与打砸*的不少是学生,最小的不过10岁;卡扎菲被年轻的士兵抓到,士兵残暴地用鞋底抽打他的脸,虐打羞辱之后用枪结束了他的生命。卡扎菲曾问士兵:以我的年龄可以做你们的父亲了,我对你们做了什么你们要这样对待我?余华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特殊时代背景下人灵魂深处的恶和浊,只是,这恶和浊不仅仅属于中国。
有位诗人说: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余华坦言他与现实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说得严重一点,他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他写作的使命几乎就是发泄、控诉或揭露,他作品中充斥着暴力和死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心的愤怒逐渐平息,他对事物有了理解之后的超然,开始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他的长篇小说一改过去的写作风格,尤其在《活着》、《许三观卖*记》里,他贴近小人物的生活,倾听他们心灵的声音,为他们的绝望悲悯叹息,又和他们一起在绝望中探寻活下去的希望,并为微渺的希望之光悲喜交集。
关于乌鸦兄弟作文【四】
森林里有一颗老树,树上有一个乌鸦窝,窝里住着一对乌鸦兄弟。
一天早晨,哥哥发现窝破了一个像小拇指一样的小洞。哥哥不紧不慢的说:“这么小的洞不用管,反正也不影响我们生活。”然后便扭过头去找吃的去了。
乌鸦弟弟也看到了那个洞,它说:“这个小洞我才懒得修呢。”说完便拍拍翅膀飞走了。
夏天到了,洞已经变得像李子那么大了。哥哥一边吃着冰棍一边悠闲地说:“弟弟,那个洞变大了,咱们要不要修修呀?”
“不用不用,我就不信它能再变大。”弟弟躺在树上懒懒地说。
夏天很快过去了,秋天来了,瑟瑟的秋吹进了像橙子一样大的洞,吹的兄弟俩直发抖,哥哥想:哼!我看你明天修不修窝。弟弟偷偷的想:反正还有哥哥呢,让他修去吧!
寒冷的冬天到了,哥哥和弟弟把被子裹的紧紧的,但也经不起风雪的打击,它们被冻死了。
这则故事体现了一个道理,出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否则就会酿成大错。
关于乌鸦兄弟作文【五】
有一天,窠破了一个洞。
大乌鸦想:“老二会去修的`。”
小乌鸦想:“老大会去修的。”
结果谁也没有去修。后来洞越来越大了。
大乌鸦想:“这一下老二一定会去修了,难道窠这样破了,它还能住吗?”
小乌鸦想:“这一下老大一定会去修了,难道窠这样破了,它还能住吗?”
结果又是谁也没有去修。
一直到了严寒的冬天,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大雪纷纷地飘落。乌鸦兄弟俩都蜷缩在破窠里,哆嗦地叫着:“冷啊!冷啊!”
大乌鸦想:“这样冷的天气,老二一定耐不住,它会去修了。”
小乌鸦想:“这样冷的天气,老大还耐得住吗?它一定会去修了。”
可是谁也没有动手,只是把身子蜷缩得更紧些。
风越刮越凶,雪越下越大。
结果,窠被风吹到地上,两只乌鸦都冻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