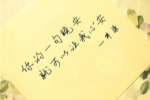回忆高考满分作文记叙文【一】
晨,多么美妙的一个字眼!
先是那晨曦。微微泛出鱼肚白的空中,渐渐透出些红火,淡淡的鹅黄之后,接着便有了点粉红色的光泽,有浓有淡,随着那云层的厚薄变化,反射着不同的光线。不一会儿,或粉、或桔、或黄或白,间隙中也有些淡蓝,如此绚烂,如此多彩,如此迷人。
再等一会儿,那朝阳终于苏醒了,伸个懒腰,从被子里透出一撮发丝,便给远山镶上一道金边。接着,朝阳一点一点挪了出来,透出火红的额头与两只眼,凝视着整个大地。金光照亮了半边天,那草叶,那花瓣,总有几个光点,似是天使撒下的一粒粒明珠,在空中缓缓飘浮着,播撒着希望。这便是晨的另一大主角,甘露。这是观音大士净瓶中的神露吧!
太阳仍在继续上升。此时已几乎不见红光,只有耀眼的金黄映亮天空,以及远处未尽的一丝黑夜之气,一点点残余的湖蓝,在太阳的千万支金箭中渐渐隐去了,等待着下一个黑夜,回来俯瞰寂静的大地。
朝阳已从远山头上透出了大半个脸,仍照耀着露水。嫩绿色的树叶、草尖也被蒙上了一层亮色,仿佛镀了金一般,美丽动人。朝阳终于又伸了个懒腰,从地平线上跳了出来。
晨风,带着一点点凉爽,迎面扑来。我被这风一吹,便猛地醒了过来,活力充沛。倘若天朗气清,举目四望,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便有一种全身心投入,再创造的美好冲动;倘若有一点晨露,另有一番风味——就像仙境中腾云驾雾一般,让我们感受大自然的幽静与神秘。
露渐渐地升腾了,它们飞向了太阳的国度,又回到了天使的怀抱之中,鼓励着我们:快啊,赶紧从现在开始努力,像我们一样奔向自己的天堂吧!
太阳也脱离了山的怀抱,抖擞精神,把自己的热献给我们,驱散黑暗,让每个人看清眼前的路。
晨,多么美妙的字眼啊!
它代表着青春与活力,它高唱着赞歌迎接每一个日子。晨,开启了日;日,累起了年。年复一年,人类充满生气的不息劳动,不就是晨之精神的体现嘛!
回忆高考满分作文记叙文【二】
智慧留白,人生至境
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在于水墨留白。白宣纸上聊聊数笔丹青之外,便是大片留白,但正是这留白,使中国画有了无尽的张力,给予我们无穷的想象,展现出朦胧而丰厚的美感。
笪重光于《画筌》中有语:“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如见竹林桃花便想见有茅庐草屋隐于其中,见蜂蝶逐马蹄而舞便想是踏花归来。宋朝郭熙云:“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流则远矣。”其理一也。
文学作品中的欲言又止或言之不尽亦是吊足了读者的胃口。那日,黛玉斜卧在塌,焚了诗稿,断了痴情,只吐了半句:“宝玉,你好……”便香消玉殒。黛玉想说什么?戛然而止而生的无穷意蕴,令后世多少文人为之啧啧,却无人敢作续貂之举,这,便是留白艺术的魅力。
而戏曲中那个简单的舞台更是将留白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唯一案一椅一空地,千军万马可走过,洞房花烛已点燃,长亭相送十八里别过……这些,皆因留白而生想象,因想象而丰富。
人生如艺术,亦需留白。留白,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
林语堂曾动情地讲:“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在这个孩子为了“美好前程”而撑着沉重的眼皮挑灯夜读,大人为了功名利禄而削尖自己的脑袋左冲右突的忙碌尘世中,我们的神经已经过于紧绷,若不适时松一松,恐怕一粒微尘便能将我们摧毁。到时便是白流了血汗,亦消磨了斗志。放慢自己匆匆前行的脚步吧,甚至可以停下来看一看沿途的风景,给心灵放个假,抛却生活的烦扰,惬意地呼吸自由的空气,你会发现,原来人生无需塞得太满,若无蜗角虚名的羁绊,轻松快乐竟是如此简单。慧开禅师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可见给心灵留白,做到心无旁骛,便能于得失之间,宠辱不惊,这实在是智慧人生的最高境界。
当然,为生命留白并不是消极懦弱的逃避主义,更不是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与前行的智慧之举。都说孩子是一张干净的白纸,你在上面画什么,他便成为什么。于是,焦急的父母便忙着在上面规划他未来的生活蓝图,从学习到娱乐,从家庭到工作,甚至兴趣爱好……这些都将这张纸填得满满的,但父母往往觉得这还远远不够。为何不留下一段空白,等孩子有了人生经验和阅历,由他自己慢慢书写?自己书写的人生,不管酸甜苦辣,那都是“我”的创造,而非他人安排。其实,这样的空白,我们真的很需要。
懂得给生命留白,腾出一片空地来播下自己的花种,用心地浇灌,开出一片灿烂的花田。
回忆高考满分作文记叙文【三】
如今数码相机已经十分先进,人们能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大量照片。然而,有人又重新拿起胶片相机,不顾一卷三十六幅的胶卷几十元的高昂成本,与暗房里费心劳神的冲洗过程。这是为什么呢?正是由于这种种麻烦逼着摄影师在按下每一次快门之前,都能够仔细深入地观察被摄物体,用心思考,因而每一张逐渐显影的照片背后都有一段值得慢慢回味的记忆。
这种回味在如今数码照片泛滥的时代已是非常稀罕了。人们用镜头代替眼睛,用照片代替记忆,以为自己这样便抓住了时光。
我也曾经这样天真地认为。我初涉摄影之时曾去过一次西藏旅游,带着自己的数码相机。蓝天,白云,碧水,雪山,面对这一切难以用人类语言形容的美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拍下来。于是,在西藏之旅的期间,我的眼睛几乎未从取景器小窗口上移开过,存储卡也被填得满满的,心想我已记录下这一切美景。然而,回家再次浏览这些相片时,却再找不回当时的那一份激动了。当时只顾着拍照,却忘了用心体会旅途的愉快,面对美景的新奇与感动,以及景观背后动人的故事传说……我这才意识到,有些东西是难以用相片记录下来的。
后来,有一次我带上相机出门“扫街”时,才真正领悟到拍照的真正目的。在老城区走街串巷,嗅到食物的诱人香味,原来是一家老字号肠粉店。走进店里,点一碟肠粉,看着老板在氤氲的烟气中忙活的身影,我忍不住举起相机按下快门。在老城区我又见到一家打制传统铜器的小店。循着“叮叮”声走过去,与老师傅打声招呼,好奇地看着打铜的过程。老师傅看着我专注的神情,露出灿烂笑容,于是我又按下快门。当我回家翻看这两张照片,我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又闻到肠粉的香味,又听到打铜的悦耳声音。
我这才明白,拍照只不过是给你一个观察体验的机会,而照片只不过是回忆的引子,真正的美好回忆在心中。
因此,拍照用胶片机还是数码相机又有何关系?照片的多与少又有何关系?只要用心体验,用心记录,定能写下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
回忆高考满分作文记叙文【四】
普通的虫,只有独自承受过破茧的苦,才能幻化成美丽的蝶;沉香树,只有自己承受过愈合伤口的痛,才能产出弥足珍贵的沉香;一个人,也只有在自己站起来之后,这个世界才能属于他。
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么只惊艳于她的美丽,却不知当初她的芽浸满了血和泪。”而如今成功的人,人们只惊羡于他们的成就,却不知当初他跌倒后站起来的痛苦。不经历命运的锤炼,不能锻造出强者;不独自克服命运的锤炼,也终不会成为强者。
那个在地坛中静静思考的人叫史铁生。一个在最狂妄的年纪失去了双腿的病人,一位在病房中无数次想到了死的年轻人,当他在地坛中独自思考生的意义、参悟了死的真谛时,他的灵魂再次站了起来,于是,他拥有了全世界。“死是一个必然会到来的节日。”“生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生。”这位身陷轮椅之中而灵魂屹立不倒的作家,不可不谓之强者。
那位在山坡山带领村民们默默植树的苍颜老人是褚时健。在经历过那个动乱的年代,饱尝了囹圄之苦与老年丧女之痛后,已经再无什么能惊起这位看似普通老者内心的波澜。在看清了名利,看透了生活,看淡了生死之后,这位老人有一次站在了众人面前,倔强地要在荒山上种出橙子。后来,这种带着褚时健坚强与倔强的橙子,拥有黄金比例的酸甜与口感,被冠以他的姓氏——褚橙。只有褚时健亲手种下的橙树所结出的果实才被称为褚橙,因为那里包含了一种在打击之后又爬起来、甚至站得更高的精神。
那个身躯瘦小面容慈祥的黑人老者是曼德拉。正如种族歧视的火不能将他烧成灰烬,反而让他浴火重生,铸就了和平统一的南非的伟业一样;几十年在监狱中的惨痛经历也不能磨损他坚定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消除种族歧视的决心。在被仇恨所击倒后,这位南非首任总统选择带着宽容重立,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带领南非前进。
曼德拉说“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后再升起的高度。”人的一生也难免被困难所击倒,而人,只有在自己站起来后,这个世界才能属于他。
回忆高考满分作文记叙文【五】
第一次见着父亲的手,是在家中翻箱倒柜时无意寻着的一张照片上,那是在一九九五年的冬天,父亲与母亲结婚时照的。照片上的父亲,意气风发,蓄着当时流行的中长发,伸出去替人递烟的手干净而且自然,手背上晒得有些黑,但厚大而踏实,给人一种很有力量,很有精神的感觉。
我拿着照片端详了好一会儿,兴冲冲地拿去给母亲看,母亲看了有些惊喜,问我是从哪里找到的,没待我说话,她又感叹道:“看你爸爸那时候多年轻,现在都老了啊。”我指照片上父亲的手对母亲说:“看,那时候爸爸的手多好看,手掌又大,手指又长。”妈妈看了好一会儿,喃喃道:“那时候没干活,手当然漂亮,看看他现在的手成什么样了。”我本想去看看父亲现在手成何样,但终因事耽搁,竟也忘记了。
再次见到父亲的手,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同学不知从哪里学来看手相的游戏,一个个小半仙们拿起对方的手指指点点,神神道道的样子,也让我颇有些相信,回到家,拿起母亲的手煞有介事地替她讲解:“这是生命线,这是爱情线,这是事业线……”父亲坐在一旁看我替妈妈看手相,突然说要我也替他看看,我放下妈妈的手,慢慢坐了过去。伸手拿起父亲的手,触到他的皮肤的那一刻,我愣住了,那种感觉让我想起了戈壁滩上的胡杨树干,是毫无生机的枯树皮叠出的沟壑,充满了刺痛的粗糙感。我的心头涌上一股心疼,轻轻将父亲的手移到眼前端详,这是一只怎样的手啊,黯淡的肤色映不出一丝生命的光彩,因为常年与金属机油打交道,指甲里满是黑色的油渍,大大小小的划伤痕迹布满了手背,连手背上的伤痕都是黑色的,这油污已随他多年的劳动深浸了他的手,将他的手侵蚀得像一块锈迹斑驳的铁片,这手心里哪里还辨得出生命线的痕迹,几十条油污墨线纵横在生命线的上方,将他的生命线分割得七零八落,却也扩展得很宽很宽。我的眼眶湿润了,心疼变成了心酸,我亲爱的父亲的手,从光滑年轻到苍老可怖,这么多年的劳作,他却从未向我提及。
在泪眼朦胧中,我依稀看到了父亲在烈日下劳动的模样,他蹲在地上,手上满是油污,他面对着滚烫的发动机,他拧着细小的螺丝,他的汗滴进尾气的浓烟里,他的手背上,黑色的伤口上覆着红色。在严冬,他也不能停下坐在火炉边烤烤火,父亲说每一桩生意都是收入,每一次收入都不能放弃,为这个家,在严冬里,他也咬牙坚持着。手里拿着铁制的工具,冷得刺骨,他的手又冻得裂开了,如形容枯槁的老人奄奄一息。我的父亲,就是用他的这双手撑起这个家。
我吸了吸鼻子,我想对他说:“您的生命线很长,我愿意伴您终老。”
回忆高考满分作文记叙文【六】
夜,无边的黑暗,淅淅沥沥的雨滴,敲打着寂静的夜空。“穿越千年的眼泪,只有梦里看得见,我多想再看你,哪怕一眼”空灵、凄婉的歌声回荡在神秘的夜空中。我伏在窗边,闭上双眼,静静的回味着今天看的那本书——《有一种花叫不谢》。
该怎样形容那本书带给我的感触呢,精彩的书,好看的书有很多很多,却从没有像这本书带给我的感触是如此的震撼!前言中有一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目光无法抵达的远方,我们拥有心灵。”生活是一本厚厚的长卷,美丽、芬芳的花在竞相绽开,一朵又一朵,岁月一样的恒久、绵长,童话一样的神奇、美好。因慧心的倾听,世界会变得辽远而宽阔,世界会变得摇曳多姿,生命会变的充盈而厚重,人生会变得充实而幸福。
不知怎样描述我此刻的心情,丝丝的感动,丝丝的心酸,丝丝的哀叹涌上心头,在我的胸腔中发酵,发酵。一个女孩在我脑海中明媚的笑着,一个只有五岁的孩子,用她微弱的力量为置身于水深火热中的非洲儿童撑起一片天空。她是人们赞叹的“爱心大使”,她是“只要蚊帐协会”最小的“蚊帐大使”,她是才上一年级的凯瑟琳!她用自己瘦小的身躯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有了芬芳的心愿,就一定会向世界放出醉人的馨香。
在漫漫书香中,你带着周身的光芒,款款微笑,颦颦走来。“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是你最真实的写照。想象着你独守空房的画面,夫妻鸿雁传书、斗茶取乐的情境,独倚窗边回首往事时的愁容,我不免伤感起来。你再也回不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岁月,再也不会有“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的情趣。你苦苦追求的爱究竟是什么?
爱是什么?我想,没有人能用语言来形容,世界上所有聪明的人加在一起,也无法向一个感受不到爱的人说明。爱有很多种,面对每一个人的爱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于爱的定义也都不同。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始终坚信着,爱是一种花,它的名字叫不谢!
回忆高考满分作文记叙文【七】
回忆起童年时光,好像有一大半都是在姥姥家度过的。那是名副其实的老房子,有绣着喜鹊报春的布窗帘、涂着米黄色掉了皮的油漆剥落的木门和盖着花布的脚踏式缝纫机。一切都带着自打我记事儿起就安置妥当了的约定俗成,就和她的习惯叫法是“姥姥家”而不是“姥爷家”一样,无从问起。可回到这里,我总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
再次回到姥姥家,迎接我的还是那熟悉、亲切的味道。
屋子很干净。新添置的等离子电视让不大的客厅显得很新、很亮。姥姥坐在沙发上频繁地换着台,像个不知疲倦的小孩子。我记得原来那台频道不多的电视是爸爸买了搬来的,(我和哥哥曾经挤着小板凳废寝忘食地看三姨妈录的《还珠格格》。当时我俩有专用的小餐盘,上面画着小鹿、小熊和金黄金黄的阳光。如今,傻小子和小丫头都已经上了高中,不再会为谁坐板凳左边而大打出手了。
突然间,感觉屋里很安静,我这才发现原先的那台洗衣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崭新的乳白色全自动洗衣机,搂着衣服静静地转啊转。
不禁有点想念小时候。因为那时的我和哥哥姐姐都是可以肆意玩闹而不会受太多责骂的。年幼的我就曾在哥哥的指挥下溜进后屋,从床底下的纸箱里拿椰汁喝;踮着脚尖儿和姐姐从冰柜里抢雪糕。傍晚时分,我会在大浴缸里明目张胆地注入一大缸水。因为爸爸一会儿就会回来,带着几条刚钓来的活鱼。于是,在“人工池塘”里,出现了我把鱼甩来甩去的身影……
唯有弥漫了几十年的气味没变,那特有的暖暖的香。
我永远记得这老房子,记得她的每一个细节。灯绳还是那样别致:客厅的灯绳上挂了个袖珍酒瓶,大屋的灯绳上有个小药瓶,这样屋里再黑也能摸到,心里头踏实。小玻璃柜里还摆着巴掌大的大象和孔雀,那是已离去的姥爷当年用捡回来的贝壳粘出来的。
真的。这里处处都有我的回忆。拉开抽屉,里面还留着我练字的字帖和画水粉画时用过的干粉块儿,还有被我“蹂躏”得残破不堪的《新华字典》。玻璃夹板里有我从小到大的照片,狼狈的、生气的、大笑的,全是我成长的足迹。它们都静静地躺在那里,伴着书柜里泛黄的旧书页,散发出亲切的味道。
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人成长,也有人离去。岁月,静静地,都让这老房子藏了起来。那便是我记忆的味道,是我儿时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