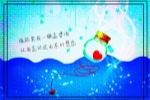听听妈妈的话作文【一】
雨是感性的`。丝丝润物却并不无声。听听,雨落在树叶上的沙沙声,青草池塘的处处蛙鸣。而我们身处城市之中,这些天籁之音,不是用耳朵去听,而是用心。
雨是传递信息的使者,是上天派她给大地带来问候。滋润土地,散发出阵阵清新的泥土芬芳。
听听,诗人笔下的雨的形态。“好雨知时节”是春雨如油最好的诠释。“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在秦观笔下雨又被带上了丝丝的愁。“清明时节雨纷纷”对已故亲人的祭奠,雨又带上了一层伤感的色彩。
下雨也许是睡觉的好时候,但我认为这是浪费。站在阳台上,窗外的景色,不外乎是那些隐天蔽日的楼房。唯独雨能够轻巧地穿过楼间的缝隙坠落下来。霎时间粉身碎骨,遁入土中,只留下一个印迹。
在屋中观雨是不过瘾的,走入自然中,任纷飞细雨打在脸上、肩上、发梢上。树上、天空已看不到鸟儿的踪迹。路上的车渐渐少了起来。行人的脚步加快了。天地一片寂静,唯有“嘀嗒”雨声。
长廊观雨又别是一番享受。听,那雨滴打在石阶上的声音,打在檐上的声音,打在草丛中的声音。如果此时在加上池塘蛙鸣。简直就是一曲超自然的交响乐。洗涤人的灵魂,净化人的心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雨洗落城市的喧嚣,洗去游子一身的归尘。
听听,那冷冷细雨打入心中,映入眼中。
听听妈妈的话作文【二】
人们总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现在想来是对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用自己的心眼看世界,去体会其中的含义,所以看到的也就不同了。
正如我们文中的人物一样:父亲的心里因为始终记挂着田里未干完的活儿,所以生性乐观坚忍的他也变得惆怅起来了;母亲因为心里惦记着田里的活,因为看到父亲的无奈,所以她的脸也因一天天缠绵不断的雨而越发惆怅了;而我们则因为看到每天对着雨发呆、脸斜成一个弧度的父亲和惆怅的母亲,所以我们无心去应和雨给我们带来的快乐,雨在我们眼中成了“该死的雨”、“令人讨厌的雨”。因为我们憎恨雨,期盼阳光,所以“我们真希望雨能马上停”,也同时把童年中的雨“调成了金黄色”。而这一切产生的源泉无非是因为他们的心。
禅语中有一句话说“不是旗帜在动,而是你的心在动。”是的,因为我们看世界看事物并非真正用我们的眼在看,而是用心体会的。所以即使一直被人们认为“贵如油”的雨,“滋润万物”的雨,因为打心眼里不愿意它的出现而变得可恶、该死起来。
但是如果它出现在干旱以后,那我想文中的人物又会有另一种表情了:也许父亲那粗糙的被太阳晒成黝黑的脸会因为雨的出现而再次倾斜成45度角;也许母亲也会因为它的出现而扫去连日来的惆怅,雨开始滋润母亲的心田,使母亲变得更加婉约动人;也许我们会因为雨的出现而变得欢呼雀跃,会在小水坑玩耍,会应和着雨点打击小花伞的节拍翩翩起舞,也希望它可以下个不停。那时的雨也许就不再是该死的、令人讨厌的了,也许会是可爱的、令人喜滋滋的了;那时也许在我们的童年记忆中,雨真的是金黄色的了。而这一切一切的“也许”,都是因为我们的那颗心啊!
听听妈妈的话作文【三】
绵长的阴雨抚慰了闷热的天气,潮湿得黏黏腻腻。然而这个学校的热却未曾褪去,每个人都躁动得不行。运动会后一个星期,不知是第几次在自修时,听见对面传出的此起彼伏的起哄声,和肆无忌惮的笑,整个学校仿佛都浮在半空之中。不禁想起朱自清先生的一句话:“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但是这样的热闹,却不是真正从内心发出的满足,只是笑容从嘴角溜过,还未流转过心底,就消失不见了。不仅仅是在学校,整个社会也同样叫嚣着,翻腾着,搅动着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滋生出躁动不安的情绪。年轻人静不下心去聆听,去发现,去收获。只是徘徊在真理的大门外,踱步着,从禁闭的门缝中妄图窥视,手却牢牢地钉死在大腿旁边。他们不知道的是:打开大门的方法,就沉淀在被搅动的湖面底下。
社会的浮华蒙蔽了年轻人的心灵,我们来不及思考,就将旧事物一股脑全部打破。民国时期,国难当头,人们头晕脑胀,就急着把西方的文化请进门来,把中国的优秀传统赶出家去。而如今,我们又被明晃晃的高楼大厦刺痛着眼睛,还没等大脑思考完毕,身体已经在“摧毁文化遗迹”的文件盖了印章。
渐渐地,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远去,每个人都在喧嚣尘世中如同行尸走肉。
我们已经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世界,却因为自身的浮躁而不幸失足,也难怪那么多老人摇头叹息,哀孺子不可教也。社会上对于90后、00后批判的声音,也并非全无道理。世世代代的人,错错落落地行走在山路上,前后已经拉得很长。年长的前辈经验丰富,果断而勇敢,领头开辟着道路。而我们踏着老一辈们踩出来的路,还因为犹豫不决陷入沼泽。这样的表现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偏见不是凭空产生的,是躁动不安的梦魇给我们的形象刷上了一层阴影。社会的浮华给我们心底点了一把火,我们自身却助长了火势的蔓延。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充实了我们的生活,也冲昏了我们的头脑。当我们沉醉在虚拟世界无法自拔时,躁动,也逐渐加快了侵蚀心灵的进程,将沉稳与耐心一点点剥离。于是,我们忘乎所以,忘记了聆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团泄不掉的火。
躁动也来源于对幸福的过度期待。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说过:“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么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学习的巨大压力将我们束缚在座位上没日没夜地埋头苦干,对于目标的过度追求更是把我们放置在了深不可见的悬崖边上。对于幸福的渴求,让我们加快步伐追赶,但一路上的磕磕绊绊促使我们萌生出逃避现实的想法。目标的高远让人无从下手,烦躁自然而然就从心底腾起。一旦开始怠惰,我们也就兜兜转转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一时的烦躁导致心不在焉的工作状态,接着加剧了工作效率的低下……来来回回在原地踏步,心中的方向逐渐迷失,幸福也就离我们更远了。
燥热摧垮了我们原本坚强的心理防线。冲动占據着心底张牙舞爪之时,我们脆弱得如同一张白纸。情绪化、片面化……一系列负面状态导致我们无法用冷静、全面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即使再简单的问题,经过焦虑的放大,也往往由原来的不堪一击变得坚不可摧。
冲动蒙蔽双眼,我们还会做出各种令人后悔的事。一辆运输货车在公路上侧翻,附近居民都被这从天而降的意外之喜冲昏了头脑,一拥而上,一哄而抢,却忽视了被围困在驾驶室里的司机。他们的行为让人心寒不已,这是对人性的漠视。这不仅仅是贪小便宜的心理在作祟,更是浮华社会下道德的缺失。
冲动不仅仅给个人的生活筑起一道屏障,还将给文学艺术带来巨大的灾难。碎片化的阅读时代衍生出的小说、段子等,以通俗爽快、随时阅读的优点撼动着经典文学的地位。在给我们带来娱乐的同时,也掩盖了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东西——文学。人们逐渐逃离这种生涩却最为优美的语言形式,渐渐的,忘记了来时的`路。现代青年作家简直是凤毛麟角,且经筛选留下的青年作家,比起莫言、刘慈欣等文化大家,他们的笔锋还是太浅显。文化记忆的断层,呼唤着我们回归一个理性思考的社会。
因此,生活需要一阵甘霖,来浇灭心中的火,平息时代的热。将我们的心灵从手机屏幕、网络小说中收回来,去触摸经典文学的美。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到“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一路由北看到南;从“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到“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梦回唐宋盛世开……那些所有的美的享受,都在一字一句中绽开。
这个社会或许不会因为我们一个人的言行而改变,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慢下来,用心去品味世界,用沉着冷静的心去浇灭生活的大火。对于幸福,或许我们无法做到贤人的宠辱不惊、云卷云舒,但至少我们要培养自己,拥有充足的耐心与自信。努力完成日常的一点一滴,幸福可能就会从天而降。
等等吧,慢慢行,一步一个脚印,让心平静。且歌且行,从惊蛰一路走到霜降。岁月并不快,有时只是我们的心被戳上加急的油印。
听听妈妈的话作文【四】
风吹过,叶落有声,沙沙沙,在我的心里,激起了波澜……
我在屋前的空地上,静静等待着他的到来。突然,呆呆望着前方的我,被身后突如其来的身影抱在了怀里。我吓了一跳,定神一看,欣喜若狂,大叫:“爷爷!”
“乖孙儿!”爷爷冲我大叫一声,然后把我托起来,高高举过头顶。
他的自行车上,捆着一大堆树苗,树***根被湿润的泥土包裹着。爷爷放下我,把树苗往地上一撂,向空地间走去:“来,陪爷爷种树,好不好?”
我和爷爷从早晨忙到了中午,从中午忙到了傍晚。屋前面的空地上,多出了一棵棵小树苗。风吹过,一片片叶子落下,像穿着红舞鞋跳舞的舞女。叶子落在地上,沙沙沙,沙沙沙。
几天后,还是屋前面的空地上,还是我们祖孙两个人,爷爷在不远处弯下了腰,把一朵朵嫩绿的花苗按在泥土里。四周也不知从哪里冒出一片片绿油油的.青草,一朵朵淡白的,晶蓝的,粉红的花儿,在草地上若隐若现,为本来荒芜的空地增添了几种色彩,带来了一丝清香。
风吹过,花朵的叶子飘落,坠地有声,沙沙沙,沙沙沙。
慢慢地,树越长越高,草越长越茂,花越长越美。
慢慢地,我越长越大,越长越高,越长越壮。
慢慢地,爷爷越来越老,越来越瘦,越来越弱。
岁月无声,岁月无情,总是把我们身边最珍贵的东西带走,以提醒我们没有得到的太多了。
奶奶生病了,爷爷回老家去了,丢下了我和这些伴我多年的小树小花小草。
不久,爷爷去世的消息传入我的我的耳畔。
我哭成个泪人,甚至晚上说些胡话。我整整几个月都没从正门出家门,生怕看见门前爷爷种的植物。
一次,可能是太想念爷爷了,我从正门走了出去,可毒辣的太阳并没有照到头顶,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阴凉。放眼望去,绿油油的草坪中点缀着花儿,一棵棵郁郁葱葱的树带来一片阴凉的天地……
风吹动树叶,一片片黄叶在风中凋零,扑向大地。它静默无声,可是我却仿佛听到了爷爷的声音。
回首,倾听叶落的声音,好似爷爷对我的倾诉……
听听落叶的声音,浓浓的爱溢满心头。
听听妈妈的话作文【五】
隔着车窗,山谷愈来愈深,空空茫茫的云气里,脚下远远地,只浮出几丛树尖,下临无地,好令人心悸。不久,黑黝黝的山洞一口接一口来吞噬他们的火车。他们咽进了山的盲肠里,汽笛的惊呼在山的内脏里回荡复回荡。阿里山把他们吞进去又吐出来,算是朝山之前的小小磨炼。
午后的阳光是一种黄澄澄的幸福,他和矗立的原始森林和林中一切鸟一切虫自由分享。如果他有那样的一把剪刀,他真想把山上的阳光剪一方回去,挂在他们厦门街的窗上,那样,雨季就不能围困他了。金辉落在人的肌肤上,干爽而温暖,可是四周的空气仍然十分寒冽,吸进肺去,使人神清意醒,有一种要飘飘升起的感觉。
他伸手去,摩挲那伟大的横断面。他的指尖溯帝王的朝代而入,止于八百多个同心圆额中心。多么什么的一点,一个崇高的生命便从此开始。那时苏轼正是壮年,宋朝的文化正盛开,像牡丹盛开在汴梁,欧阳修墓土犹新,黄庭坚周彦邦的灵感犹畅。他的手指按在一个古老的春天上。美丽的年轮轮回着太阳的光圈,推向元,推向明,推向清。太美了。太奇妙了。
感悟:这是余光中的阿里山的游记,风格干练,干练清爽。就像是“’隧道吞进鸣笛着的火车”,让你从内到外切身感受他的奇妙的旅程。阿里山秀丽,宁静的景色让人身临其境,尤其是那吸进去的清新而寒冷的空气,让我有种想去阿里山看看的冲动。那里不仅仅是秀丽的自然风光,同样有着象征历史记忆的物,余光中独特的写法让我记忆深刻,他借助八百多年的大树年轮来回溯历史,实在是妙不可言!让人感受到作者对大好自然风光的无比赞美之情。
听听妈妈的话作文【六】
绿油油的稻田里有许多青蛙,他们在那里忙碌地捕捉害虫。傍晚,青蛙们常聚在一起,进行大合唱,“呱呱呱”的声音在稻田上空回荡。
有一只小青蛙的叫声特别清脆响亮,大家称赞他唱得好。小青蛙听到夸奖,“呱呱呱”唱得更加响亮了。他还暗下决心,要做一名歌唱家,并刻苦练习,白天黑夜不停地唱。
小青蛙以为自己的歌唱得越来越好,大家一定会更加喜欢。没想到,青蛙们不愿和他在一起,总是避得远远的。小青蛙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肯定见我的歌越唱越出色,嫉妒了。”
大青蛙走过去对小青蛙说“唱歌只是我们的业余爱好,消灭害虫才是职责。你不努力多捕捉害虫,却整天唱个不停,伙伴们怎么会不反感呢?”
听听妈妈的话作文【七】
昨天去听余光中的讲座。余老八旬高龄,精神矍铄,修秀儒雅,一派学者风范,名家之态。仅仅2小时所论的中文与英文、文笔与译笔,对我来说是极有价值的启蒙,解答了我长久以来的疑问,也纠正了很多错误的观念。
讲座中,有节选《听听那冷雨》,配上江南丝竹,其味妙绝,听罢使人不禁潸然。现摘录如下: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
“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之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的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紧,那腥气。
“云绦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只像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亲,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再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更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荡气回肠。一瞬间,我在南洋的岛屿上失去了意识,恍然回到了烟雨的江南,我的家乡。幼时的幻境、去年的记忆,有相隔千年之感,如今回味,竟如太浓的酒香,叫人迷失了自己,丢掉了魂魄。
大家的一行墨,就是十年功。
世界上没有一样学问是不值得钻研终生的。即使钻研终生,又怎么够呢?
不认清自己的才华,是暴殄天物。而让自己那一点点天赋发挥出来,又怎是轻易之事?此间辛苦,吾辈断未尝过;却自鸣得意,实在可鄙。
今晨又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