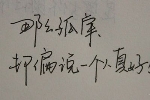我家的榆钱树作文【一】
一棵树和一只鸟儿是好朋友。鸟儿坐在树枝上,天天给树唱歌,树呢,天天听着鸟儿唱。
日子一天天过去,寒冷的冬天就要来到了。鸟儿必须离开树,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树对鸟儿说:“再见了,小鸟!明年请你再回来,还唱歌给我听。”
鸟儿说: “好的,我明年一定回来,给你唱歌,请等着我吧!”
鸟儿说完,就向南方飞去了。
春天又来了。原野上、森林里的雪都融化了。鸟儿又回到这里,找她的好朋友树来了。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树,不见了,只剩下树根留在那里。
“立在这儿的那棵树,到什么地方去了呀?”鸟儿问树根说。
树根回答: “伐木人用斧子把他砍倒,拉到山谷里去了。”
鸟儿向山谷里飞去。
山谷里有个很大的工厂,锯木头的声音,“沙——沙——”地响着。
鸟儿落在工厂的大门上。
她问大门说:“门先生,我的好朋友树在哪儿,您知道吗?”
门回答说: “树么,在厂子里给切成细条条儿,做成火柴,运到那边的村子里卖掉了。”
鸟儿向村子里飞去。
在一盏煤油灯旁,坐着一个小女孩儿。
鸟儿问女孩儿: “小姑娘,请告诉我,你知道火柴在那儿吗?”
小女孩儿回答说:“火柴已经用光了。可是,火柴点燃的火,还在这个灯里亮着。”
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
接着,她就唱起去年唱过的歌儿,给灯火听。
唱完了歌儿,鸟儿又对着灯火看了一会儿,就飞走了。
我家的榆钱树作文【二】
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吉鸿昌
在花团锦蔟的花园中有一棵郁郁青青的大树。大树枝上有一只灵巧的小鸟。鸟儿们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好朋友。
狂风呼号下小鸟躲进大树那茂盛青翠的叶丛间,享受关心和呵护,小鸟就以歌声回报这位仁慈的朋友。每天清晨伴随着花香馥郁小鸟站在树梢,晨曦的露珠闪烁着黎明的袅袅阳光。小鸟清了清嗓子唱起吗优美的歌来。就好像一个个音符在七彩的云霄中跳跃。大树则在一旁静静地聆听着。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北国的寒冬来临了。风,肆虐地咆哮着,小鸟还是依依不舍。最终小鸟离开了,鸟儿得飞到那没有寒冷的国界去了。
离别时小鸟还眷恋地依偎在大树旁说:"明年,我一定回来给你唱歌,等着我,呜......"小鸟噙着泪水去了南方,但很快春天又来了。小鸟兴奋地加快了回家的翅膀,可是鸟儿的朋友--树。没有了。只剩下那孤苦伶仃的树根。小鸟哭着问:"我的好朋友树去哪了?"
树根久久没有回答,空灵的一片寂静,小鸟知道树一定是被砍伐到工厂去了。于是鸟儿扑扑翅膀飞向工厂去了。小鸟听到"沙沙"的锯子声,鸟儿落在工厂的大门上问大门:"门先生,我的好朋友去哪了?请告诉我!"大门沉重地说:"大树被机器切成了火柴,我见过有个小姑娘买了一包。"于是小鸟又执着地飞到了小姑娘家又热切地问:"小姑娘你能告诉我火柴去哪了吗?"小鸟的眼睛水灵灵地眨巴,眨巴,小姑娘回答说:"火柴已经用完了,只剩下这点燃的油灯,还有那个火在烧。"小鸟迷茫地望着油灯上的火光闪烁,默默的望着。
小鸟振了振翅膀唱起了去年唱过的歌,灯火听着没有一丝风动。待小鸟将歌唱完,又默默地沉望了许久,然后流下一滴眼泪,飞走了,就这样飞走了。我知道鸟儿的心在哭泣,我想那心头索绕的必定是友谊。没想到做朋友竟是送给鸟儿最好的礼物。可是那伐木工厂......唉!可悲,期望没有下一次。至少我祝福鸟儿们。
我家的榆钱树作文【三】
春天又来了。原野上,森林里的雪都融化了。这时,我听到了一阵清脆的铃铛声。我以为那是小鸟回来了,我正准备迎接他,可是,我发现,那不是小鸟,而是伐木工人,我伤心极了。
伐木人下了车,渐渐地向我逼近了。接着,斧子一刀一刀地砍在了我的身上。我痛极了。但我强忍着,我告诉伐木人:“如果你们看见小鸟,请转告它,我被送到山里的工厂了!”伐木人满不在乎地回答我:“恩!”话音刚落,我便失去了知觉。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火柴加工厂了。我看见大门,忙跟他说:“门大叔,如果您看见小鸟,一定请您告诉它,我被做成火柴,送到山里的村庄去了。”门大树看了我一眼,嘴巴动了一下,好象在说:“恩”。
我还想嘱咐他一下,可我已被拉进车间里了,锔子在我身上沙——沙——沙地响着,不一会儿,我就被锯成了细条条儿,做成了火柴。果然,我被运到村子里,卖到了一个小女孩的家。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天天盼望着小鸟来看我。可是,火柴越来越少,可小鸟还是没有出现。
今天,是最后一根火柴了,火柴被小女孩点燃了。我感到失望和无助。正在这时,忽然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小姑娘,你知道火柴在哪里吗?”接着,我看到一只美丽的小鸟落到了我的面前。是它,正是它,是我以前朝夕相处的朋友,是我日夜思念的小鸟
。我兴奋极了!好想和它打声招呼,可是我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我觉得我的身体越来越热,我难过极了,小鸟认出我来了吗?我低下头,一滴眼泪流了下来。可这时,我却听到了世界上最好听的歌声,我的朋友唱歌给我听了。它盯着我看了许久许久才离开。
我望着它的背影,恋恋不舍地想和它说声再见,可我觉得,我已经快不行了,我的光越来越弱了,终于,火灭了。
我家的榆钱树作文【四】
----前言
小时候,拥有的那些美丽从来没有感觉到可贵,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们会悄无声息得被时光丢弃。长大了,偶尔捡拾起一片童年的记忆,竟是欣喜不能,如获至宝,甚至喜极涕零。这感觉,只有穿过了几多风雨沧桑,正在渐渐老去的我们才有那么深刻的感触,不是吗?
周日,带女儿去公园。行至入口处,不经意抬头的一个瞬间竟然发现了榆钱儿。那是多么熟悉的榆钱儿啊,却仿佛又显得陌生了许多。明晃晃的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只好快速换了一个角度想要认认真真看看这是不是我记忆里久违的榆钱儿,将脖子高高仰起,一遍遍端祥着,然后踮起脚尖想要摘一串下来。
”妈,快点走啊,你在干嘛呢?“女儿在前面急不可待地叫着。”宝贝,妈看到榆钱儿了,真的是榆钱儿啊!“我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女儿瞪大了双眼:”什么是榆钱儿?能吃吗?“我连连应她:”能,能,能,我们小的时候还用来做菜呢!可好吃了。“女儿一个剑步飞奔过来。
那树太高,我怎么也够不着它的枝桠,正好走过来几个约摸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她们看我着急的样子,笑笑说:”太高了,要不咱也摘一些下来吃。“女儿悄悄附我耳边问:”真的能吃吗?“这小丫头还不信她妈妈的话,我大声地又一次对她说:”真的能吃,小时候在你姥姥家可多这东西了,我们常常上树来摘下做成菜吃。“一旁的老太太也附合着:”是啊,做菜可香哩。“女儿听了便让我摘一片给她吃。
我来来回回徘徊着,舍不得离开,嘴里还不停念叨:“怎么往年来的时候没见着呢?是来的时间不对吗?”女儿看我这样子,就乐得不行。她说:“妈,摘不下来别摘了,你看,前面还有许多呢,咱往前走走,那里,那不是榆钱儿吗?你至于那样稀罕?”
或许,我稀罕的并不是榆钱儿本身,而是那些带着榆钱儿的童年快乐。
母亲住的巷子或许不能称之为巷子,因为我们临山而居,也因为门前有一大片的空地,还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土坡,母亲的家住在半山坡上。那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直至现在曾经那一排的人家老死的老死,搬走的搬走,唯有父亲,母亲和隔壁一个守寡的七大妈,还有大片大片的废墟单调而和谐地存在着。
母亲有一双勤劳的手,也有一颗慧质兰心,她能将贫瘠的土地栽种成一片热闹的春天,她守着那一片清静安然地过着她与父亲的春秋冬夏,我曾笑着于母亲说:“妈,别嫌这里孤独寂寞,这里可谓是一片桃花源!”
母亲笑笑,不再语。
其实,那里也曾经热闹过。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些陈旧的老房子里也酝酿着丰满的故事,那些与我一般大小的孩子们曾经与我一起在晨风里奔跑过,也在落日里笑闹过。
七大妈家的那棵杏树我们不知道偷着上去多少次了,还有东面那个光棍尹大爷的红枣树我们也是总瞅着主人不在家时爬上去用棍子不停敲啊,打啊,直至红枣落了一地,叶子也落了一地,为了不让他发现我们又慌乱地将叶子扫在别处,把脚印抹了个干净。
还有,二大妈家的二女儿又被她爹打了出来,估计是又喝多了,他打起女儿来总是没头没脸的,长辈没个长辈样子,女儿也从来不喊他一声爹。夏日的黄昏,大哥二哥和一群猴子们又跑到地里摘回麦穗烤着吃了,瞧他们小小年纪做这个可真在行,几块砖头垒起来一个小火灶,然后小脑袋凑一起争着烤,不行,我也得跑过去凑热闹。
人们下地干活累了一天,也只有晚上这会儿是可以坐在一起聊聊的,看他们各自端着饭碗就跑了出来,自然而然凑到一起,赤着脚片子,或
圪蹴(蹲) 或直接坐在土地上说着东家的长,西家的短。耳边是不甘寂寞的蟋蟀叫个不停,我们那些小孩子就跑来跑去争来抢去,笑声响满了整个小山村。很迟很迟了,连月亮都有点犯困了,大人们才各自散去,尽管我们还舍不得在黑暗里安静下来,可架不住大人们一声声地呼唤。
而今,那里显得异常安静,七大妈的腿脚极其不利索,就算再有孩子们去偷她家的杏儿,相信她也定是追赶不上,可是,那些偷过她杏儿的孩子们都早长大成了人,像长了翅膀的鸟儿一样飞得很远很远,尽管她的杏儿年年还是那样缀满枝头,却再不及那些年甘甜诱人。
三叔也搬到了新房子,门上常年挂着一把生锈的大铁锁,而爷爷却已一捧黄土成了凭吊,再不见他徘徊来去从父亲的家到三叔的家,再不见他紧皱的双眉,听不到他边走边说着三叔家的孩子真捣蛋。还有姨奶家的那个带点傻气儿的五儿媳把她的公公一砖头拍得上了吊,从此那个红火热闹的家就没了生气,最后,人去屋空,也不过是一把铁锁尘封了厚厚的记忆。
那些老屋子,陈旧得堆满了故事,却也陈旧得再直不起腰身。
二大妈家的二女儿也已年近不惑,她的那个凶恶的爹早已做古,就连她家的墙头也烂成了一堆泥。可我清楚记得那一堆烂泥的下面曾经长着一棵老榆树。
那老榆树长得甚是喜人,也许它比我年龄还大,反正自我记事起它就很高很大,也很壮。虽然它只是生长在二大妈家的墙角,可左邻右舍无不宠爱它。
榆钱满树的时节,她们端着一个小盆子站在树下聊天,我却麻利地爬上树去摘下一缕缕榆钱儿,再听她们夸我几声那便是心里偷着乐个没完,我一边摘,一边吃,等到家家户户的盆子都放满了,母亲催着快点下来,我却站在树上扮着鬼脸就是不下。
她们还在聊着那些碎七碎八的事情,什么谁家的孩子被打了,谁家的庄稼被水淹了,或是谁家地里的草长得比庄稼还旺,要么是谁家的媳妇又和婆婆吵架了,看她们说得一个比一个带劲儿,太阳眼看着都落到西山根儿了,依然还是舍不得分开。
这时,那个二大妈的男人回来了,大老远看见,她就忙着说要去做饭了,于是众人散去,我也忙跳下了树。
跟着母亲回到家里,就只等她做上香喷喷的饭菜了。母亲嘱咐我把榆钱儿里的细小的树枝棍捡了出去,然后她将土豆洗净,削皮,用擦板擦成丝,再将榆钱儿洗净,然后就是锅里放上油,调料,一起烩着。不一会儿,锅里就会飘出淡淡的香。
想来,很多年不曾闻到那个味儿了,虽然那是多么朴素的菜,可谓粗茶淡饭,可如今思来,却远比那些山珍海味更可口。
乡愁,是一种镶嵌在生命里的味道,乡愁里那零零星星的记忆就如流淌在生命里不息的血液一般,不是吗?
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果然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榆树,个个挂满了榆钱儿,鲜嫩鲜嫩得真是诱人,可幸,有一棵随手就可摘了下来,我急切地放进嘴里,哦,真香,一如儿时的味道,甜甜的,绵绵的,柔柔的。
女儿也要,我便喂她嘴里,可她只是说:”就那样吧!没有多么香啊!“
难道,一样的榆钱儿,于我,吃进去的更多的有着生活的味道?更多,有着几缕乡愁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