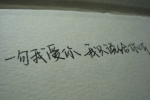叙事作文的评分量表【一】
老A说过,有些地方去过就不会忘记。
我去到地方并不多,但我依然信仰每一个地方我都会记住。
去到重庆几次,记得有一个地方叫石碾盘的,那下车的地方有一家叫作高佬牛肉面的面馆,至于为什么不叫高佬面庄或是高佬庄,就无从知晓了。有那么几天,我黑白颠倒,开始如鬼魅一般昼伏夜出,所幸高佬二十四小时营业,白日睡去,夜间还能到这里,吃一碗面或是米线,再要一杯纯净水,然后熬通宵,写自己的稿。夜间到这里吃东西的人,无非四种。一、致力于麻将的,二、努力上网却挨不住饿的,三、生活白无聊赖,靠着父母供着的无业青年,他们对夜生活充斥着极大的兴趣,不到凌晨四、五点断不会回家,四、即是工作一直到深夜的公司职工。一、二、三是可耻的,而我就在这群可耻的人中愈加可耻地用自己的文字光冕堂皇的浪费光阴。在朋友的文字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浪费光阴本不是错,错的是明知自己在浪费光阴,却依旧装做懵然不知。我或许即是这种人罢?
坐在店里,店里店外皆是不绝的过客、路人,我平静地看着他门南来北往,匆匆行色。
我出了高佬沿着人行道一直走,路过一个三岔口,未作停留便向右拐,经过外观几墩石柱很似圆明院的沙坪公园,接着上桥,那是一座很小,小得我已记不得名的桥,只记得桥下有火车在进站出站,向南向北。我路过的时候,一似乎眼瞎而戴着墨镜的老先生正拉着二胡,是名曲《二泉映月》,我听了许久,竟迷离地将手伸进口袋,拿出5元钱,走向他面前放钱币的小桶,突然曲声戛然而止,老先生估计越吹越没了兴致,对数钱兴致勃勃,摘下墨镜一张一张小心翼翼的数钱,立马转身,把手缩回口袋,心里暗庆没有失财。
去到八中,大门不让进,我看了看一旁不高的铁栅栏,毫不犹豫的跳了进去。我想八中的保安可能比较懒,甚至懒得理我,见我进去也假装没看见,因为若他当作看见,势必要叫我出去,而我势必会跑,他若不追势必没面子,追又势必得绕一大圈,等他绕到,我势必又早跑得无影无踪,而他不仅徒劳无功,且势必更没面子,经过一阵势必,他选择了沉默是金。
八中的内部结构,占地面积与我们校相差无几,只是人家操场是塑胶的,而我们是水泥的。他们的.教室设施也明显较为先进,一个班人数也较少,不似我们像搞帮会的――多多益善。转了两圈,我终明了什么叫浪费人力财力物力,就他们那五、六层的教学楼,竟也弄一电梯,真不把钱当钱花,不过也充分体现了,恩!八中人都很懒。
走来走去,只见到初一和高三的教室,我就十分纳闷,莫不是八中人个个IQ二百五,读完初中直接跳级读高三。但转想不太可能,唯一可能就是他们为节省门牌把初中统一为了初一,高中为高三,不过想想够呛的,读三年才升一个级。
路过一个路口,看见四、五青年站在一起,各自叼着烟闲聊。我心里暗自庆幸数数是从小数到大,否则这四五青年立马升级成了五四青年,多么迅速,且极具跳跃性,四五青年怡然自得地向空中吐着烟圈,样子似乎童心未泯,还互相比较,恩!我的要大些。
看了四五青年后,我特郁闷地想找个无人的地方坐坐,无意间走到了街心公园,里面的人并不多,但每隔十米必有一对情侣,最后漫搠了半小时之久,才勉强找到一处可坐的地方坐下。行人三三两两地走,让我忽然觉得生命中真的过客许多,不曾停留。日后,定要写个什么记住这个城市,也记住这些个过客,就命名为重庆行者记,之后若再写,就叫重庆者行记,再次就叫重庆记行者,(怎么听着像捅了猴子窝似的)但定不可叫重庆记者行,那会产生歧义,产生误导作用,或许就存在无数误导,误导我行色匆匆,误导我从生命中过客。
风过无痕,却已吹过。于是,起身继续地向前行走,去和更多的人相遇、相错。
没有人会去记住一个没必要记住的人,但是我会,因为总得要一个人去记住,不是你,便是我。
离开的前一晚,我出去走走,路过那座小桥,老先生没在,桥下的火车,不在向南向北,进站出站,全都静静地停在那里。走过八中,里面很暗,只在昏暗的路灯下有那么一小块光明,大门紧锁,寂静无人。今天,有些冷四五青年不知去到了哪里,不知是否依旧会叼着烟,比着烟圈。街心公园的情侣都已不知去到何处,只剩一位老人和我,老人在不远处发呆,我在昏暗的街灯下写着自己的文字。记得过去听收音机,最喜欢听中午十二点整,丢丢主持的音乐贺卡和晚上十点、不知谁主持的清风夜语。
今夜,我也在清风夜语,只是我的语只在纸上。
叙事作文的评分量表【二】
我在乡下度假,和几位可爱的小朋友在莺歌的尖山上放风筝,初春的东风吹得太猛,系在强韧钓鱼线上的风筝突然挣断了它的束缚,往更远的西边的山头飞去,它一直往高处往远处飞,飞离了我们痴望的视线。
那时已是黄昏,天边有多彩的云霞,那一只有各种色彩的蝴蝶风筝,在我们渺茫的视线里,恍愧飞进了彩霞之中。
“林大哥,那只风筝会飞到哪里呢?”小朋友问我。
“我不知道,你们以为它会飞到哪里?”
“我想它是飞到大海里了,因为大海最远。”一位小朋友说。
“不是,它一定飞到一朵最大的花里了,因为它是一只蝴蝶嘛!”另一位说。
“不是不是,它会飞到太空,然后在无始无终的太空里,永不消失,永不坠落。”最后一位说。
然后我们就坐在山头上想着那只风筝,直到夕阳都落到群山的怀抱,我们才踏着山路,沿着愈来愈暗的小径,回到我临时的住处。我打开起居室的灯,发现我的桌子上平放着一张从台北打来的电报,上面写着我的一位好友已经过世了,第二天早上将为他举行追思礼拜。我跌坐在宽大的座椅上出神,落地窗外已经几乎全黑了,只能模糊的看到远方迷离的山头。
那一只我刚刚放着飞走的风筝,以及小朋友讨论风筝去处的言语像小灯一样,在我的心头一闪一闪,它是飞到大海里了,因为大海最远;它一定飞到最大的一朵花里了,因为它是一只蝴蝶嘛;或者它会飞到太空里,永不消失,永不坠落,于是我把电报小心的折好,放进上衣的口袋里。
朋友生前是一个沉默的人,他的消失也采取了沉默的方式,他事先一点也没有消失的预象,就在夜里读着一册书,扭熄了床头的小灯,就再也不醒了。好像是胡适说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他采取的是另一条路:宁默而死,不鸣而生,因为他是那样的沉默,更让我感觉到他在春天里离去的忧伤。
夜里,我躺在床上读史坦贝克的小说《伊甸园东》,讨论的是旧约里的一个章节,该隐***死了他的兄弟亚伯,他背着忧伤见到了上帝,上帝对他说:“你可以辖制罪。你可以辖制,可是你不一定能辖制,因为伊甸园里,不一定全是纯美的世界。
我一夜未睡。
清晨天刚亮的时候,我就起身了,开车去参加朋友的告别式。春天的早晨真是美丽的,微风从很远的地方飘送过来,我踩紧油门,让汽车穿在风里发出嗖嗖的声音,两边的路灯急速的往后退去,荷锄的农人正要下田,去耕耘他们的土地。
路过三峡,我远远地看见一个水池里开了一片又大又自的花,那些花笔直的从地里伸张出来,非常强烈的吸引了我。我把车子停下来,沿着种满水稻的田埂往田中的花走去,那些白花种在翠绿的稻田里,好像一则美丽的传说,让人说不出一种落寞的心情。
站在那一亩花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花,雪白的花瓣只有一瓣,围成一个弧形,花心只是一根鹅黄色的蕊,从茎的中心伸出来。它的叶子是透明的翠绿,上面还停着一些尚未蒸发的露珠,美得触目惊心。
正在出神之际,来了一位农人,他到花田中剪花,准备去赶清晨的早市。我问他那是什么花?农人说是“马蹄兰”。仔细看,它们正像是奔波在尘世里答答的马蹄,可是它不真是马蹄,也没有回音。
“这花可以开多久?”我问农人。
“如果不去剪它,让它开在土地上,可以开个两三星期,如果剪下来,三天就谢了。”
“怎么差别那么大?”
“因为它是草茎的,而且长在水里,长在水里的植物一剪枝,活的时间都是很短的,人也是一样,不得其志就活不长了。”
农人和我蹲在花田谈了半天,一直到天完全亮了。我要向他买一束马蹄兰,他说:“我送给你吧!难得有人开车经过特别停下来看我的花田。”
我抱着一大把马蹄兰,它刚剪下来的茎还滴着生命的水珠,可是我知道,它的生命已经大部分被剪断了。它愈是显得那么娇艳清新,我的心愈是往下沉落。
朋友的告别式非常庄严隆重,到处摆满大大小小的白菊花,仍是沉默。我把一束马蹄兰轻轻放在遗照下面,就告别了出来,马蹄兰的幽静无语使我想起一段古话:“旋岗偃狱而常静,江河竞泣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而生命呢?在沉静中却慢慢的往远处走去。它有时飞得不见踪影,像一只鼓风而去的风筝,有时又默默的被裁剪,像一朵在流着生命汁液的马蹄兰。
朋友,你走远了,我还能听到你的蹄声,在孤独的小径里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