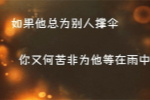秋季写景作文800字【一】
飘雪之晨,我倚窗而坐,柔荑托颚,静观雪景。雪零星落下,如窗花飘零,而天公并不作美,接之遂化无;似美人,伊着一袭素衣,袅娜身姿舞,款款而至;如无香之梨花,但雪因无香,平添了几分素净,安宁,淡雅,清新,似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娥。
至院,见雪洒满地,即止。不忍心踏之,如此美好之物,怎能忍心践踏或蹂躏?静静立着,雪也不间断地落着,雪与我,似是已化进这冬季里了。雪伴我,无孤独之感,倒是添了些许欢愉。悄悄地,我们谁也不言,生怕坏了这静。我们认为,只须这样久久凝视,足矣。
梅开之夜,我悄然走进阳台,刚跨了门槛,便闻见梅香袅袅,梅香淡然入鼻,浓烈却不失淡雅。香气在空气中久久萦绕,我跟着香气走进,原是梅花,虽望不见她,却能想象出她一人于丛中独芳自开的情境,那种不惧,不畏,不怕的深情,只淡然一笑而过。她的婀娜多姿的身影湮没在黑夜里。
正这样想着,疾步跑去开了灯,梅花的芳颜便尽现。不得不感叹她的美,动人,让人从心底里觉得她是极美的。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雪与梅,天公之佳作。墙隅之处,梅独开,雪伴她,黯然落下。氤氲香气于空气中酝酿,久久方才入鼻,却浓浓久不散去。再转眸望雪,洁白无瑕,至纯至真,若有玉与其同色,那必然是玉中极品。
雪与梅,互相伴之,相得益彰;雪配梅,无约定,却如已约定一般,每每冬季,一同出现,同为冬之佳品,皆于丛中笑;雪同梅,不离不弃,即使淡然消无,也定会在下一个冬季同时翩然而至,永远不弃。
秋季写景作文800字【二】
来到洪湖边,最先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荷叶和荷花,密密层层,仿佛湖面上铺有一层地毯,毯子上绣满了盛开的花朵儿。在湖边走了一会,老天爷下起了大雨,我们躲在茅草亭子下,看着雨水打在荷叶上,水珠仿佛是一个个小巧可爱的精灵在荷叶上跳过来跳过去。荷花也像喜欢这场雨似的,像个穿着舞裙的仙女在湖中跳起欢快的舞蹈。
洪湖荷花的种类可多了!“东方红”、“白鸽”、“红双喜”、“白千叶”?我最喜欢的是“白鸽”,它是很纯净的白,真像一只只白鸽子落在绿叶中,随时都会飞走一样。
你知道街上推板车的'奶奶卖的莲蓬小时候是什么颜色吗?嘿嘿,我看见了,所有品种的莲蓬小时候都是黄色的。
秋季写景作文800字【三】
一阵如雨般的急响,“哗啦啦”,银杏树上的果实被打落下来。我站在路口吹响手中的果核,声音微弱而清越,响成了一片风景。
我在这声里雨里笑着去追远方的风景。
……一株开满了细碎白花的柠檬树,满树都是微甜的清香气息,小米似的白色花瓣在木吉他的弦歌里洒了一地。
吉他断弦,初醒的我怔忪了许久,手中握着的书还翻在写三毛的柠檬树的一篇文章的那一页。那棵屋顶上的柠檬树是三毛拥有的风景,而把我把它收藏在梦里。
“哗啦啦”,银杏树上果实急落的声音,是那种世俗的聒噪。
妈妈在和暖的阳光里走进来叫我,“去看看那些果子吧”,她那好奇和兴奋的音调,将我“我们怎么不种一棵柠檬树呢”的建议扼在喉咙里。
我趿着鞋出门,看到一片杂乱的浅黄色和翠绿色错杂的地块,带着长柄的果实纷纷落下来,有的还摔破了皮,溢出少许鹅黄色的浆液。我厌恶地皱着眉头蹲下身来触摸皱缩的皮层,指尖上一层淡淡的粉末。它太丑陋了,让我像触电似的缩回了手。
我有些后悔那个美梦的中断,后悔我没把那个建议说出口。
“我小的时候,拿这种果核当乐器呢。”妈妈忽然走过来半蹲在我身旁,提起一只完好果实的柄。微笑着的她似乎已沉浸在回忆里,丝毫没有顾及我迟疑的眼光。
不由分说地,她捡了几颗饱满的果实,放到水龙头上冲洗起来,水流像快刀剥去腐肉一样一层层剥下果肉,最后还剩下的果核呈木色,向上了釉一样光滑,细小剔透的水珠顺着纺锤形的壳滚落下来,让人想起远古时的埙和翠色的木叶。
我不禁也想尝试,仔细洗好其余的果核,将它们逐个摆在窗台上晾晒。细碎的光线灌进果核的纹路里,流成一道道浅金色的沟槽,此时我竟觉得它们有些美丽。隔着浅茶色的玻璃可以看见所剩不多的果实混着银杏叶继续如雨般落在地上,浅黄和翠绿杂乱地交织着。
对着错杂色块生硬的厌恶渐渐变得柔软起来,我将卡在喉咙里的那句话又咽了回去。
“哗啦啦”,这也许是最后一茬果实了吧。
我在声里雨里转过身来,轻轻吹着手中的果核,它呈木色,有微苦的味道,比微甜的柠檬香气更加实在。
每个人都在远方藏着一片风景,或许是一株柠檬树,或许是一把木吉他。但它们只适合根植于远方。而在近处,我只要一回头,便能看见身边翠绿嫩黄如雨般急落。
这些是银杏果,又不只是这些东西。
它质朴,它在身边真实存在,它成熟坠落的时间清晰可感,它的果核能唱一首清越的歌,歌声在你身边响着,总不散去,渐渐地响成一抹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