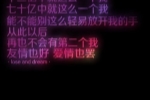传承红色基因作文500到600字【一】
是父亲,鼓励我茁壮成长;是父亲,帮助我度过难关;是父亲,引领我不断进步;是父亲,让我爱的温暖。在我心中,父爱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从点点滴滴的小事中自然显露出来的。
那是一个寒冬腊月的傍晚。父亲跟往常一样骑车接我回家。大风狂哮着迎面吹来,路边的行人都缩紧了脖子,空旷的马路上只有父亲弯着腰,带着我,艰难地踩着自行车。尽管爸爸像一堵墙似地挡在前面,我在后座上还是被寒风吹得瑟瑟发抖。
不一会儿,雪从阴云密布的天幕中疾驰而下。“太冷了,咱先找个地方暖和一下吧!”我用发颤的声音说。父亲急忙停下车,摸了摸我的手,又看了看天。“这雪一时半会儿恐怕停不下来,咱们再坚持一下好不好?很快就到家了。”说着,父亲脱下外套披在我的身上,又骑上了车。在父亲温暖的大外套下,我终于觉得身上有了暖和气儿。但我忽然想到,爸爸帮我挡风,还穿这么少……。于是我在风中大声问:“爸,您也冷吧,外套还是给您吧?”“儿子,老爸骑车热着呢!”父亲在风中大声地回答我。
雪越下越大,风越来越猛。车轮开始打滑,我们在风雪中显得寸步难行。我站起来,搂住父亲的脖子,手碰上了他的耳朵,啊,可真凉呀!可是,当我顺着父亲的脖子往下摸,竟然湿漉漉的。原来,父亲已累得满身大汗。路灯下,父亲额头上那晶莹的露珠,不知是雪水还是汗水。
时间好像凝固了,感觉过了几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家门口。
打开门,回到温暖明亮的家。这时,我突然被父亲的脸吓了一跳。那是一张跟平常很不一样的面孔:嘴唇乌青,耳朵通红,鼻尖发亮,脸上多了好些皱纹。我第一次发现,父亲已苍老了许多;我第一次注意到,父亲的头顶已被一圈白发包围了起来;我也第一次体会到,父亲为了儿子根本顾不上自己。我的心在微微颤动,鼻子一阵发酸,眼泪只想往眼睛里涌。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也是父亲教我的。我默默走过去,紧紧地扑在父亲的怀里,父亲则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背。
父爱就是这么微小而无言,却温暖而伟大的。从此以后,只要回想起那个风雪交加的傍晚,我的心中总是涌起一股春天的暖流。
传承红色基因作文500到600字【二】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稍微改善了一下笔记方法,就是阅读四十到五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回翻kindle书签并做关键事件与词语的摘录。(其实是因为边读边记磕磕巴巴不太爽
上一次阅读到孟德尔,而短短数十年间“基因已从植物学实验中的抽象概念演变为操纵社会发展的强大工具。”美国有些州甚至立法进行绝育手术,将无辜的女性统一收容,“只要行为、意愿选择或者外表超过人们接受的准则,那么他们就会被划入这个可怕的怪圈。”美洲的种族净化甚嚣尘上,1936年欧洲的遗传清洗活动也不甘示弱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这中间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时间机器》,描述了近亲繁殖并且选育后留下的孱弱未来人类种群,《人猿泰山》则坚信虽然生长环境与教育缺失,高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基因仍然会带来聪慧与美好品质。忍不住想起苏联时期著名反乌托邦作品《我们》中的“母亲标准”和“父亲标准”,虽然原著意在讽刺过度标准化的社会,但是在基因选育方面异曲同工。(不知道现在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和这些历史有多少关系?)
在摩尔根的果蝇实验带来基因连锁、基因互换、显性遗传图谱等概念后,遗传学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多基因遗传的研究也补足了孟德尔理论在人类遗传性状呈平滑的钟形分布方面无法解释的不足。
作为一个阅读量很少并且不怎么读历史的人,万万没想到看一本基因历史书还能看得心潮澎湃,基因发展的抽丝剥茧真如同一本推理小说。
传承红色基因作文500到600字【三】
在达尔文之前的人类,都觉得自己是神的子孙,或者是跟神有某种关系,然后达尔文横空出世,拿着一堆动物的骸骨和化石,对狂妄自大的人类说:别做梦了,咱们不过是猴子的亲戚而已,咱们的老祖宗包括地球上一切卑贱的生物,咱们也终将被更高级的生物所代替。
达尔文的这些话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也是很难接受的,看看日本人就知道了,让他们承认自己的爷爷辈曾经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都那么难,更何况承认自己是猪狗的后代呢?
不过《自私的基因》的作者又给我们提供了另一条思路,当然作者自己也说,这种新思路甚至在达尔文时期就已经初现端倪了,什么思路呢?那就是,我们只不过是基因制造出来的保护壳而已,世间的生物只不过是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壳,大家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助基因繁衍下去。
说得更简单一点儿,作者认为,咱们其实就是一辆坦克,而驾驶员就是基因。
不太好接受是吧?没关系,如作者所说,这只是一种思路而已,当然他觉得这种思路更加符合事实。
暂且接受这个观点,看由此出发能推导出什么结论。
首先,这个理论肯定了人类在生物界的特殊性。因为人类之前的进化,全是依靠基因的突变,这种方式漫长而无效率,而人类产生之后,人类就可以利用杂交等技术使得进化变得有方向性了,而更进一步,人类可以改变基因,创造出任何生物。
这个结论听上去有伦理问题,而且也很可怕呵呵,没关系,后面的结论大多是比较有意思的。
基因的寿命无限长,而它的载体却没必要很长。这是对生老病死的一种解释,因为只要有繁殖,基因就可以把自己延续下去,而我们--基因的载体,只要完成了这个任务,那继续活下去也就没啥用了,所以当人完成了抚养未成年人的任务之后,就要面对死亡。
基因不会直接控制我们,而是生产出我们之后听之任之,就像程序员与电子游戏,程序员编出来游戏后就不做什么大的修改了,只要把它放到市场上就好,成功的游戏留在市场上卖钱。
一个社会的领导者总是少的,群众总是多的,厉害的人总是少的,受欺负的总是多的,因为基因博弈论证明,少数鹰派和多数鸽派是种群的最佳搭配方式。
传承红色基因作文500到600字【四】
我们从来不知道最早的英国人到底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在潮湿的岛屿上,创造出了王室和政府理论、财产与契约的理论、法律和税赋的理论,这些理论改变并最终提升了我们,不列颠岛曾是罗马的行省,伴随着罗马的衰老,公元410年罗马军团被召回帝国首都后,不列颠行省三面受敌(西是爱尔兰部族、东面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北面是皮克特人),只能自求多福。
在整个5世纪,来自现在德国、丹麦和低地国家的人作为英国人的先辈开始大量定居下来。到6世纪末,一共有12个王国,后来兼并为7个。
到8世纪末维京人入侵,7国合并为4国:诺森比亚、麦西亚、东安格利亚和韦塞克斯北方维京人一点一点征服了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吞并了东安格利亚,在诺森比亚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蚕食了一半麦西亚。当他们最终觊觎韦塞克斯时,被阿尔弗雷德国王击败。
在定义一个民族的地位时,除了语言,民族意识是一个很重要标准,事实上,一个民族总是需要借助一个“外国身份”的对照来形成,比如,对意大利人来说,奥地利人就是外国身份9世纪的英吉利人,他们面临的外国人就是维京人到10世纪时,英国完成了英格兰的民族统一,形成了完整独立的民族国家,将其他欧洲国家远远甩在了身后,当然,英格兰的民族融合体现为一个过程,边界也具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读后感·盎格鲁—撒克逊人逐渐向西扩张,被征服的不列吞人被称为“陌生人”或者“外族人”,后来被称为“威尔士人”,威尔士人的原意就是“陌生人”或“外国人”。
历史学家苏珊·雷诺兹说:“英格兰王国的居民习惯称自己为英国人,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不是一个用连字符连接起来的王国,而是国民认为它们归属同一个民族国家”
10世纪是这个早期英吉利国家的黄金时期:统一,富裕,依照法律施治,后来发展出了议会民主、司法独立和个人自由等,逐渐形成了区别与邻国的种种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