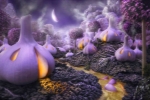写太阳升起的作文450字【一】
《太阳照常升起》这本书我以前读过,只是隔了这几年,印象有些模糊了,故事几乎完全忘却,所记得的唯有书的末尾,女人对男人说“要是能在一起该多好”,男人回答说“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
这段对话大概是很有名的,记得孙甘露在一篇随笔里引用过,而且那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的,因为《太阳照常升起》里那个男人没有性能力,所以他只能“想想”。
说实话,若不是孙甘露在书中提起来,我连这个情节也会忘记,因为以前我有一阵子把海明威的书都从图书馆中借来读了,一下子吃太多,囫囵吞枣,反而没有回味。
前些天我在扬州逛书店,看到译文出版社的《太阳照常升起》,就准备买回来重新读一下,但是买回来之后,细看这本书,首先就发现装帧设计很糟糕,居然是粉红色调的,有一条类似大红锦缎被面的花边(自从张爱玲的《小团圆》红了之后,上海出的文艺类书籍似乎都染上这种慵懒颓靡的媚俗气息了今天我看到一家服装店刚开张,标牌上居然也是大红锦缎被面,店的名字居然也叫“小团圆”)
还有呢,我不满意这个版本的译文,有些语气助词不很恰当,比如“那个罗梅罗还是个孩子哩”,类似的句子很多,破坏了作品中极重要的东西,语感。另外,这个译者的序文还要糟糕,一开始我读了两行就读不下去了,然后跳过直接读正文,正文读完了后,由于原作的魅力,我还不想离开这本书,就又翻到了卷首的“译者序”,“捏着鼻子”读完,简直都要吐了,这个译者用马列主义加上民族主义那一套评判方法来解读这本书,不仅仅是曲解,我甚至怀疑他根本没有读懂《太阳照常升起》……不过,看看序文的写作时间“一九八三年元旦于哈尔滨”,也就能理解一二了。
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在大战中负伤失去性能力,这个是全书的引子,但是这会让读者误以为杰克就是因为这个不能和勃莱特在一起,而事实上,杰克就是有性能力,也不可能和勃莱特长久的在一起,因为像杰克、勃莱特、比尔、迈克……
这些人是一些没有家园的“流亡者”,他们过着波西米亚式的放荡生活,而精神上也确实是“迷惘”的,为什么“迷惘”?我绝不同意译者序中所说的什么“资本主义危机”“帝国主义战争”“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之类的废话,的确,杰克是在大战中受的伤,但战争只是一个表征,真正起到关键因素的,还是现代性到来之后(这个是不管你是资本主义还是什么主义都要面对的问题),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人被迫离开了土地和家园,只能在世界上四处漂流,所以,当杰克这些人的“根”被现代之利刃斩断后,一些传统的价值观,生活状态,甚至是宗教信仰,也随之崩塌瓦解。
但是,在杰克的朋友之中,只有犹太人科恩是个特殊的例子,他对于女性的态度,对于恋爱和婚姻的态度还是比较传统的,所以在杰克一伙人之中,科恩才显得那样不合时宜,甚至是令人讨厌,而海明威之所以不惜笔墨描绘科恩这个人物,就是想用他的“传统”来反衬杰克这伙人的“现代”,当然,科恩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留恋的东西,正是杰克这些人抛弃的,或者说是刻意回避的。
另外,在海明威涉足文坛的时代,美国社会所流行的清教徒思想,包括后来的禁酒令,也是一个重要的背景,我个人觉得这其实也是现代性征象之一种,只不过它是从反面映衬出来的,在《太阳照常升起》里面,杰克,比尔,迈克这些人之所以宁愿漂泊海外,整日喝个烂醉,也与此有关,而海明威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描绘饮酒,美食,斗牛,旅行这些刺激的,享乐主义的活动,也不乏跟彼时国内那种氛围唱反调的意思。
书的后半段主要描写杰克一伙人在西班牙“圣福明节”的经历,两天前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是在回家的长途车上,当时车窗外是一片春光明媚,而书中所描述的是那种狂欢节到来的气氛,尤其是这种气氛是通过一些异乡人,一些旅客眼中所看到的,这真让我着迷,所以当时我想,这本书在旅途的间隙之中阅读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觉得海明威之所以那样迷恋斗牛,不仅仅因为斗牛活动里面体现一种猛烈的,阳刚的男性生命力之美,更重要的,是在斗牛活动中斗牛士和公牛之间的关系,一种在迷恋和伤害之间游移不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最高级的斗牛士都是很明了的,就像书中的罗梅罗,他爱公牛,但是他在场上却时时处在被公牛抵死或者主动***死公牛的荒谬危险的境地之中,而斗牛活动最吸引人的地方也在于此,一旦斗牛士注意到了个人安危,刻意回避和公牛的危险距离,斗牛也就没有什么看头了。
另外,斗牛士和公牛也存在一个逗引和被逗引的关系。这一切都很像我们人类赖以繁衍生息的一种最重要的关系,男人和女人,逗引和被逗引,伤害和被伤害。这其实也就对应了杰克、迈克、科恩和勃莱特之间的关系,还有勃莱特和罗梅罗之间的关系。
海明威说过他的写作不过反映出“冰山一角”,而我认为要理解这句话,应该从他的写作技术这个角度入手,因为文字是一个抽象的表达方式,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的写作会同时包含叙述、描绘、思辨、评论等等的因素,比如托尔斯泰、昆德拉这样的作家。
而海明威仅仅是做到叙述和描绘,他对于生活场景、环境、对话、氛围的呈现也都是节制的,他不评论,也不去分析人物的所谓“心理世界”,但他想要告诉我们的内容却已经隐含在海面下的巨大冰山之中了,这种手法很像电影,这可能也是海明威作品大多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原因,另外说句题外话,王朔有些小说就是这样的,比如我很喜欢的《玩的就是心跳》。
写太阳升起的作文450字【二】
1926年,还藉藉无名的海明威推出了首部长篇《太阳照常升起》,个人以为是他最好的长篇之一,虽然在当时算不上石破天惊。之前,他也有过一系列短篇投石问路,纵然水波不兴,也成为长篇准备中的练笔,使长篇处女作丝毫没有生涩的痕迹。当然这也有巴黎的良好催化作用在其中——饥饿与贫穷的磨练,良师斯坦因小姐的指点,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恩恩爱爱、相濡以沫……
可惜的是,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在其成名后就一一分解。窃以为,吃得太饱,钞票与老婆太多,往往与才华的枯竭程度成正比。这是后话。
起初并不明白科恩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所起的作用。他显然不是一个应该被忽略的人物,开首就是一篇科恩小传,将其人交代清楚:就读于老牌名校——普林斯顿大学,曾是大学拳击冠军——身强体壮,出身富有的犹太家庭——身家清白,为人厚道,对女人尤其心软——要么被女人抛弃,要么被女人捏在手心。看起来并无不妥,中产阶级的普通一员,却无值得大书特书之处。看到后来发现苗头不对,他与书中正派的主人公及其寓公朋友总是格格不入,就象牛栏里那头想与公牛处好却被孤立的犍牛。后来我恍然大悟,科恩是作为一个未曾受过创伤的参照物而存在。所谓受过创伤,就是吃过战争的苦头,象巴恩斯被战争阉了就是一个直接的象征。
科恩压根不明白这里面的游戏规则,他跟那帮人处不来,极少喝醉,又特别较真,将逢场作戏的阿施利夫人当作女神,随时准备为心上人作出奋力一击,而他确实这么做了,又傻乎乎地直言斗牛可能会令人感到乏味。总之,他所做的一切都不入那帮身怀战争创伤、经常烂醉如泥、到处寻欢作乐的寓公们(哪怕是***者)的法眼。而他只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大好青年,战争象一条河,泾渭分明地将他拦在另一边。
受伤的区别于未受伤的,最本质的一点是,什么都没所谓了,日常生活乏味难耐,沉醉于酒精、斗牛等一切刺激之物方是正途。就享乐主义的角度而言,本书可以成为上世纪二十年代巴黎咖啡吧指南和潘普洛纳斗牛的专业解说。有文化的中产阶级仿佛是特别脆弱易溃的群体,在战争创伤这个合理的理由下,他们以往遵循的一切土崩瓦解,又自行形成了一套易于接受且互相认同的准则。
就象家庭有重大变故,孩子就不能够做一个正常的好孩子。实际情况是,破碎家庭亦有健全的孩子,神经大条的未必是文盲,而解甲归田、如常生活者比比皆是。而巴恩斯最终发现,即便他没有受伤,如美少年斗牛士罗梅罗那样生猛,与阿施利夫人也撑不了多久,这才是致命打击。
因为垮掉的是主流,所以科恩便成了不合时宜的怪物。反之,如果科恩是主角,那斗牛是乏味的有望成为名言。其实如果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们也就是他,想必能够和谐相处。
写太阳升起的作文450字【三】
你于我,是整个少年时代的憧憬。你于我,是回忆中的缕缕阳光。
像是上天注定的缘分,你和我在上幼稚园的时候就相识了。我们从陌生到相知,从冷漠到嬉闹。
那时的你流着长长的鼻涕,满衣服几尽口水。每次谁一欺负你,你便往地上狠狠一坐,“哇”地哭起来。老师闻声赶来,教诲着欺负你的人儿,那小人儿当不愧是我了。
后来,我们都长大了,不流长长的鼻涕一下子坐在地上哭了。我们的友情倒是也增进了不少。
还记得我们小学时捏的陶胚吗?那时的你笨笨的,还是我帮你捏的。还记得那颗被你扔出砸在领居玻璃上的石子吗?说来真巧,你没有那种特技却能将玻璃砸出一个圆,不平不仄,比圆规画的都圆。
至今,那块陶胚和石子都被我珍藏着。突然有一天,陶胚碎了,石子丢了,你也要离开了。
那天,我赶到学校,天空很蓝,白云很白,鸟儿的声音清脆地歌唱着。这倒不像电影中离别时的场景,丝毫看不出半点忧伤之感。
你和同学一一说了再见,和我说了几句保重的话,便坐上汽车走了。我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但压抑的离别之愁还是不断的涌上心头。
离别后,晚上你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不要哭。请记住,我永远是你心中的太阳,不管我们相隔多远。要记住之前的美好时光,还有我这个你心中的太阳!”
我哭泣时,你这个太阳就在一旁安慰我,给予我温暖;我失望时,你这个太阳就在一旁鼓励我,给予我信心;我开心时,你这个太阳就在一旁陪我一起笑,给予我友情的最大爱!
几年后,你突然出现在我家后院。当我看见你时,我激动地冲上去抱住了你,和你互相讲着这几年的事情。
那天的傍晚,我对着最后一抹金色耀眼的夕阳喊道:“我的太阳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