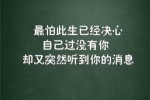红色基因的作文怎么写800字【一】
所谓行者重在一个“行”字,心向往之,身体力行,从一而终。所谓基因,就是中华儿女五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精魂。
二十年前,一位年轻人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出发,背起行囊只身前往北京,这位年轻人叫雷军。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了对理想的忠诚实践,来到了这里,证明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都应在内心为自己鼓掌,对自己的勇毅投以敬畏并祝福。
我不由得想起了这座城市的口号,“勇立潮头,敢为人先”我想起了这个国家的忧患意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便是行者的`基因。
回望千年,历史早已给行者清晰的注解,一生只写一本书的司马迁;一生只走一条路的玄奘法师;一生尝草采草的草民李时珍;汨罗江畔屈原不屈的灵魂;长江岸边诗仙傲岸的风帆。行者的英姿风流千古。
与此相反,那些彷徨者,该是多么让人叹惋。渭水直钩姜子牙,碧水浩渺,终究等到发尽白啊。寒江独钓蓑笠翁,人鸟绝灭,可曾获得一尾青睐呢?“陋室空堂,曾经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何尝不是曹雪芹的哀怨?“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除了英雄惜英雄的时空勾连,又何尝不是项王个人悲剧的写实,“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无奈啊,乌江也听罢了项王的悲歌“时不利兮骓不逝”呀!
有实用主义者的不屑,“千年的英雄与我何干”,有成功学信徒的窃喜“我知道成功的又一法门”,而就在我们身旁,就有这些被我们称为“学霸”、“学神”的人,放下“985”、“211”的名校光环,挣脱世俗利益考量的羁绊,从容面对从头再来的痛苦,呼应着内心最恳切的呼唤。“何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惶惶欲何之?”我想起了厦门大学贴吧的一首长诗“真正的梦想,死亡又怎可将它阻挡?”“究竟是人言可畏还是你的梦想柔弱的不值一提?”
我们都有行者的基因,让行者的基因去表达,让行者的印记撑起我们的精气神,让我们在千年的史册上划定行者的坐标,让我们从今天出发,向着无愧于心的方向!
古来贤者皆寂寞,唯有“行者”留其名。
红色基因的作文怎么写800字【二】
是父亲,鼓励我茁壮成长;是父亲,帮助我度过难关;是父亲,引领我不断进步;是父亲,让我爱的温暖。在我心中,父爱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从点点滴滴的小事中自然显露出来的。
那是一个寒冬腊月的傍晚。父亲跟往常一样骑车接我回家。大风狂哮着迎面吹来,路边的行人都缩紧了脖子,空旷的马路上只有父亲弯着腰,带着我,艰难地踩着自行车。尽管爸爸像一堵墙似地挡在前面,我在后座上还是被寒风吹得瑟瑟发抖。
不一会儿,雪从阴云密布的天幕中疾驰而下。“太冷了,咱先找个地方暖和一下吧!”我用发颤的声音说。父亲急忙停下车,摸了摸我的手,又看了看天。“这雪一时半会儿恐怕停不下来,咱们再坚持一下好不好?很快就到家了。”说着,父亲脱下外套披在我的身上,又骑上了车。在父亲温暖的大外套下,我终于觉得身上有了暖和气儿。但我忽然想到,爸爸帮我挡风,还穿这么少……。于是我在风中大声问:“爸,您也冷吧,外套还是给您吧?”“儿子,老爸骑车热着呢!”父亲在风中大声地回答我。
雪越下越大,风越来越猛。车轮开始打滑,我们在风雪中显得寸步难行。我站起来,搂住父亲的脖子,手碰上了他的耳朵,啊,可真凉呀!可是,当我顺着父亲的脖子往下摸,竟然湿漉漉的。原来,父亲已累得满身大汗。路灯下,父亲额头上那晶莹的露珠,不知是雪水还是汗水。
时间好像凝固了,感觉过了几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家门口。
打开门,回到温暖明亮的家。这时,我突然被父亲的脸吓了一跳。那是一张跟平常很不一样的面孔:嘴唇乌青,耳朵通红,鼻尖发亮,脸上多了好些皱纹。我第一次发现,父亲已苍老了许多;我第一次注意到,父亲的头顶已被一圈白发包围了起来;我也第一次体会到,父亲为了儿子根本顾不上自己。我的心在微微颤动,鼻子一阵发酸,眼泪只想往眼睛里涌。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也是父亲教我的。我默默走过去,紧紧地扑在父亲的怀里,父亲则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背。
父爱就是这么微小而无言,却温暖而伟大的。从此以后,只要回想起那个风雪交加的傍晚,我的心中总是涌起一股春天的暖流。
红色基因的作文怎么写800字【三】
我们从来不知道最早的英国人到底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在潮湿的岛屿上,创造出了王室和政府理论、财产与契约的理论、法律和税赋的理论,这些理论改变并最终提升了我们,不列颠岛曾是罗马的行省,伴随着罗马的衰老,公元410年罗马军团被召回帝国首都后,不列颠行省三面受敌(西是爱尔兰部族、东面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北面是皮克特人),只能自求多福。
在整个5世纪,来自现在德国、丹麦和低地国家的人作为英国人的先辈开始大量定居下来。到6世纪末,一共有12个王国,后来兼并为7个。
到8世纪末维京人入侵,7国合并为4国:诺森比亚、麦西亚、东安格利亚和韦塞克斯北方维京人一点一点征服了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吞并了东安格利亚,在诺森比亚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蚕食了一半麦西亚。当他们最终觊觎韦塞克斯时,被阿尔弗雷德国王击败。
在定义一个民族的地位时,除了语言,民族意识是一个很重要标准,事实上,一个民族总是需要借助一个“外国身份”的对照来形成,比如,对意大利人来说,奥地利人就是外国身份9世纪的英吉利人,他们面临的外国人就是维京人到10世纪时,英国完成了英格兰的民族统一,形成了完整独立的民族国家,将其他欧洲国家远远甩在了身后,当然,英格兰的民族融合体现为一个过程,边界也具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读后感·盎格鲁—撒克逊人逐渐向西扩张,被征服的不列吞人被称为“陌生人”或者“外族人”,后来被称为“威尔士人”,威尔士人的原意就是“陌生人”或“外国人”。
历史学家苏珊·雷诺兹说:“英格兰王国的居民习惯称自己为英国人,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不是一个用连字符连接起来的王国,而是国民认为它们归属同一个民族国家”
10世纪是这个早期英吉利国家的黄金时期:统一,富裕,依照法律施治,后来发展出了议会民主、司法独立和个人自由等,逐渐形成了区别与邻国的种种特质。
红色基因的作文怎么写800字【四】
忏悔者爱德华,阿尔弗雷德家族最后一位君王,死于1066年1月,没有留下一男半子。据说,爱德华曾制定其第二个侄子诺曼底公爵威廉为继承人,但也有人说,爱德华在病榻上推翻了这一遗嘱,改由自己的妹夫哈罗德·戈德温伯爵继承王位。历史上认为,威廉收到教皇的支持,而哈罗德被英格兰贤人会议推举。
哈罗德加冕后,威廉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威廉的嫡系部队是诺曼人。诺曼民族尚武好战。10世纪时诺曼人征服了法国北部的维京人。哈罗德准备迎战威廉的入侵时,看到了凶险的征兆:1066年哈雷彗星穿越英格兰。最终,戈德温三兄弟战死疆场,1066年圣诞节,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威廉顺理成章加冕为威廉一世,正式成为英格兰国王。
对英国人来说,诺曼征服是一场灾难。本地贵族被夺爵驱遣或没收财产,本地贵族或逃亡、或流散欧洲。威廉开始了一个绝对君主的统治。他将英格兰作为自己的囊中之物,随心所欲的处置。
盎格鲁编年史记载:他要求彻底进行财产清查,不能隐瞒一寸土地、一头公牛、一头奶牛、或者一头猪。调查成果就是我们熟知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Book),也称《最终税册》,为了收取租税,调查细致严苛,被调查者如履薄冰,好像在接受末日审判,故调查结果被称为《末日审判书》。威廉几乎将整个国家分赐给他的`雇佣军和忠实的臣下。至少92%的土地封给了生于海峡另一边的人,200多名大地主中只有两个是本地人:阿尔丁的索克尔和林肯的考斯文。当新贵族安顿下来开始享受他们的特权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逐渐被淡忘。诺曼征服,也将英格兰置于讲法语的贵族统治下。
盎格鲁—撒克逊人,尤其是伦敦商人,有意识的藏起了他们的英吉利身份,口音带上了法国腔,以便跻身上层社会。想攀高枝的不限城里人,历史学家发现,1114年的某个农庄,登记薄上尽是索朗、雷诺等很法国的名字。读后感·哪些古英国名字,只有5个幸存下来了:阿尔弗雷德,埃德加,埃德温,阿德蒙德,以及至今仍然很流行的爱德华。英国人战败不仅导致诺曼名字流行,就连肉类的词汇也可见一斑。说英语的农夫招呼家畜用的是最质朴的语言:cow,pig,sheep。现在诺曼领主的餐盘纷纷换成了法语词语的新名字:beef,pork,mutton。
政治词汇也未能幸免,“贤人会议”、“习惯权利”等词语渐渐绝迹,新涌现出来的是“效忠”、“封臣”、“佃农”、“农奴”等。朝向个人自由、契约自由以及平等使用普通法的进程被阻断了。“英国人高声哀叹他们失去的自由,不断谋划怎么撼动整个如此严苛、忍无可忍的枷锁”。砸锁诺曼枷锁的想法,激励着后代英国人与斯图亚特王朝展开斗争,后来又在北美的革命中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