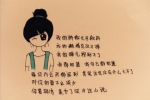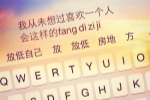写景物悄然绽放的作文【一】
在花的足音中响起一声轻笑,美穿越流光,悄然绽放。——题记
在燕子的微语中——
在家门前的小小的花园里,阳光重重地坠到花瓣之上,她弯着腰,捡拾起那些或粉或紫的小花伞。一瞬间,指尖碰到枝叶上细细的绒毛,阳光被与母亲一样温柔的目光所融化,犹腻在露珠上。我站在一旁看着,脚步似乎被牵引着,下一秒就会同她一起拿着小铁锹,在薄薄的绿雾中俯下身子,为每一个种芽松土,“劈里啪啦”,将枝叶上的虫声敲碎,揉进更为柔与的花的梦想中去。
“嗞嗞”,心壤上一阵酸痒,有一些我无法触摸的东西已开始生长,在尚贫瘠的地表之下,我能感受到传来的巨大的心跳声,“怦怦”,强劲而有力。
在柳烟的堆砌中——
在清濛的早晨里,空气中隐隐浮动着清甜的香气。她依然在那里,在小小的花园。她的双颊被周围锦织的嫣红映得光润,青蓝色的棉布衣衫也浸润着如水一般的温柔。在浓烈张扬的色彩里,她纯净而又质朴。我站在一旁看着,我的笑也似乎被牵引着,下一秒就会飞到嘴角。
“噌噌”,心壤上涌出一片翠绿,枝叶摩挲成阳光的声音。叶儿轻轻颤抖,让我看到天空的隐秘心跳。
在裙摆的盛开中——
在午后微醺的阳光里,她站在一朵一朵的花中。我站在一旁看着,而她唤住了我。我穿过丛丛的花叶,来到她身边。脚下因踩着沃实的泥土,心也一下子松软。
“这个给你。”掌心在她指腹滑过后,被柔软的触觉所包裹——是几朵栀子花。层层厚重如丝绒一般的花瓣,揉成小小一朵,到接近花瓣边缘,似是因剧烈燃烧而微微卷曲成柔与的波浪。我凑到花前,嗅了嗅,清丽而又甜美。
我感觉心中的那些东西忽然膨大了起来,胸膛里被装得满满当当,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饱满起来。
风将花香吹乱,我不由抬起头去追寻风的足迹。刚一抬头,便对上她的目光。她不说什么,只是站在那里,温温柔柔地笑着,一如温润平凉的玉石,怀抱着与柔的光。
“啪!”一瞬间似乎听到花开的声音,我低头寻找,才发现胸膛中已开满了花,开满了美。它们是在絮絮的时光中的哪一处落脚?或许在裙摆盛开前,或许在柳烟堆砌前,或许在燕子微语前,美,悄然绽放。
写景物悄然绽放的作文【二】
街边有两棵腊梅,一棵在东首,一棵在西首。
我不知道它们的年纪,很多人都不知道。家里的老人告诉我,他们搬来这里前,就有这两棵腊梅了,年年开花。
我喜欢这两棵腊梅。每年冬天,当雪花飞扬,腊梅的花就开了。它的花蕾象一粒纽扣那么大,黄里透着白,白里透着红,阵阵清香在街边四逸开来,这香透着甜,沁人心扉。喜欢它的花,喜欢它的香气,更喜欢它雪中傲然的风骨。无论多冷,路过树边,我都不禁停下脚步,细细欣赏。
人们都喜欢这两棵腊梅。可是呀,有的人却看不惯了,他们叼着香烟,穿着西装,拿着公文包,小心翼翼地从车上下来,生怕弄脏了他们的皮鞋,看也不看地说:“路太窄,要拓宽。”回头就坐进了车里。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工程队来了,他们开始搅拌水泥,向被砸开的路边浇去,流动的水泥象是洪水猛兽,咆哮着大叫着向西首的腊梅奔去。
树是不能动的,离了土,树就会死。于是凝固的水泥象是乌龟的硬壳,生生的盖在腊梅突出的根须上。虬须满布的树呀,找不到水,找不到土,只有冰冷的水泥,干燥的空气。
西首的树死了。
于是呀,工程队的人把它砍断了,拦腰砍断的树只剩树桩,突出的根隐约可见,诉说过去的故事,刺痛人们的心灵。
人们看不下去了,纷纷出面去阻止工程队,西首的树无法复生,东首的树不能重蹈覆辙。水泥搅拌机停了下来,铁镐铁锤被放在了路边,人们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可是呀,第二天清晨,当人们揉着朦胧的睡眼向窗外望去时,水泥的界限早已一寸一寸前进,硬生生地包裹住了东首的树根。人们咬牙切齿,只恨自己的粗心大意,又失去了一棵腊梅。
冬天到了,东首的树没有开花;春天过了,东首的树没有发芽。
于是,人们便坚定地相信,东首的树也死了。
冬天的路上还是很冷,却始终没有下雪。地上的水被凝成了冰,冻成了石块。默默地走在人来人往的宽阔的道路上,我感到了无尽的孤独与怅然若失。
忽地,我闻到了一阵芳香,甜甜的,有种沁人的香气。抬头寻找,东首的腊梅桩上,还是那么沧桑,但它的枝干上,却开出了星星点点的腊梅!
这花比以往要小,比以往要淡,但香气还是那么的沁人心扉,让人沉醉。花蕾上仍有些许的水珠,象是朦胧的睡眼。东首的树就象沉睡了一年的睡美人,此刻慢慢醒来,给人们了惊喜。
人们说是上天让它活了过来,我却不这么认为。是它的风骨与不屈的意志救活了它,让它在苦涩的水泥中复活过来,重新放出光彩。
美,悄然绽放……
写景物悄然绽放的作文【三】
在一串串火红的冰糖葫芦中,我看到了童年时期孩子绽放的笑靥。
天空灰暗,路上的行人耸起肩,急匆匆地向前走去,仿佛成了黑色的剪影。寒凉的风袭来,店铺昏黄的灯光黯淡了不少,心情有些沉闷。
路边,有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小摊子。那冰糖葫芦,一个个红得耀眼,像是过年时高挂的红灯笼。这一抹鲜艳的亮色总算为大街上添了点暖意,可仅仅是一抹而已,几乎没人注意到它的存在,没人停步买上一串。摊主也在翻阅一本书,想必她也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生意吧。
隔着一层玻璃,冰糖葫芦多少显得有些沉闷。可这妨碍不了它的美。夺目的红色静静地闪着,傲然冲击着暮色的空气,尽力去释放璀璨,山楂上透明的薄薄冰糖,流转着耀眼的金色光辉,驱开一片寒冷。它自在地绽放出红色的光芒,不管有没有欣赏它的目光,它都在努力地与严寒对抗,仿佛一朵怒放的红梅,兀自美丽,傲待风雪。
不知是谁说过,冰糖葫芦是童年专属的记忆。小时候的我们,也许是被它的美打动,才想拥有的吧。不远处传来一阵嘻笑声,是一群放学的孩童,蹦跳着走了过来。
“呀,冰糖葫芦!”不知是谁叫了一声,紧接着所有的孩童都围了过去,争先恐后地叫着:“我要一根!我要一根!”每个人都期待着去握住那根竹签,仿佛握住了它就握住了幸福。他们手中攥着葫芦串,冻得红扑扑的小脸与红玛瑙似的山楂相映成趣,洋溢着天真烂漫,驱走了死沉沉的阴暗。我心中忽然一动,说:“糖葫芦串儿开花了。”
一样的鲜红,一样的灿烂,一样的不畏严寒,冰糖葫芦的记忆不就是属于小孩子的么?小孩子的天真烂漫让世界一下子焕发出生机和温暖,就像是火红的糖葫芦能驱散阴翳和寒意。
孩子们绽放出的笑容美到了极致,冰糖葫芦的美也一并绽放开来,悄悄地,不带任何声响,却让温暖和美好弥散开来。
在冰糖葫芦绽放之际,我看到了只属于孩子的美,也悄然绽开。
写景物悄然绽放的作文【四】
路边的荒草中,一簇梅花正在悄然绽放。
时间已是寒冬,鹅毛般洁白的雪,正从天上缓缓落下,飘转,沉落,融化,之后便没了身影。
在这一片洁白中,空空荡荡,单调的只剩了白,仿佛要将天地合为一体。我不经意的摇了摇沉重的头颅,揉了揉酸痛的双眼,无意间瞥见遍地洁白之中,独立着一簇梅花,这梅花仿佛是黑暗中突现的一缕曙光,拯救了这死寂一般的世界。
万物皆静,可唯有这梅花如有人召唤般,促使我凑近观看。
走进之后,才发现露出鲜艳颜色的花瓣仅有一半,而花茎以及剩下的一半早已被雪埋没。白雪,险些将冬日里唯一的一处美,“***死”在襁褓中。
我愣了一会,赶忙卸下手套,用带着热的手,慢慢的拂去落在花上的雪块,却发现花瓣上留着脚印,或许是哪个不看路的家伙也曾伤害过这处美。
雪从花瓣上滑落,坠入大片雪白中,梅花却显得更晶莹了,发出鲜艳的光芒。
我漫无目的的环顾四周:高大的树木已失去往常的活力,光秃秃的树枝上,也没了鸟的栖息,平日里嫩绿的小草,如今也变得荒草丛生,潺潺流动的小溪,也静止不动了。
这一切,都因为惧怕严寒,逃走了,死去了。
梅花不怕冷吗?绝不是的,或许对它而言,美不是与百花争夺春天后得到世人艳羡的目光,而是在严寒中悄然绽放自己的精彩!
冬天里,一簇梅花正在悄然绽放……
写景物悄然绽放的作文【五】
从未想过那样的笑会在一位年近迟暮的老人脸上出现,那样温存的、柔软的笑,有爱意如水般从皮肤的褶皱间淌过。美,就象门前摆着的菊花,悄然绽放。
从不知老人多大年纪,也不曾去关心,老人却一如既往地待所有人都热情。“上班呀,路上要小心。”“开车要慢点儿,健康最重要。”“别忘了带伞,下午要下雨的。”她这样亲切热乎地招呼着每个人,被招呼的人或是轻轻点头后离开,或是停下脚步,也熟稔地拉过老人,唠上几句:“是呀,你也是。”老人就会显得极为愉快,为了这被人接受的好意,她的嘴角会轻扬,漾出一个恰到好处的笑容。
“小姑娘,这么早,上学去哈?”我点点头。“好呀,念书好呀,要记得多学点儿知识喔。”清晨的空气潮湿却又刺骨,老人就在门前微微颤抖,门前两盆金黄的菊花含着苞儿摇晃着,与老人一起目送着我离开。
听说老人是个苦命的人,儿女不孝,把她当作累赘,都对她避之不及。我曾见过老人的儿子来看望她。那一天老人的屋前屋后似乎都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她的笑意掩饰不住地充盈在脸上,就连屋前那两盆久未开放的菊,也似乎涂抹上了这喜庆的色彩,氤氲开一抹湿润的明黄。老人的儿子就在她浓浓的期待中来了,却是冷着脸,将带来的一些生活必需品放在桌上就要走,无视为他精心打扫的房子与准备的吃食。她带着些乞求的目光想要留住儿子,却是留也留不住,满屋子的希望与喜悦,都随着她儿子的离去黯然失色了。
我以为老人会消沉下去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却惊讶地发现,老人门前那两盆久久没有动静的菊,有一盆已经独自绽放——细嫩鹅黄的蕊,明黄的花心,象一团燃烧的火焰,“火光”中映出老人依旧含笑的眼。忍不住走进老人的屋子,与她攀谈起来。说话间,还是忍不住问了老人儿子的事,老人先是一愣,空气也象凝固般静止了,当我正在为自己的冒失后悔时,老人却低声开了口:“是我做得还不够好,身为一个母亲,我应该做得更多,或许这样,他就会意识到我对他的好。”说到这里,老人笑了,满脸的皱纹里,流淌着绵远的爱。我静默着,却在心底为这样甘于付出而感动。老人的笑,就象门前的菊,绽放在这个稍显寒冷的季节,却温暖了我所有的记忆。
美,悄然绽放,即使是年老体衰,美貌也早已逝去的老人,也会绽放美丽,让人感受到如沐初阳的温暖。
写景物悄然绽放的作文【六】
春的美是蓬勃而芬芳的,它不像夏那么袒露、秋那么成熟、冬那么内向。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当早春的第一缕阳光跳出地平线,照耀在大地的时候,封冻在山川上、覆盖在枝头上的冰雪开始融化,凝结在枝头的坚冰也开始慢慢化成水顺着枝条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和风吹拂,细雨滋润,原本光秃秃的枝开始冒尖,爱美的大地也悄悄换上了新装。你看原野上,道路旁,房前屋后那一棵棵一排排的树,都又悄悄地吐出了新芽,翠翠的、绿绿的、浅绿、浅黄,微微带着粉红色……
墨绿的野草疯长,艳丽的向日葵在空中摇曳。享受着春风拂面的细腻,嗅息着清香怡人的芬芳,轻抚着那一缕缕纤细嫩绿的柳条。我们向春天祝福,祝福她绽放新的生命;祝福她又一次为大自然增添累累硕果,描绘灿烂的风景;祝福她的生命从此多姿多彩。春是浓密的山林,杂花生树,飞鸟穿林;春是无暇的碧玉,月下皎洁地泛着淡淡银光;我们将春天造就的每一番景象铭记心头,去品味,去摸索,去聆听,去感受那“心弦之动,开合释然”的韵律。
雨,是春与大地交流的方式,也是春姑娘对大地的祈祷,她穿着绝美的轻纱漫步在大街小巷、浓密的山林,向人们展示着她那绚丽的舞姿,给灰白的心灵注入生机与希望。你只需静下心来,泡一杯清茶,开始作画:大地是一张上好的宣纸,春雨是一只饱蘸绿意的笔,你只需轻轻地点上去,那绿便晕开去,晕开去……
连绵的春雨过后,天气便突然明朗起来,阳光暖暖的,一点儿也不烈、不灼。春的阳光温暖而充满活力,唤醒一切沉睡的雕塑。你只需轻踏青苔,嗅息花的芬芳,去领会那迷离的美。阳光像绚丽的彩练,把美好的青春装点得辉煌绚丽。当你独自忍受失败的悲哀时,阳光像你台马力十足的吹风机,烘干你的腮边珍珠般的泪珠。泪光中,看到春姑娘正挥着洒脱地舞步走来,冬爷爷残损的脚步渐行渐远……
春之花——悄然绽放。
写景物悄然绽放的作文【七】
依旧是冬日的早晨,我照常起床洗漱。打开大门,一阵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我不禁打了个哆嗦,背上沉甸甸的书包,要迟到了,我加紧向学校走去。
天刚蒙蒙亮,依稀还能瞥见几颗闪耀着的\'星星,调皮地冲我眨眼。可我却无暇欣赏,急匆匆地向教学楼跑去。“无聊”的早读又开始了,窗外一阵异样的声音传入我耳鼓,我好奇地瞥了瞥窗外,四个垃圾箱赫然在目,什么垃圾都有,纸屑、果皮、零食……甚至连四个垃圾箱也装不下这垃圾——周围还有着星星点点的垃圾袋,我还看见了一个模糊的略显肥胖的身影在收拾垃圾,看不清是谁。我克制住了自己,不看向窗外,继续早读。
下了早读课,太阳发出温暖的光芒,我随着这阳光再次看几窗外,那身影消失了,垃圾箱里的垃圾、周围的垃圾袋都没了。清风徐来,小草和那常绿的树叶尽情地享受着阳光雨露的滋润,更绿、更鲜、更美,一切让上了一节早读课的我顿时豁然开朗起来。
我跑出教室,想打听这神秘身影的人,后来得知,那是食堂的缪健师傅,不仅负责食堂打扫,还负责倒掉整个学校的卫生打扫,对于接近六十岁的他来说,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啊!
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看见他,他依然拖着垃圾箱走出校门,背影却是单薄了许多,似乎没有了之前的强壮和有力,只有那驼着的背和沉重的脚步,他摩擦地面的咔咔声一声声沉闷地敲击在我的心头。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越来越小,消失在校门外……
后来几天,我没有再看见缪建师傅,垃圾箱里也满满当当了,不自觉,我信着步子走到那个缪建师傅打扫的地方,又有一个身影在忙碌,可再也不是缪建师傅了,听说他在别人的劝说下去南京治病了,接替他工作的是李师傅。
一阵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但在这一刻,我心里却倍感温暖。美,就这样在我们校园悄然绽放着,传递着。
本文地址:美悄然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