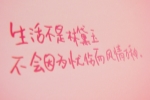坐邮轮旅游的感受作文【一】
到了那天, 我准备好一切的东西来到机场 ,机场的人真多啊!妈妈跟我办好手续,我就由一个阿姨把我带到了无人陪伴的儿童那个地方去了。像我这种情况的还有一个比我大的姐姐。不过她是自己坐飞机去西安的,是3:30的飞机,我是乘飞机到湖北武汉的,是3:00的飞机。到了2:45分,我由一个年轻的阿姨把我带到了候机厅,在候机厅,我找了一个坐位坐下,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阿姨把我带上了一辆大汽车,那辆大汽车把我们带到飞机前,我就按顺序排队,依次上飞机。来到飞机上,我就对照机票上的位置坐下,我是坐在第一排的,到了3:30的时候广播里就说:“飞机快要起飞了,请大家系好安全带。”过了一会儿,飞机就起飞了。飞机越飞越高,刚开始我看见了整个广州市。慢慢地飞高了,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只看见一片白云,升到最高的.时候,展现在我眼前的就是一片白芒芒的一片。我想:“如果,世界就是这样白芒芒的片,一点儿色彩也没有,那世界就会变得像以前那样,没有人类,没有现在那么繁华。”不知不觉,广播里又说:“飞机,已经到达目的地武汉。武汉现在的温度是零下4摄氏度。”听了广播后,我连忙从包里拿出一件棉袄穿上,把围巾系好。穿好衣服后我排好队下了飞机。
通过这次坐飞机,我受到了启发就是:我能独自出远门了。
坐邮轮旅游的感受作文【二】
??火车,还真爽!700字今天阳光灿烂,彩云朵朵,鲜花怒放,小鸟兴奋的叫着,好像在祝我玩的愉快,一种欢快感不禁油然而生。在候车室等车时,我坐立不安,一直朝着窗外看,恨不得让火车马上进站,让我看看它的雄姿,让我体验坐火车的感觉。
盼望着盼望着,检票的时间终于到了,我迅速的冲向了属于我的那节车厢。车厢门前有一个着装整齐、漂亮的女检票员在检查火车票。可能是因为暑期出来旅游的人比较多,车门前堵着一大堆人,我排了好久的队,才上了火车。上了车,我迫不及待的让爸爸带我浏览了一遍各个车厢,大家都其乐无穷的,玩游戏机,打牌的……
我和堂弟乐开了花,尽情地享受乘坐火车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把带来的零食搬放在火车上,像过节一样,围在一起。火车上新鲜事可真多呢:有卖零食的,有卖玩具的,也有推销袜子的,还有中午卖盒饭的……
我玩累了,喝足了,吃饱了,就坐下来细细观赏窗外的.风景。突然间我惊住了,一眼望过去全都是绿野,我的心灵在那一瞬间得到震撼和净化。我好象无意中扑进了一副巨大柔美的画卷中了吧!我的眼前是一排排整齐而挺拔的树木,它们英姿勃发的站立在铁路旁,仿佛是铁路忠诚的卫士,火车驶过树枝摇摇摆摆的,好好像在向人们打招呼呢!车转了一个弯,树全都不见了,只有一座座山,连绵起伏。抬头望去,漫山遍野还是绿色的,充满着灵动的生机,美极了。看着窗外的景象,我任大脑在美中陶醉,任心潮在美中起伏,我不禁感叹,我曾经领略过九鲤湖的清丽,大蜚山的雄伟菜溪岩的壮观,可是此时,我却被窗外自然的美所推翻了。我爱这大自然的景色。
坐火车真好,能让我体验新鲜的感觉,还让我饱览大自然的风光,我喜欢坐火车!
坐邮轮旅游的感受作文【三】
岷县通闾井镇的那条公路,是建国初、一九五五年修通的。通车剪彩时,我们戴着红领巾,唱着歌,敲着锣,打着鼓,在街头儿下迎接,当看见几辆解放牌汽车远远隆隆开来时,我们那时的心情,如同现在人看到了飞碟般地兴奋。半个世纪过去了,通车剪彩场面就像是昨天般地明晰。但是,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闾井人,从改革开放前的那几十年一直坐的是拉货的那种“敞篷班车”,受了几十年的“洋罪”,不知别人的的记忆如何,我的记忆是八辈子也忘不了!只要我一坐上班车,我就想起来我所坐过的那种班车,先写两篇你读读:
有一次,腊月里我回岷县闾井探亲,在岷县城卖上车票却一连等了三天。第四天终于坐上了岷县发往马坞乡的敞篷班车。还算运气不错,我抢到了前边靠右角位置。
没坐过的网友或许不知道,那时各地所放的名曰敞篷班车,其实是普通拉货的老牌解放车,不过在墨绿的车箱中间拉着根铁链子罢了;坐车的旅客,无论大小老幼,不是坐着,而是人挨人站在车箱里的。因此,班车稍微一晃动,各个角落就会出现不同程度地挤圧。尤其是车在转弯、减速时,相互挤压就更厉害了。因之,车箱前边两角相对稍微轻松些。在我认为也相对安全些。
坐上这种班车,只要车一走动,车箱就象蜂窝,笑闹声,叫唤声,说话声不绝于耳,这种混合交响声和着往来的挤压力,时起时伏,忽高忽低,实属正常,天王老子也没法,禁止不了。车快到石家台儿了,突然传来几声撕心裂肺的小孩的哭叫声,和几个女人同时叫喊声。听到叫声,全车旅客好象没反应,只是,驾驶室后站着的两个探亲的现役军人,用拳头使劲砸了几下驾驶室顶,大喊:
“开慢些,师傅——挤死人了!”
车猛地刹住,开车的司机打开车箱门,伸出头,气凶凶地问:“嫌挤是吧?嫌挤我开回去给你们换辆轿车来!”随即,使劲“啪!”地关上车门,极利索地调过车头,油门踩到底,往县城方向就开。
我有点急了,弯腰朝驾驶室大喊:“张师,你将就好些者!”我见车减速,接着说:“张师傅……你有折回到县上的(路程)不就早到申都了嘛……带孩子的到申都就下去了!”
过后我细细地想,他未必真敢折回到县上去,只是我到现在不明白,一车老小,那样折腾一下,又何必呢?人啊,才是永远读不懂的.一本书!
他又慢慢地、不情愿地刹住车,从驾驶室钻出来,站到地上,转过身,以商量的口吻说:“怎么办?你们大家说……”
是我引火烧身,我当然不能缩头,我尽量放低声说:“张师傅,要不这样,带孩子的几个都是在申都下的,也不远了,把车票线退给她们,叫她们慢慢地走回去,好吗?”
他想了半天,说:“也行,那就这样吧。”
可是那几个女人说啥也不下去。僵持了半天,司机又说:“那就将就点,不要死声哇气地叫唤,我们还是走吧——谁让你们是东山区人呢……”
司机倒过车头,重新将油门踩到底,车哼哧哼哧地只是喘气,老牌解放的车还是跑不起来,但车箱的摇晃程度并没有减弱。只是在我和那两个军人的带头下,七八个青年挽着胳膊,将带小孩子的几个女人围在了中间,以减少对他们的挤圧。
“大大吆——差(cá)点儿闯下祸了……”
“哎,挤死还不让人叫唤!”
“……”
“悄悄儿地,师傅不是可有生气了。”
一小时多,终于到了申都。到了申都就好些了,下去了几个旅客、尤其是带小孩的旅客下去了,车上的旅客松了口气。
“谢天谢地,我终于到家了……”每次到了闾井街上下车时,我都是这样想。
说实在的那时坐一天敞车,比干一天活还要累,那时人虽然年轻,每次到家,我想的不是先吃饭,而是美美地睡上一大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