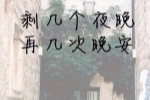车站的故事作文800字【一】
当你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再三说着珍重、珍重;当你深深地看着我的眼,再三说着别送、别送;当你踏上离别的列车,我终于不停地呼唤:诺儿、诺儿,你可要回来啊!我会在这儿等你的……
看着列车顺着铁轨将你送往站牌所指的方向,我的心也随着“咣当、咣当”的车轮声在颤动,在流泪……我时常会去那送走你的地方找你,因为你曾经站在这里,因为你是从这里出发的,因为你……还因为你说过你会回来的,还因为你还说过我们之间的情谊是永远的,还因为你说过……
我知道在这离别的车站,许多人再难重逢,剩下的只是那美好的回忆,剩下的只是那对车站的企盼。虽然我们距离得很远很远,虽然至今列车还未把你带回来;但是我想,你一定会回来的,你总会乘坐列车回来的,因为你不会忘记我那含泪的眼睛,你不会忘记你的诺言,你不会……
当我站在车站等你时,当我极目远眺时,当我望着一列列列车呼啸而至时,当我一次次黯然神伤地离开车站时,当我看到许多和我一样的人失望地离开车站时;我觉得那车站上的站牌也低垂着头,也在为我们的离愁而伤感,它好像也无法承受每天离别的人群带给它的伤痛;那车轮撞击着铁轨发出的“咣当、咣当”声,也在为我们的失望而内疚,它也好像也不情愿太快地离开车站,也在说:我会慢点、我会慢点……
我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这车站台,望着开来的开走的那和你乘坐的一样的列车;我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这既陌生而又熟悉的车站,来到这曾经有过你的身影现在却没有你的身影的地方;我一次又一次站在车站上,抹着永远也抹不完的泪水。诺儿,回来吧……
车站的故事作文800字【二】
我吃完晚饭后距离火车出发还有一个小时零十分钟,等公交车又花费了几分钟,最终由于做出租车速度比较快,所以在距离火车出发还有五十五分钟的时候来到了火车站!
看来我们两个人还是来早了,由于现在不是高峰期,所以火车站也没有很多的人,所以我和刘明就随便挑选了一个位置坐下来等待着!
就这样等待着实在是有一些无聊透顶,可是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消磨时间,火车站里总是有提示信息以及广播,这样不时之间听见还是很有感觉的!
我就在候车室一直玩手机,不过也没有感觉时间很缓慢,四十分钟一下子就过去了,当广播提示之时,我们两个人立即行动,也没有耗费什么时间,当六点五十分钟的时候就上火车了!
车站的故事作文800字【三】
在一个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的早晨,还有一点点湿润的气息。
在一个车站有一群等车的'人,有大家小姐,有工地的农民,有白领,有带有传染病的医生,有中年妇女,也有抱着几个月的婴儿的妇女,很是热闹。
当然在车站也有规定,妇女儿童,老人,职业工人,都有属于他们的车站。
在车站的一旁,立着一块高高的牌子,牌子后面是一个“绿色通道”牌子上面写着:母子上车处。但是,牌子后站的应该是妇女儿童却站的是四个假文盲。第一个穿着一件大衣,手插在两边的兜里,嘴里还哼着一首小曲,看起来很悠闲的样子,但是他不知道,他已经列入了“文盲区”尽管他可能不是文盲。第二个头戴毡帽,闭目养神,身上穿着毛领大衣,手插在裤兜里,脚慢慢抖动着,可能湿润的空气冻着他了吧!他后面的那个人,一脸埋怨,撇着嘴,像和人吵架了似的。一副自以为是,闷闷不乐的样子。下面穿了一件棉袄,一件棉裤,手和前两位一样。第四个人,脸上带着口罩,身上穿的像一个北极熊一样,好像生病了,病恹恹的。牌子后站着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她好像没地方站。
这四个人又不是文盲,那为什么还要站在“母子上车处”就因为两个字“便宜”第一个人可能是这样想的:我没看见,就站一会没什么,反正也没人管。就因为没人管,才要看自己的自觉性。第二个人会想我闭着眼,我看不见。但是同时,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比上了眼,就等于关上了心灵之窗,关上了良知。第三个人会想:站哪都一样,反正都要上车。你站在了一个不属于你的位置,你会让一个属于他的人没地方站。第四个人会想:我生病了,别找我的事。不要想着自己有特权,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
你们如果都这样想,那就完了,世界将笼罩在自私中。
打消这个念头吧!
同学们!不要为了自己的一己利益而让别人无法享受属于他的利益,不能占有不属于自己的车站。
车站的故事作文800字【四】
我没走几步,就被赶了出来。在我张望的瞬间,我再次走出火车站的出口。第二次走出出口。
我又从我曾经走过的网吧面前走过,在积水低洼的地洞口走过。我想从火车站的出口走进去,然后跨过并排伸向远方的铁轨,回到地洞口的那一边,但是我被站务管理员赶了出来。我只好再次从地洞口走过。
地洞口在灰暗的钠灯照射下显得有些恍惚,我似乎看不清彼方。呼入一口新鲜的空气之后,我明白我已经走出地洞口,走出灰暗,走到铁轨的另一方。
我就在这儿轻轻地回望。回望我曾经跨过、曾经魂牵梦萦的铁轨。之前,我就是从这儿上去,然后看到远方驶来的列车在这里徐徐停下。远方带来的旅客,使口音的地域性差异在这儿分外鲜明。
我就是从这儿上去的。之后看见了石子,铁轨下面烙着的石子。我并没有那样轻盈地走过去。我感受到了铁沧桑的沉重,感受到了彼方的沉重。恣意增长的灰色在停靠的车厢上蹒跚,粗犷却又在明亮与灰暗之间的铁轨伸向未知的远方。我没有踟躇,我就那样完成了一次铁轨的跨越。
不同的轨道上停靠的不同的车厢在缄默,我无法透彻地领悟它们的表达。是坚于沉默还是安于安宁?不得而知。穿着黄色衣服的工作人员在旁边一一查看,没有了牵引力,它们在此处恬然地陶醉于他人他物的抚摸。
突然间想起老狼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总是被现实篡改。
关于现在,你总是彷徨又无奈,任凭岁月黯然又憔悴地离开。“
也许老狼略带沙哑的低声吟唱是对的。谁知道,列车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远方?
这儿完全没有了烟雨江南的痕迹,尽管此处并非江南。倘若不是江南,那么我觉得它能算得上半个江南。因为它有江南的特质。呼啸而过的列车带着旋风从海岸驶向内陆,从现代走向远古,从灵动趋向沉稳。“江南”里横穿梅雨季节的使者,逾越了时空的界限,把现代带去远古,把远古带来现代,把现代还原,让远古氧化。
我看到了从远方到来的列车。车上沉睡的旅客使列车更见沉默,站上稀少旅人让火车站愈显凄清。偌大的空间回旋着小贩叫卖的吆喝声,我望了望脚下的铁轨,开始往出口走。
之后我想再次跨越铁道,却被赶了出来。是否,每个真实的背后,总有坚守的人?
往回走,到了铁轨的另一边。
回望,发现列车正在启动,蹦溅出来的笛声,穿破高空。
车站的故事作文800字【五】
站在车站旁等待公交车,绵绵细雨诠释着带有几分惆怅的秋日,一辆辆车在我眼前驶过,逝者如斯,人群来来往往不知在下一刻这些人会在何处,又不知这些人又会不会在与我相见,若相见是否还在这里,是否还会想起。
一辆车驶过乘客有上有下,井然有序。人们匆匆而过,一辆车行驶过来,有离开,接着又是下一辆。一次次循环,虽然人不一样,做的样子却如此的相似。焦急,忧愁,悲伤,欣喜充盈着车站,淡淡的月光洒在黝黑的柏油路上,洒在人们的那多愁善感的心畔间。以许只有哪朦胧的月,青石板的台阶和深邃的车站铭记着历史,夜的苍穹、月、车站、车,人竟构成了一幅悠然平和的画。
上车,离开了驻足已久的车站仿佛现在我已孑然一身,坐在斑驳的车椅上望着窗外不知下一站在哪里会遇到什么,会看到什么。暮然间竟想到人生不就像一辆车或者是坐车的人,没有人会知道下一站在哪,下一站会做什么。在下一站会不会和你相识的人离别,会不会又有不认识的结识。
车上还有一老一小,一长一幼。小女孩在车上玩,老人则神态安然的坐着,看着的一老一小,心随之一颤小女孩老了不就好那老人一样吗,老人还是孩童时不是和那小女孩一样吗。此是生命像梦一般,今天我所见得想的会是巧合吗。
车停了下车撑开伞消失在冥冥黑夜,留下的还有命运曲折的安排
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经历,但却有纤毫的相似的人生。
车虽停了,我还在人生的轨迹上相遇知己。
车站的故事作文800字【六】
柴斯特大家都不会陌生吧!没错,它就是《时代广场的蟋蟀》里的蟋蟀,《中央车站》就是里边的一篇非常感人的文章,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现在就由我来给你讲讲吧!
星期五下午的音乐会之后,玛利欧的爸爸妈妈有急事必须外出,只有玛利欧一个人看报摊。玛利欧和柴斯特吃了晚饭,玛利欧吃了一个煎蛋三明治,他又给柴斯特拿了一片桑叶。晚饭过后,他们玩起了游戏,跳蛙是他们最喜的游戏之一,玩了半个小时,结果柴斯特跳过了三十四次,失误五次,在玛利欧每次都把位置放的很难的情况下,这已经算是很高的成绩了!到了十点,玛利欧打起了哈欠,他们便不玩了,柴斯特为玛利欧单独开了一场演奏会,玛利欧睡着了,塔克对柴斯特说:“亨利捡到一份时刻表,火车一个小时后就要开了!”“我马上就来。”柴斯特说,他环视着报摊,那盒面巾纸、那个闹钟、爸爸的烟斗。当他到钱箱的时候听了一下,把那个小小的银铃拿出来,去了排水管,塔克问它:“你拿这个东西干嘛!”“这是我的东西!”柴斯特说,“玛利欧说的!”塔克在一堆报纸里东翻西翻才找到一个小胶袋,说:“这里面是为你准备的食物,路上吃!”柴斯特努力记住时代广场的一切细节!“真奇怪!”最后他说:“有时候,觉得这个地铁站似乎也挺美丽的!”柴斯特跳上亨利的背,亨利和塔克带着它跑到火车站,柴斯特把自己安顿在一个风吹不到的地方。火车要开了,这时三个朋友才发现还有千言万语没有说,但来不及了,只好一个劲儿的道别,火车开进了隧道,亨利和塔克回家了······
读了这本书,我仿佛看到了这三个好朋友的友谊温暖了全世界,温暖了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心,我感悟到:只要人们懂得回报,爱就会充满人世间。我坚信,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忘了那三个好朋友,和他们永不灭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