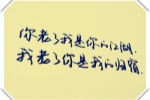乡土情怀类作文【一】
《乡土中国》开篇第一句“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正如费老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基层社会的确具有浓浓的乡土味。这里的“乡土味”并不是都市人眼中给乡下人冠上“没认识多少字、听到汽车喇叭鸣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的”的愚昧,而且经过实践证明,乡下人的学习能力并不比都市人差,只是对于知识和城市生活规律的需要没有都市人强烈。我们都知道,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制约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基层人民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的发展。再加上乡土社会是一个社会变迁速度十分缓慢的社会,人民已经习惯了乡土社会里安稳的生活,以致于不能适应其他快速变迁型的社会,这个才是“乡土社会”之所以“乡土”的原因。
费老认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语言和文字都是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工具,在乡土社会里,人们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和交流方式,有时候大可以不必使用文字,表情、动作、声音都是人们独特的交流方式。除非乡土社会的本质改变,要不然,文字下乡进程将会相当缓慢。
在社会结构上,《乡土中国》深入浅出地把社会分为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团体格局指的是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这个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而差序格局则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老还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都在水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而所谓伦,也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多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当代中国社会又何尝不是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在办事的时候,人们总是先找关系。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性质导致了许多“走后门”的现象,在官场上也导致了很多腐败的现象。这一个比喻浅显而又深刻,在看待人的私心问题上,让我感触至深。
当代社会所强调的德治依旧是源于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维系着私人的道德”需要靠个人的内在克制来遵守,于是很多应该遵守的规则便成了“礼”,“礼是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当代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礼治”依然存在。在农村,遇到矛盾的时候都是请一些长者或权威人士来评评理,实在调解不了才选择诉诸于法律手段。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无讼”的社会。
在一成不变的乡土社会里,保守封闭的特征形成了“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的现象。即使是在当代的民主社会,人们依旧不重视自己的权力,敷衍地对待选举活动,对政治大事也不闻不问。只有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才会寻求政治或者法律上的庇护。在乡土社会中,长老的生活是最为丰富,因此长老具有权威性,年轻一代对长老只可惟命是从。
虽然乡土社会的社会变迁速度慢,但是乡土社会毕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旧的社会制度不符合实际情况、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时候, “名实分离”的情况就会出现。“名”是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是不可以轻易改变的,所以人们只好依旧采用这个“名”而在实际的操作上采用自己的那一套“实”。这可能也折射出传统中国人们保守封闭的特点。
写到这里,不禁感叹费孝通先生孜孜不倦,敢于探索的精神,虽然《乡土中国》的创造时间离现今已经65年,但是这本书里所研究出来的理论依然是经久不衰,对于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本质看的如此透彻。我还要把这本著作精读几次,加深自己对乡土社会的理解。
乡土情怀类作文【二】
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归往何处?
“生于斯,长于斯,终老是吾乡”乃是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似乎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所谓的“熟悉”社会中:生活在为土地所囿,在一个先我而在的生活环境。正如“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所描述的就是这样因熟悉而得到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而这种因熟悉而得到的信任,并非是契约精神的重视,而是对行为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这样的礼俗社会,是一种没有具体目的,因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称之为“有机的团结”。与之相对应的是法理社会,“机械的团结”,是为了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
常说乡下人愚,究其原委,并非是智力不如城里人,而是缺少适应城里社会需要的知识。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乡土社会,空间阻隔小,面对面的群组并不必要求助于文字。
那么除了空间阻隔,还有就是时间阻隔了,比如个人的今昔之隔,社会的世代之隔。
在一个依本能而活动的动物不会发生时间上的阻隔问题。它的寿命是一连串的“当前”。谁也不能剪断时间,像是一条水,没有刀割得断。但是在人却不然,人的当前时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累积。
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多动用的圈子也不一定是相同的。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死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此,我们的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范围能收能放,比如,我们如何来定义“家”的大小?与之相对应的团体格局,所谓“西洋社会像捆柴”,团体之间是有界限的。
在差序格局下,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中,每个人都“克己复礼”。而在团体格局下,尤其是宗教观念,每个人在神前平等,神对每个人都公道。
家时一个绵续性的事业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而不是横的。
关于礼治与法治:礼治是”教化“,修身克己,其维持力量不在外部权利而是身内良心。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改革以适应法治的推行,防止法治的好处未得而又破坏了礼治。
权利的分类。横暴权利和同意权利。横暴权利时指社会冲突,上下之别。而同意权利是源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合作。
教化性权利乃是以稳定的文化传统作为前提。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的嫁衣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来说又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的过程。
长幼之序时教化权利所发生的效力。当文化不稳定时,传统办法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问题时,教化权利必然跟着缩小。
“在我们客套中互问年龄并不是偶然的,这礼貌正反映出我们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是长幼之序。”
乡土情怀类作文【三】
费老认为,乡土中国的家和族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不但承担着生育功能,更是作为一个事业社群承担了许多生育以外的职能。所以,家庭一般都是以家族的形态呈现的。对于这一部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乡土社会男女关系和感情的论述。作者引用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的理论陈述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啊阿波罗式的';一种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为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消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老说,乡土社会的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势必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很难逾越的鸿沟。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最后,费老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乡土中国》这本书不厚,也就104页,但是这短短的百来页文字去很好地剖析了我们国家最基础的社会,当然我们现如今所处的社会已较费老的那个年代相差甚远,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那个时代的社会本质来解释我们当代的某些社会想象,我想这可能也是我们这堂课的指定书目里面将这本书归为历史类的原因吧。有人说要认识中国就必须先认识中国的农民,而要认识中国的农民,就不能不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很赞同这个观点。
乡土情怀类作文【四】
在众多老师的怂恿下,怀揣着各种熟悉感细致地读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首先,孩提时代的乡土印象再次浮现:五线谱般的电线杆上鸟儿叽叽喳喳,清澈见底的小溪流里鱼儿欢蹦乱跳,绿油油的田野上牧童的短笛在轻声歌唱,一垛垛的稻草堆背后孩童们你藏我躲……可是,回首今朝的乡土概貌已不同往昔,禁不住泛起内心那股暖暖的乡土涟漪。
很是惊诧,费老在“乡土本色”一行文中提到,他初次出国时,他的祖母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他的箱子底下。看到这,心里暗暗惊喜那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是什么,并不是神秘的贵重物品,你是否也知晓了。后来,他祖母避人和他说了,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惊诧完后,也诉说一段我曾不敢启齿但与之相似的经历,第一次离家求学时,我母亲,不算很老的农村妇女,也是把一包用红纸包裹着的东西放在了我箱子的最深处,好奇地问:“是什么?”母亲语重心长的说:“给你保平安的,希望你出门在外一切平平安安……”一直压在箱底,直到后来算是翻箱倒柜找东西时,又显眼的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好奇心驱使我打开了它,一抔灶土和几颗茶粒。
这就是暖暖的乡土,不仅有母爱的寄托,还有那淳朴的乡土情缘牵系着。
我,也算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对乡村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很深厚、很诚挚的埋藏在心底。一踏进大学,身上那股“土里土气”的质朴俨然与外界格格不入,但日子久了,又生怕与乡村有关的“味道”将随着喧闹的外界渐行渐远,所以,有时就特别想回到过去看看,小时候的村庄、暑期支教的乡村、大一学习生活的南平校区。摸摸那片烙上童年脚印的黄土地,嗅嗅那乡土的味道,那是被自然孕育着千百年的村庄;在支教的期间,重温童年幼稚的游戏,阳光下童真无邪的笑脸洒满大地,充分展现孩子快乐的本性;怀念静谧的南平校区,修身养性,与世无争,悠闲的学习、生活便是一种享受。一种厚重感油然而生,这不正是某年某月后所向往、所追求的吗?
将来的某一天,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能够在自己的小天地,拥有半亩良田,披星戴月,荷锄而归。远离城市的喧嚣与人际的勾心斗角,融入大自然,真真切切的享受乡村的宁静与安详,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生长在暖暖的乡土上,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
也许,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能明白泥土的可贵,才能体会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具有浓厚的乡土性。虽然,城里人藐视乡下人土里土气,但是,在乡下,“土”是我们的命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随着季节的更替,锄地播种,精耕细作,尽管寸草不生,仍然期盼能从土里长出希望,收获果实。
或许,哪里来的最终本该回到哪里去,一如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立足于用汗水浇灌的那一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沉默而苍黄的土地,以此来报答那暖暖的乡土养育我们世代族人的大恩大德。
乡土情怀类作文【五】
近期热播电视剧《白鹿原》大受欢迎,描绘了20世纪初在渭河平原这片土地上,中国农村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部剧让笔者不由得想起由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教授作的《乡土中国》一书,是研究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
本书最初出版于1947年,许多内容和观点或许已经过时,但其中仍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笔者会将读书笔记分享给大家,共同学习探讨。
乡土情怀类作文【六】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什么是“忘本”。据新华字典解释是境遇变好后忘掉自己原来的状况和因此能得到幸福的根源。
而这就有些像有的城里人。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祖先亦是乡下人,他们忘记了这天的幸福是占人口80%的乡下人贡献的结果。不但忘本就算啦,更让人悲哀地是他们却反过来取笑我们的乡下人“笨”,“愚蠢”。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费先生给了我们很好的解释:乡下人不知道汽车来了就应怎样躲避并不是智力问题,而是知识问题,乡下人没见过世面才会茫然无措而已。
相对于城里人来说,乡下人就要重本的多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乡下人是万分重视土地的。他们深深的植根于土地中!到哪儿都不会忘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世代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几本上不流动,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那几个姓,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就正因这样,乡土社会就是一个熟人的社会,熟悉到自觉地去遵守传统的规范,不需要法律的存在,更不需要借助契约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这些都是基于人与人的熟悉。但在人口流动迅速的现代社会,我们还有那种熟悉吗?答案是没有!但同时我们的现代社会又缺少完善的法理去规范种种的行为,这也就导致了很多人游走在茫然的空间里,也就难免有很多城里人会忘记自己的本源,正因他们很多都面临信仰的危机。不像乡下人坚信土地就能够,坚信土地会给他们带来好运!
乡土情怀类作文【七】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费老在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乡下人在面对汽车到来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个是城里的孩子故作聪明地将包谷喊成是小麦。这两个例子很轻而易见地就说明了那个所谓的“愚”只是见识问题,与智力有何干呢?继而费老很自然地过渡到了“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到了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只是现在的所谓乡下人看到汽车就像看到自行车一样频繁,根本不存在不知如何是好的问题,到时还有些所谓城里人至今还不知道包谷和小麦有何区别,不过,这自然是题外话了。
乡土情怀类作文【八】
这两天在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在“差序格局”一章里面有这么一段关于东西方社会格局差异的很有趣的描述:他将西方社会的格局描绘为一种柴火捆的状态。
这些一根一根的柴火,则是由个人组成的团体。这些团体有非常清晰的边界:谁是圈子里的,谁是圈子外的。这个团体的责任与义务是什么。大家在这个社会框架下和而不同的组合在一起。费老把这种柴火捆称为“团体格局”。
而在中国,关系则是完全不同的,费老将其描述为同心圆,或者涟漪。一圈一圈的是由不同的亲疏远近组成的。陌生人,点头之交,半生不熟,熟人,近友,至亲之类的。这个圈的最中心,则是自己。
这里可以顺手解释一个词,即儒家的“人伦”。伦理的“伦”字即为这水波一圈一圈的形状。后来被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那么这两个模型有什么引申出来的应用呢?一个就是“公”与“私”的问题。在西方的群体格局下这个界限是被明确规定的,即那一根一根的柴火彼此之间明确的边界,这个是“权利”。在范围内可以适当地讲人情,但是范围外则是权利问题。
中国的“公”根据费老的说法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去占一下便宜,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存在。而有趣的是在中国的“私”不是自私,而是“利群”。就是为我这个小群体来谋求福利的利益。所以对于在局中不顾公共利益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反倒有可谓是“无私”的动机。
但在传统的涟漪结构里,这个圈的大小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而是极富伸缩性的。比如说“家”,究竟是配偶孩子的核心家庭,还是加上附近旁支的家族,还是把各路姑侄老表都算进去的庞大家族,到了最后一句“自家人”真喊起来,感觉天下一家也没什么问题。
而在这个伸缩之中,人在结构里的关系是会产生巨大变化的。可能上一分钟还热乎的很,下一分钟随着重新划定范围就可以冷眼相向。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至今依旧对人情世道冷暖如此敏感。
儒家一开始就没打算跟这种思维方式过不去,他们只是加了一个字——“推”。所谓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我们对于小家的感觉推广到更大的受众范围里去。而当所有人都被这一个个扩大的涟漪包裹的时候,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里天下大同也就不远了。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这套思维方式依旧在我们的文化里起着巨大的作用。大家还是会想要首先去照顾家人,一些想要改变世界受伤的人会想首先去爱那些爱着自己,真正重要的人。在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涟漪的界限与范围。同时在同一个圈内的,往往会出现一些很麻烦的问题。既然都是在考虑亲疏远近,一些至亲之人的博弈就会变得很麻烦,或许解释了为何婆媳关系是中国自古的老大难。
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个模型里是没有什么界限意识的。甚至没有自己。所以很多父母含辛茹苦舍命付出的同时也对孩子横加干涉。当我们批判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或许这个里面也有很重的文化因素呢。
最后,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对于公共事务是一个多重囚徒困境:谁不占便宜谁吃亏。但同时大家都占便宜就会导致这个系统的崩溃。所以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道德来对所有人进行限制和约束,大家同时也要对破坏规则的人进行制裁或者舆论轰炸。
这些听起来,似乎都没有过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