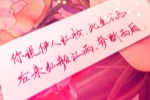有关思念作文550字【一】
小时候,常见在外求学的小姨泪流满面的与姥姥诉说其别前别后的思念之情。因此,我自以为那时的我已将思念读透,那就是分别时的依依不舍,相见时的哽咽无语。没想到十年后的那一次,我才真正读懂了思念。
老爸是一名机关干部,经常出差,不过时间都很短,最多三四天。以前他出过差,我也没当回事,少了一个人约束我,乐得我都要去感谢他的上级领导了。
这不,星期天,老爸接到命令,到烟台党校学习。星期一,早上六点,他便要出发,我懒地过早起床,只在被窝里与老爸道了一声“再见”,心里想:总算少了一个在一旁唠唠叨叨、指手划脚的了!越想越高兴,唱着歌我就从床上一跃而起,……
老爸去学习的时间很长,老妈说有一个多月,且留当地住宿,只有星期六、星期日才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
星期一我觉得不错,家里的空气比以前是那么地自由,放松。可后面的时间问题就出现了。星期三,老妈有自习,谁从地下室向上拿煤呢?不拿煤怎么生炉子呢?不生炉子暖气能热吗?可我们母子要抵住寒冷呀,老妈只得拿出电热扇打着。此时,我突然明白,原来老爸平日里为家做了那么多,一种敬佩带着思念的感情油然而生。
等到星期四的时候,我已全然受不了。平日里老爸是家里的活宝,他的每一句有意或无意的话都能引得我和老妈的大笑,欢乐因他而充溢着整个房间,而且我和老爸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学术探讨与争论”无法正常进行了,所有的家国大事只能暂时放置一边了……因为我的身边少了一本活字典。尽管老爸每晚都打来电话,事事嘱咐我和老妈,但少了一个人,不禁显得冷清了许多。是呀,在我吃饭的时候,在做完作业的时候,在上学路上,我都会想起老爸。他在烟台学什么知识呢?他课余时间的生活比我快乐吗?他穿得的衣服保暖吗?他吃得饭菜合他的胃口吗?他这几天是瘦了还是胖了?我叫嚷着老妈“命令”老爸早日回来,心里呀,急得不得了。
终于等到星期五了,我双眼紧盯电子台历,每过一秒,我都高兴,因为我就要见到我亲爱的老爸了!
傍晚,老爸回来了!他说他也很想我们,没等单位派车去接就搭个便车赶了回来。
此时,我才明白为何小姨离家回家总是爱流眼泪,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思念一次就是半年呀!
思念是什么?如今,我才懂得,它不是仅以眼泪为表现形式的,以亲人离别的时间长短来衡量的情感。思念,就是对你所思念的人给予的那份无法用语言描绘的真爱。
有关思念作文550字【二】
思念,像一块外面包着的巧克力糖果,一层层苦涩褪尽后是小小的甜。但苦涩才是主味,那股甜只会稍纵即逝,太短暂了。
家乡,理论上说我应该是不会思念的,因为现在我居住的地方经济发达,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但是,在长期的物质支持下,我的内心渐渐觉得有一点空荡。不知不觉之中,我开始思念起家乡来。在这次的暑假,一次偶然之中我又一次走到回到家乡的路上。
家乡是什么样的呢?
记忆里的家乡,空气是那么纯净,没有丝毫的污染,呼吸起来感觉很舒服。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曾经退出我生活中的人和物无不让我思念。还记得夏日的夜晚,月亮照亮着大地,没有灯光点亮的昏黄的光,只有一群群如同游动的星星般闪亮的萤火虫。在萤火虫黄绿色的光芒照射下,一片片白日里原本是金黄色的稻田随风浮动着墨绿色。那断断续续的光芒和月光一起照亮漫长夜晚,让人不得不沉浸在这一幅大自然纯天然美之中。
离开五年了,我还记得走的时候那时候树木低矮,头顶还很空荡,今年夏天回来一看到头顶上的很高处,树木就像孩子一样在时间的洗礼下变得越来越茂盛,长得越来越高。
思念家乡,只因我爱她。
有关思念作文550字【三】
我思念的故乡,当我凝视窗外迷茫飘渺的雨丝,听着优美、动人的乐曲,我的心被带回了你的身边。曾经触摸到土地的灵魂,我知道,这时的我身处在地球东半部的黄土高坡上。在坡上的空地里,我席地而坐,风从身边吹过,吹走了我身上的尘埃,吹走了我全部的忧伤和欢乐。我开始静静地沉思,心灵便有了一种超俗的意念。身处在原地的时候,没有细心,那是因为心早就被轻风吹向远处,可现在回想起来,心灵深处一片的平静。
我思念着的故乡,如果我的心是故乡放飞的一只鸽子,那我温暖的窝一定是你----我的故乡。秋色如水,春光明媚,冬夜里的星空,夏日里的炽热,都是我深深的思念。故乡的一棵树、一片土、一朵云、一团雾、一阵风、一滴雨、都在我的眼前浮现。经过弯曲的小路,来到河边的林子,我捡起了落在地上的一片黄叶。看着这片落叶,我把它顺手藏在了岁月的抽屉里,等待新生的机会。
有关思念作文550字【四】
记得我刚来到四川时,妈妈一人在广安市(小平故里)打拼,工作很忙,房子还是租的,无法照顾我,所以把我送到县城外婆家待了一年。
在外婆家时,我可调皮了,简直是一个麻烦小孩。一会玩玩那里,一会翻翻这里,房子真的被我翻了个底朝天。
外婆每天都会训斥我,我都无所谓,习惯了。但是最可恨的是外公,这个有歇斯底里的外公,他的东西,谁碰了,跟谁追究到底。我在外婆家不能释放所有的“激情”,只好到楼下三舅爷爷家中去玩了。
刚见到他时,觉得很搞笑。他是一个秃头老人,头油光光的像鸡蛋一样,十分可爱;大大的嘴厚得像饺子,笑起来特别灿烂,真是个好玩的老爷爷。
在三舅爷爷家,我可以毫无保留的“激情燃烧”,真是爽呆了。无论我做错了什么,两位老人总是尽可能的包容我。有一次,我在他们家里发现一桶鲜而深的红色豆子。奇怪了,我见过身材娇小玲珑的绿豆,也吃过颜色鲜活明亮的黄豆……,“这是什么豆呢?”。三舅爷爷说:这是红豆呀!哇,好特别的豆了呀!一颗颗大而饱,红彤彤的看着真喜庆。我又问:“为什么买的红豆比米还多呢?”,三舅爷爷说:“因为它不仅味道好,营养也高呀!”说着,他用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小脑袋。
后来,每次看见他们早上吃的是红豆沙包、红豆稀饭,中午吃的是红豆汤、红豆炖猪蹄、红豆闷红烧肉时,我就按耐不住,口水流得三千尺呀!
有一次,两位老人请我与他们一起共餐。我高兴极了,蹦到椅子上,挑起筷子,狂吃一番,我美滋滋地吃了一顿,味道好极了。也许红豆的味道是豆子中的瑰宝,我爱上了红豆,我巳不能抵抗红豆的诱惑了。
以后,我隔三差五地就去楼下享受着红豆的快乐味道。由于我的贪得无厌,红豆很快消声灭迹了。
爷爷问我:“源源,你还想红豆吗?以后爷爷再买给你吃吧!”。可是我却大发脾气,闹着让爷爷现在就快去买。三舅爷爷脸上有些为难,走进小屋里和三舅奶奶争论了好一会儿,他出了门,消失在金色的烈日下。
一下午了,天出渐渐泛起一层层迷人的紫霞,黄昏到来了。几颗调皮的星星早早地来到天空玩耍;房檐上,乌鸦在纵情高歌。
门开了,是“红豆”归来了。三舅爷爷满头大汗地提着一大筐大颗饱满的红豆,三舅奶奶急忙接过红豆,扶着爷爷到椅子上歇一歇。我仔细端详了一下三舅爷爷,他筋脉突兀的手有些红肿,一串串豆大的汗珠顺着苍老的脸颊边缘慢慢地流下。我问三舅奶奶,爷爷怎么这么累啊!奶奶答:“现在市场上没有红豆卖了,只有到农村才能弄到”。
是啊,乡村的峭壁和长途跋涉是对老人莫大的考验啊!但是面对我的无理取闹,爷爷毫无怨言,不顾路途艰辛……哎!此时,我不禁感概万干,觉得自己有些自我形秽。我问爷爷:“其实我只是闹着玩而巳,你又何心如此认真呢?”爷爷答:“没什么,源源是小客人嘛!”我觉得他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日子一天一天地擦肩而过,终于到回广安的时侯了。
为了我,三舅爷爷一大早就开始忙里忙外了,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中午,他俩请我到他们家吃这顿离别饭。一看饭桌:简直就是红豆之“满汉全席”,色、香、味俱佳呀!吃着吃着,我不禁泪落纷纷……。
走时,我还拿了一颗最大的红豆,装在包里,留作纪念。
后来,我才知道红豆又叫相心豆。
几年了,那颗红豆早与我失散在天涯海角。后来,三舅爷爷居然得了肺癌。
几个月后,三舅爷爷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后,我的心久久……无法平息。
三舅爷爷永远闭上了眼晴,那慈祥的双眼,消失在人间,消失在温謦美好的人间,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走了。
我不知道那颗纪念的红豆在哪里呀!这么多年了,那颗红豆肯定“老了”。但是,我希望那颗老而不朽的红豆能代表我对爷爷深深的思念。
有关思念作文550字【五】
曾经,外婆家的那条小巷子里,有一位卖艺人。
瑞安飞云那时有许多老房子,邻里间都熟,有家小作坊,门前有个卖艺人会在那表演一些小技艺。其实按现在来说是一些小魔术,通过手的动作,让糖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看热闹的孩子很多,我每周日都会去外婆家,自然也会去那玩儿。
听说他都是中午到那表演,太阳下山了回家,他帮着那家作坊招览生意,表演好了就进店买吃的。
他个子不算高,却很壮,灵活的手指使我们看不清动作。每天都会有一堆小孩围在那儿,看他表演。他的每套动作都非常规范。表演前,他会先把桌上白色的面粉堆开,变成一座“小山”。再把表演道具拿出,有三个不同颜色的杯子。随之,他再把一颗奶糖放在一个杯子下,让我们看好了。他快速地把三个杯子移来移去,有时围成一个圈,有时还会把其中一个杯子扔起来,拍拍桌子,杯子再掉下来……最后,让我们猜在哪个杯子里,可是,糖却哪儿也不在,跑到了旁边的面粉小山堆里。一吹气,一颗米白色的糖出现在面粉里。“看见没?糖不见了!进店买吃的,说话算数!”我们也只好去买。
卖艺人有些胡渣,第一次见到他还有些害怕。“小朋友,你们喜欢吃糖吧,猜到糖在哪,我就把糖送你!看好喽!”他做的动作很娴熟,眼睛有时盯着我们有时望着天空,还会一边唱着歌一边表演,几天就会换新的动作,我们都不会厌烦。虽然,他表演得满头大汗了,却还在那儿表演得很卖力。一天下午,他似乎在移杯子时有失误,孩子们拆他台。“这局不算!小失误,小失误!”嘿嘿,再来一次,他有些紧张了,但过一会儿就好了。
每次收摊后,他都会把所有东西塞到一个袋子里,再把桌子扛到肩上,走!背影很魁梧,走路一摆一摆的,像只鸭子。
前年,他不见了,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也不知什么原因,心里有些失落,不知为什么。曾想着会再见到他与的他的“小魔术”,这些玩意儿使我觉得很新鲜,因为在城市里看不到这样的卖艺人。他表演时的个性也让我记忆很深。只要有去外婆家,我都会去看看他在不在,但每次都带着期待去,拖着失望回。
“外婆小时候也经常看卖艺人表演,人比现在还多。但现在卖艺人越来越少了,你能感受到,很幸福!”前个星期,外婆对我说。那个卖艺人不在城市里出现,乡下的小巷里也没了……
有关思念作文550字【六】
还,记得昨天,那个冬夜,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了一切,只剩寂寞更沉淀。心已淡然。携一缕寒,飘进荒芜;只需一季,便会重生。空气中的温暖不再遥运,仿佛即使闭着的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蓝白色的思念,突然停留在永恒的'瞬间……
――题记
一轮明月挂在中天,淡淡的月晕,宛若少女脸上的粉黛,更增添几多妩媚,几分姿色。没有众星的点缀,亦没有百花的装饰。冬天的夜,令人着迷的是一种意境。雪还在落,它飘扬着上天的语言,传述着远古的语言。
闲坐着,任凭时间流淌,耳际只有钟声依旧徘徊。“走,出去走走吧”。两个朋友跑来对我说。
“好吧,难得这个夜晚。”
雪夜很静。远近的房舍都黑黑地睡了,梦中呓语被严丝含缝的门窗关住。满世界唯有这雪野里执着地响着“咔嚓”“咔嚓”音乐般的声音。
一圈一圈地走着,我们无言。白色的花瓣落在朋友们的发梢上,顷刻间消释了。
一个朋友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看,对面居民楼上有个小孩看咱们呢!”
我抬头一看,果真如此。一个小黑点。
另一个朋友笑着说:“让我来逗他一下。”他用手放在嘴上大喊:“喂,小孩,干嘛呢!”这下子,小黑点消失了,我们三个会心地笑了。我感的手心热着一股流在涌动。
那个朋友对我说:“你怎么这几天蔫的?没有一点儿精神。”
我苦笑着,说:“也没什么,只是感到有些压抑。”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墨蓝色与白色溶为了一体。最深的内涵,是深邃和宽广。
朋友缓缓地对我说:“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空篓子,然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从这世界上捡一样东西放进去,所以才有了越来越累的感觉。既然都难以割舍,就不要想背负的沉重,而想拥有的快乐。像我这样,做自己喜欢的事。”
于是,他用手放在嘴上作出喇叭状大喊:“我――很――傻!”
“我――也――很――傻!”我模仿他。
“我――不――傻!”另一人朋友引得我们发笑。
“我――很――快――乐!”
“我――也――很――快――乐!”
“我――更――快――乐!”
三人的声音穿过了雪夜,在校园上空久久回荡。风儿将它们传送至天堂,聆听快乐的到来。
天上的雪是地上的雪,天上地上已经没有了界限。我们赞颂着白色,又被这白色弄湿。我们又在友谊晒干又晾干,整个世界被这无尽的纯洁陶醉而感动。
唯一不需要写诗的夜晚,是下雪的夜晚。空中飘着的,地上铺展的全是纯粹的诗。树木的笔寂然举着,它想写诗,却被诗感动得不知诗为何物,于是静静地站在雪里站在诗里,好像在说,笔是多余的,在宇宙的纯诗空前,没有诗人,只有读诗的人;也没有读诗的人,只有诗;其实也没有诗,只有无边无际的宁静,无边无际的纯真……
有关思念作文550字【七】
和东四的孙大姐通电话。孙大姐是居委会的,在编本地的一本志书,希望用我的一篇稿子。孙大姐这人我没见过,但话里听得出来,一提几号院,那里头装着几口子人,一百年内有过什么有趣的事儿,都在人家脑子里装着呢。聊起来,就好像回了一趟家,不知不觉,聊了将近一个钟头,话题早已经离开了稿子,转到了东四的贝勒爷、石头狮子上头。结束的时候还有些意犹未尽,跟孙大姐说,回北京的时候,看您去。
挂电话的时候,听见那边屋里其他的人在说笑,有一个清脆的女声笑得很张扬地说:“你就贫吧你。”
电话挂上了,那句话的影子,仿佛还在耳边呢。不是地道的胡同北京人。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闭上眼睛,这话音儿好熟,说这话的多半是当年胡同里我称作姐姐的那些北京女孩子们。
那时候自来水还没有装进各家,早晨起来,大伙儿得拿着各式洗脸盆子上院子中央水龙头前头排队等着去,经常看见不耐烦的女孩子,把洗脸盆放在脚边,当着人面大喇喇拿面小镜子就开始梳头。前些日子看篇文章里有说法,说有教养的女孩子绝不当着男人的面儿补妆。要照这个说法,我们胡同的姐姐们大概没一个能算淑女了,可她们的头发多半又长又亮。
这时候,往往就有自做潇洒的GG想方设法地凑过去聊天,中间不知道说了什么风话,便听见这样清脆的女声咯咯笑着来一句——“你就贫吧你。”
有多少粗线条的鸳鸯红线,就是这么串上的呢?只怕胡同里嫁了人的JJ们自己也记不得了。
在胡同里,街坊,是个很说不清的词儿。邻里吵架骂街的时候,二大爷瞪着斗鸡眼,那模样简直可以吃了四大妈,可是每天他还得照样和四大妈对门,闻四大妈家韭黄炒鸡蛋的香味抽鼻子,昕四大妈家电匣子里“坐宫”唱到精彩处要关灯睡觉喊一嗓子:“四姐您让我听完这段儿成不?”
街坊之间没有秘密。你们家还有几棵葱邻居比你还清楚,谁家的小家伙拉屎了一院儿的人都得跟着闻味儿。晚上睡不着觉,略一凝神能听见后院那谁家的新媳妇和新郎官也没睡呢,两口子叽叽喳喳能聊到半夜,当然声音都是压低了的你绝听不清两口子的'悄悄话。只偶尔那新媳妇会咕的一笑,不自觉放大了声音让你听到一句——“你就贫吧你。”
多少年后,忽然觉得,那一句略带娇嗔的话里面,不知道有多少旖旎风光呢。
更多的时候,是夏天热了,看见某个院门里面几个黑影靠着门框磕牙,间或有下夜班的回来,推着自行车从几个人中间穿过进院,还得低低地说一声——对不住。
这就是乘凉呢。哥们儿姐们儿聊着天,还能看看马路上的风景——马路上有什么好看的?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大伙儿都那么着,谁也没觉得不正常。
几乎无例外的是每个人手里都抓着一把瓜子,一边聊,一边噼噼啪啪嗑得热闹。有时候,就听见嘎嘎大笑,不知道谁说了什么笑话,便有很不淑女的对着那讲笑话的男生肩膀上猛推一把。半戏虐地说:“你就贫吧你。”
那种笑声消散在胡同里,就像草叶上的露珠一样自然。
一瞬间,仿佛胡同里头的国槐已经在了眼前,耳边还是那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清脆地笑着的声音——“你就贫吧你”,还有故都那淡淡的煤烟味儿。
电话里听来的一句话,就让人想家,还写了这么多,我这是怎么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