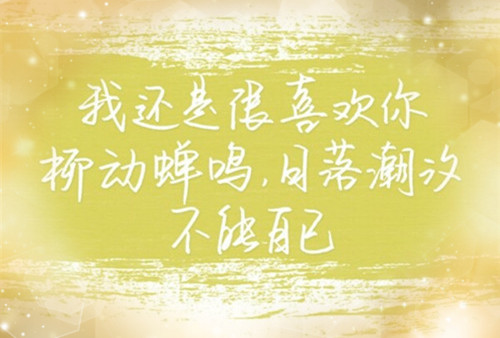
苏醒作文800字【一】
大部份时间片中的人物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探讨「良心」(conscience)。这个词似乎有着天然的、不容置疑的正当性,而锡兰却刻意强调了「良心」制造的种种矛盾──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人际关系层面。比如,他讴歌伊斯兰教的圣洁,却嫌恶神职人员的脏鞋;推崇互助精神,却信不过任何一个邻居;他爱人性(humanity),却恨每一个活生生的人(human)。和妻子争执的时候,他问「Idolizing a man, and then being mad at him because he's not a god. Do you think that's fair?」说得不正是他自己吗?作为一个扶手椅学者(armchair scholar*),他活在抽象概念的世界里,那是一个真空无菌的完美世界,只容得下「道德」「原则」「良心」这些没有生命的名词,而绝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能够栖居的,包括他自己。他对自己的审判,一点也不比他对神职人员和他姐姐的审判更仁慈。
这种自我审判,某种意义上源於对自身动物本能的抗拒。
Aydin醉酒后说了一句,「Justice doesn't exist among animals」。果然人喝醉之後容易开智慧。是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动物的生存本能并不包括「慈善」和不以利己为基础的「利他主义」。然而我们常常忘记,人类终究也是动物,再多的文明和教化也压抑不住从骨头和血液里流出来的动物本能。其实到头来,又要回到弗洛伊德老人家的模型,「良心」是超我(superego),是一个social construct,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是价值判断;「动物本能」则是本我(id),是原始的慾望,是马匹对缰绳的挣脱(要自由),也是被击毙的野兔最後的心跳(要活下),是没有是非正邪之分的。
在Aydin身上,超我和本我的斗争异常激烈,以至於自我(ego)难得片刻安宁,亦失了作出实际行动所需的精神能量。Aydin在朋友家喝酒时最後说了一句,「我们总是被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蒙骗。起床时有满脑子的计划,而一天还是在碌碌无为中过了。」片中有好多没有付诸实践的想法,比如乡村女教师的请求,Aydin读信时满心热忱,最终却什麽也没有做;还有想做而没有做的慈善捐款账单以及想而没有成的伊斯坦布尔。包括他写作的状态,也是缺乏行动力的。他甚至连对妻子的爱也无法执行。我猜想他是一个典型的洁癖完美主义拖延症患者,一切在他想像的疆域里都是完美的,而一旦照入现实,便不再受他的控制,便免不了纰漏。与其妥协接受不完美,他宁愿什麽也不做。
弗洛伊德臭名昭着的'「死本能」似乎也能用来解释这种「惰性」。他说,生命由无机物演化而成,人从黑暗、温暖而平静的子宫而来。生命一旦开始,一种意欲返回无机状态的倾向随之而生。惰性让我们站着想坐下,坐下想躺下,而躺下即是死亡的状态,而睡眠与死亡的境界与人所来自的地方条件相似。惰性也让我们不思进取、安於现状,倾向於依赖熟悉的人事物,希望回到孩提时代甚至是母亲的子宫内。猜想超我﹣本我斗争激烈的Aydin「归於寂灭」的愿望也特别强,因此懒於行动。
影片的最後,Aydin终於开始写《土耳其戏剧史》。我想他也许更应该重返舞台,在那里他可以饰演浪荡子、堕落狂或者一只狗,他可以「被允许」「正当地」下流、撒野和狂吠。这对他整合超我﹣自我﹣本我有好处 : P
*Armchair Scholar指的是不通过实验或田野调查获取信息,而只凭现有的文献进行学术工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