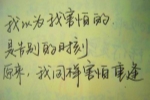我们的铁蛋作文【一】
今天是星期五,老师说下午要给我们重新安排座位,我心里既期待又担心,我会和谁同桌呢?
”叮铃铃、叮铃铃\"上课铃响了,我们的班主任大张老师走进教室给我们排座位,张老师说:\"谁愿意和刘梓桐同桌?”这时,杨思航同学举起手说:“我愿意。”我听了心里很开心。
我的新同桌是个小男孩,头发黑黑的、短短的。眼睛大大的、亮亮的,像闪亮的星星。皮肤不白不黑,他的嘴巴红红的、身体胖胖的,特别可爱。
他不但长得可爱,而且待人很热情。
我一和他同桌,他就从书包里拿了一本书对我说:\"这本书可有意思了,你要不要看?”我说:“谢谢,下课再看吧。”
希望新的学期我和我新同桌一起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我们的铁蛋作文【二】
一头乌黑的长发,薄薄的嘴唇,一笑起来就露出两颗大板牙。一乐开怀,便把眼睛眯成两条缝,这便是我的同桌——季蓉蓉。
我总喜欢叫她“老季”,也许是因为她比较man吧!有一次,“欠揍大王”李宇繁又来给她起外号、造绯闻了,她两眼一瞪,双腿一抬,小李立马四脚朝天,瘫坐在三米之外的地上。
老季是我们的组长,她大概是除女汉子罗雨洁外最凶的组长了。有一次,我迟到了,刚跨进教室,她就一声河东狮吼:“怎么才到,就差你作业没交了!”她夺过我的书包,一把扯出作业本,叠在课桌子上。我吓得两腿发抖,一边坐下,一边向她苦苦求饶:“组长大人息怒,组长大人息怒……”她两手一抄,哼了一声,抱着作业走了。
她成绩不错,我从第三名的宝座退下来后,这把交椅就交给了她。即便这样,我们偶尔还会打打组合拳。一次数学考,她有几道题不会做,我也有几道棘手题,我们趁老师不注意联手作弊,互抄了事。有一道题,我俩都一筹莫展,于是低声讨论起来。没想到,数学老师一回头,两眼放光,“唰”地就是两个粉笔头,全都正中靶心,数学老师“武林高手”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我俩赶紧低下头,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六年了,50位同学很快就要各奔东西了。每当想起校园里发生的那一幕幕,依然是那样的难忘与美好。是吧,同学们?是吧,老季?是吧,我的可爱的同桌?夜已深,今天无眠。耳畔回荡着优美而熟悉的旋律:“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我们的铁蛋作文【三】
看到这一单元的习作要求时,我不禁愣住了,顿时陷入了遐想中,觉得很矛盾,很犹豫。
这次的习作要求是让我们对一直疼爱、呵护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声:“我爱你!”我都六年级了,从小到大还从未对他们说过这句话,现在说出来,实在不好意思。但仔细一想,不就是因为有了父母的爱与呵护我才幸福的长这么大吗?思前想后,我觉得让我当面说出“我爱你”这个方案太难办,于是决定把“我爱你”这三个字写在小纸条上让他们看。
这天,爸爸妈妈都出去办事了,弟弟也去上英语辅导班了。我独自坐在凳子上想了半天,心里又忐忑又激动又紧张,我甚至想到了他们看到纸条的n种场面。屋里很静,阳光穿过窗外的树枝温暖的照着我,只能听到墙上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我仔细的听着这每一秒的震动,想到了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他们无时不刻都在爱着我,而我,不过要在小纸条上写个“我爱你”,又算得了什么?豁出去了!我站起身,在一张干干净净的白纸上,认认真真的把这三个字写出来,耐心的等着爸爸妈妈回来。此时秒针的声音更响了,像小鼓在轻微的敲打,时间怎么如此的难熬呀!
已近中午了,阳光更暖和,更刺眼了,看来这是上帝特意为我准备的一天。没过一会儿,就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他们回来了!我急忙穿上鞋给他们开门,爸爸妈妈手里掂了一大堆东西,后面跟着乐呵呵的弟弟。
我迎上去,接过东西,等把东西一一放好,我结结巴巴的对他们说:“爸,妈,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说着便把他们拉到里屋。
刚要把小纸条拿出来,正在看电视的弟弟就大声对我叫道:“什么呀?姐姐,什么呀?”
“没什么,你快看电视吧!”我忙说。还好弟弟不问了,专心的看起电视来(我心里松了口气,要不被弟弟看到,我就……)。
妈妈笑着说:“什么呀?搞得神神秘秘的,我还要做饭呢!”
“不急,不急。”我说。我一鼓劲把小纸条拿出来,双手举到头顶让他们看。
爸爸看了惊奇的说:“咱妞啥时候懂事了?!”妈妈也一愣接着又轻轻的笑了。看到他们幸福的表情,我也不好意思的笑了。
在心里,我想对爸爸妈妈说“哈哈,你们的妞本来就是懂事的,只不过她不擅于表达而已,你们对我的爱,我都记心里了!”
我们的铁蛋作文【四】
??们的班级咳、咳、咳,我来了,今天来谈谈咱们班的阶层现状,先别问我班内为何会有阶层,阶层立场不只有社会上才有吗?NO,NO,NO,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必然有斗争,有斗争就存在站队问题,所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判断就形成了阶层立场。
首先,分析君王阶层———班主任级,君主;顾名思意就是掌控最高权力,大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威严。还好我们的班主任是体察民情的明君。
其次,说说丞相阶层———班长。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传授着君主的指示,管理着宠大的队伍。看是让人羡慕,实则格外辛劳。
接着,郡首阶层,———各大委员。一手掌权,却又无军权,管理中遇到难题,碰到钉子就无可奈何,只好面承上级,反应情况。
之后,纸老虎阶层———各位高官的狐朋狗友,凭借朝内有人,狐假虎威,若遇上个凶神恶煞,就灰溜溜地投降举手了,也正是“墙上芦苇,头重足轻跟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再次,地主阶层———组长类别,职权不大,恰大有喜好指手划脚的本领,凭着自已小小权力,把手下掌控的三五小兵摆弄的团团转。像这种阶层何德何能担复兴大任,做时代新人。
最后,奴隶阶层,———无官一身轻的大众学生,他们虽然因种种因素未能戴上任何头衔,但是是群体的大多数,个个都是精英骨干,事事心知肚明,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我们只是分工不同,目标一定是一样的。都在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一个梦想。
我的分析也许浮浅,但是很大程度上给各个阶层敲响了警钟。愿各阶层有则改之,无则加冤。
我们的铁蛋作文【五】
夜未央,在城市边缘有他们这样一群人:洒了一天的汗水,回到狭窄的木屋里,清洗后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盖上单薄的被子,慢慢睡着了。
他们只是生活在贫穷地区的农民,每天为了家里人能过上好日子,能够吃得饱、睡得暖,他们不惜每天天刚亮就起来去干活,待到天已全黑才归来。归来时身上的衣服已经全湿,可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而是欣喜地想着过了一天,离好日子便更近了......
一个清晨,万簌俱寂,东边的地平线泛起的一丝亮光,小心翼翼地浸润着浅蓝色的天幕。我辗转了一整晚,索性趁天未全亮起身去看日出。刚下楼走了不久,便看到两名中年男子。他们着装十分不一样,于是我就好奇地打量起来。其中一名男子穿着黑色的衣服,虽有些褶皱,但还算干净。因并无特别,我的视线就快速地转向另一名男子。他戴着一顶黄色的安全帽,蓬松的头发夹着银丝被帽子罩住了,额头上有淡淡的皱纹,有着说不尽、道不得的沧桑。他穿着一身灰色的工服,上面却布满了细小的尘埃,若不是他动了动身子,我是怎样也看不出来的。我脚步故意放慢了些,终是听见了他们的话语。
只见,灰色男子笑着望着对方,说道:经理,今天是不是到俺发工资了?说完,露出一丝期待的神情。那个经理听后从袋中掏出一叠钱,递给他,还说了句:好好干,便拍了拍他的肩走了。接到钱后的男子笑意越发浓烈了,也顾不得手脏,一手拿着钱,一手沾了些唾沫慢慢地数了起来。不一会儿,许是发现边上的一缕目光正望向他,他便抬头望向边上的我,竟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将钱塞进口袋中。只是那锃亮的目光与那扬起的嘴角却怎么也遮不住他内心的喜悦。
少时,他向我点点头,转身离开,嘴中还小声地说着话:今晚俺要买块猪肉给娃娃吃,给娃娃娘买件新衣,还要寄点钱给俺爹娘......许是他越走越远,后面的话便听不清了。路边上,风一阵大过一阵,树叶在风中摇曳,我的目光越过眼前的平地,他的影子挟裹着晨风在平地上,逐渐模糊。
像他这样的他们幸福快乐、勤奋、努力,不仅仅是为了摆脱贫苦的生活,还是用自己的行为激励更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追赶比他们条件好的我们,不因为他们而拖累进步的国家,让国家富强起来。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照在他们身上,才发现他们咬着牙向城市中心走了很长的路。他们不会退缩,因为他们坚信,他们终将会变成我们。
我们的铁蛋作文【六】
一堵墙,隔开了我们。一张纸,分开了我和你。我们的相遇就好像是在昨日,没想到今天我们就要分别。我们在20xx年相识,在20xx年分别。
毕业了,推开教室的门,里面有的是追逐打闹的我们,而不是一片寂静;黑板上有的是老师留下的笔记,而不是一片漆黑;桌上有的是一本本书籍和一支支钢笔,而不是一片荒芜。
还记得小升初前一天老师给我们听写,写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名字。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的听写本上都是一个大大的A。
还记得老师以前总是对我们唠叨他们教的上一届怎么怎么好,现在我们终于成为老师口中那神奇的上一届。
还记得老师总是说学校是我们的家,我们要爱护它,现在我们终于离开了这个家,这个有我们六年的记忆的家。在学校最偏僻的一个角落,我们种下了一株太阳花,每天每个人总要去看看它,后来,它竟长出了一大片。
再后来,我们毕业那一天,老师带着我们把那些花都拔了,独留下了最初种下的那一株,老师说:“这最初种下的就是老师我,你们就是后来长出的那一些,现在你们都走了,那么那些还留着干什么?”我们沉默了,最后,我们怎么回的教室,没有一个人记得。
进考场前,所有人都在谈笑风生,但当从考场出来时,很多人都哭了,唯独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分别,我们还在一起。可是,在领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其他班上的人都快走完了,我们还在教室,操场嬉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出了校门口,我们就要各奔东西,很难再聚在一块了。出了校门口,有多少人哭了?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视线已被泪水遮挡。
以前,有多少人盼望着毕业,可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又有多少人舍不得。教师节,我们约好去看望一下老师。当我们来到那儿时,迎接我们的\'是熟悉又陌生的钢筋水泥。
学校还是那个学校,老师还是那个老师,只是我们已不是以前的我们。不经意间听到两个小朋友说:“唉,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毕业啊,那个时候就不用再天天望着老师了。”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想的,只是现在我们后悔了。那株太阳花似乎又长出了新的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