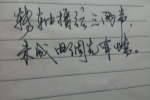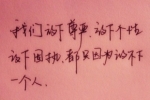考研英语作文原创模板【一】
您好!
您知道吗?每当我走过语音室时,总会透过明净的玻璃窗去看看里面的设备,语音室里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那么新奇,那么吸引人。跟着您,在高科技设备装配的语音室里学英语,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可是,自语音室建好以来,您从未带同学们进去参观过,更没带同学们进去上过一节课,这使得我的愿望变得那样渺茫。
王老师,记得您每次在我们教室里上课时,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在小声说笑,因此,教室里总是乱哄哄的`,可您却很少制止。王老师,维持课堂秩序是您的职责呀,您为什么不去制止他们?还有,您每次提问学生时,一旦同学回答不上来,您总会露出一副不耐烦的神情,为此,许多同学感到很伤心,好多同学也不喜欢上您的课。
王老师,学校培育了我五年,我希望学校越办越好,希望老师能教得开心,我们也能学得开心。因此,我诚心诚意地给您提几条建议,希望您能采纳。
一、每周带同学们到语音室上一次英语课。
二、您不要不管那些上课小声说笑的同学。作为一名教师,您有责任对他们进行批评和教育。
三、今后,请您对那些回答不上问题的同学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并耐心地讲解,这些同学会非常感激您的,他们也会越来越喜欢您的。
王老师,如果您能采纳我的建议,我将十分开心。我坚信您一定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好老师!
祝您工作顺利!
您的学生:张辉君
3月26日
考研英语作文原创模板【二】
从前,有两个人一起外出,走的时候,一个人忘了关门,另一个人把门紧锁着,等回来时,锁门的人发现家里东西被盗了,另一个人家里却安然无恙,两人十分的不解,于是商量下次出门时把门都开着,结果强盗来了,看到门都开着,吓得满头大汗,转身就跑。
这个故事是说做坏事的人心虚。
考研英语作文原创模板【三】
从前,有个人中了箭伤,找来一个医生给他治病,医生找到伤处后,从药箱里拿出一把剪刀,将露在外面的箭弄断后,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那……里面的……箭……”那人颤抖着问道。
“我是外科医生,只负责皮外的事……”医生边说边往外走。
考研英语作文原创模板【四】
森林里,大大小小、食肉的、食草的动物们生活在一起,各自都有各自的觅食本领,都在一块儿成长长大。一只狐狸在生活之余,感觉闲着无聊,便自愿做了教书先生,每天傍晚时分,在湖畔一棵大树下教森林里的蟋蟀、蚂蚱、蛐蛐等昆虫以及乌龟、蜥蜴等爬行动物们识字、算术,讲故事。因为讲得好,树上的喜鹊、百灵、黄鹂等鸟儿们也不时来听狐狸讲故事。学习结束后,在明亮的'月光下,他们围着狐狸,有的弹琴,有的唱歌,有的跳舞,表示对狐狸的感谢。狐狸的心里很有成就感、自豪感。尤其是当它看到路过的狼一副孤独、落寞的样子时,狐狸的心里更是美滋滋的。
有一天,狐狸对它的学生们说:"同学们,别看老虎、狮子号称是‘森林之王’,我只是一位自由的森林活动家,不过我是‘无冕之王’,什么狼狗马鹿,见了我都会害怕而逃;我要是抖起威风,大熊二豹见了我也得打哆嗦。只不过平时我不愿意出手罢了。每天轻松地抓几只小兔、鸡鸭填饱肚皮就行了。吃饱了,给你们上好课、你们高兴才是我最看重的,是我生命的最大价值体现。"小动物们听了很是感动。有的自觉充当了狐狸的信息员,将探知道的鸡鸭、鼠兔的居所、行踪及时告诉狐狸,帮助狐狸觅食。狐狸告诉小动物们:"三日后,我给你们露一露,展示展示。到时候,就连虎王也会亲眼目睹、见证我的威风和风采。"
三天后,狐狸以邀请老虎检阅它教学成效的名义行走森林。一路上,森林里的动物们看到狐狸身后的老虎,纷纷四下逃散。小动物学生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惊呆了,惊呆之后是满满的崇拜。这件事成为森林界的著名热点事件,记者鹦鹉连发报道,动物们也口口相传,一些动物也从此对狐狸刮目相看。事件传至人类界,人类将其称为"狐假虎威",评价道:倚仗别人的权势欺压、恐吓人,算不得英雄。
考研英语作文原创模板【五】
从前,有一个叫司原氏的人在一次夜间打猎时,发现了一只鹿。这只鹿听到野地里传来的声音,突然警觉起来。当它看到司原氏正拉弓搭箭瞄准自己的时候,撒腿就朝东面方向跑了。司原氏并不气馁,他知道在大黑天鹿跑不快,于是跟在后面紧紧追赶,并且一边追赶一边大声地喊叫,试图以此把鹿吓懵。
正在这时,西面来了一伙追赶猪的人。他们听到司原氏的喊声,以为是东面有人在堵截这头猪,于是就跟着喊叫起来。司原氏不知那伙人在喊叫什么。他看到那边喊叫的人很多,心想必定也是在追赶猎物,于是他放弃了自己追赶的鹿,朝众人喊叫的方向跑去,并且在半路上找了个地方隐蔽起来。那伙人叫着喊着从司原氏隐蔽的地方跑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司原氏竟然发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一头浑身白色、肥肥胖胖的笨兽。他十分兴奋,以为自己得到了一头吉祥的珍贵动物。司原氏扑上前去把它捉住,然后带着这吉祥的野兽回了家。
司原氏拿出家中所有精、粗食料来喂养这头珍贵的兽。这头兽也十分亲近司原氏。它一见到司原氏便摇头摆尾,朝司原氏发出可爱的"哼哼"声,因此司原氏越发喜爱它了。
没过几天,刮起了狂风,下起了暴雨。暴雨淋在这头白兽身上,将附着在它身上的白色泥土全都冲刷掉了。司原氏仔细一看,才发现它原来竟是自己家里丢失的老公猪,而今却被司原氏当作宝贝从外面带回了家里。
遇事不动脑筋,司原氏在追猪人的喊叫声中随声附和,放弃了追鹿,结果一无所获。因此,大凡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的人,追求到手的往往不是真理。
考研英语作文原创模板【六】
老屋有思想,知道进出的门紧锁。偶尔树的枝叶把房顶抚摸,清月的愁思凉着四季,半堵墙的豁豁里,几只猫翻出翻进,自由的畅通无阻。蒿草几乎要越过院墙,一棵杏树偷出在水泥没有打面的院落的空地上,肆无忌惮的张扬,炫耀着自己的能耐。几只麻雀,偶尔站在杏树枝头,活跃了一地的鸟粪。
父亲比老屋先老,父亲走了,老屋还在。风风雨雨里,老屋虫蛀的门窗,仿佛父亲脱落的牙齿,嚼不动一天又一天坚硬的日子。是父亲把老屋的欢笑带进了泥土,可是,老屋支撑着不能再弯的腰,千疮百孔的站立在大山里,烟熏火燎里似乎还有洋芋蛋的味道。
老屋是黄土打的墙,家在黄土高原的人,对于“打墙”都不陌生,黄土墙围起来,那就是咱的家。墙里墙外,家长里短,都是满满家乡的记忆……
一层一层垒起来的土墙,有的经历千百年风雨依然挺立,它是老屋的主人的主人,勤劳和智慧的产物,是祖先艰苦奋斗的遗迹,也是我们不能忘却的瑰宝。
打墙在人们生活中是一件有关安居的大事,过去的房子多为土木结构,墙是用黄土打起来的。打墙既是个技术活儿,又是力气活儿。
打土墙所需工具一般有:两个比碗口还粗的木夹杆,一个墙头堵梯、八根一模一样的松木椽,石墩子(柱子)四五个,木榔头两三个、绳子若干条。
打墙一般七八个人,有“七紧八慢九消停”之说。墙上一人叫土,绞路一人指挥,其他人挥铁锨,将干湿适度的备土撂往墙上。不要脏土,脏土粘结性差。土太干打不实,垒不起来,土太湿硬度又差,打好的墙容易塌下来。土中加水多少全凭经验。墙上叫土者就是现场指挥。他手中的镢头既是指挥棒又是工具。
土撂够后,人们放下铁锨,马上换杵子上墙打墙。低板通常六人,中板四人,高板二人。墙上地方有限,打墙人提杵子必须两肘夹紧,否则就会影响他人。打墙人还要像打球换场一样,两头换着打,以防用力不均衡造成倒墙。为步调一致,每打一下,都要高声齐喊:“嗨!”这样既叫齐了动作,又赶走了疲劳。
墙根子有三尺宽的,二尺八的,还有二尺六二尺四的,视墙高低而定,越高根子越宽。不管墙高低,墙头都是一尺宽,上窄下宽才容易站稳。打完最后一板,就要收稍子。这时墙高了,土不易上去。劲大了会撂过墙,劲小了又上不去,讲究要“蛤蟆亮脊背”。就是土离锨后,飞上空中翻个过儿,稳稳落在墙头而土不散。这可是一件只有少数人能***技术活儿。此时杵子不能使猛劲,还要斜着落在土上。打好后再把墙头铲成光滑的鱼脊梁型,以利雨水落下。这一套活路全由墙上叫土者一人完成。
一班子人打墙,还是十分热闹的,边干活边谝闲传,说笑话,干累了就歇,抽根烟,喝口水,再接着干。晌午饭时,主人来叫吃饭饭,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拉家常。吃饱了,也歇好了,接着干活。
老屋显示着远去的背影,也就是山村里的一代又一代人,在土墙里修建着自己的土建筑。现在的土屋,荒凉、孤寂,杂草丛生,不时从里面跳出成群的`地老鼠、野鸡。隐隐的蛤蟆声,还有不知名的昆虫,一个劲地喊叫着,为这个土屋老院增添了一种凄凉。
无论生活多么窘迫,土墙的老屋里曾经有过温馨。而这些回忆,只属于农村人,自幼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不会体验过。那是精神上的财富,也代表着勤劳朴实的智慧。
老屋里的墙面上,还贴满我儿子在小学的奖状,这里也是我结婚时的新房。一家几代人生活的地方,在苍老里有过欣喜,更有过欢乐,还有过悲伤和忧愁,盛不下所有的情和爱,老屋里的人各奔西东。
山旮旯里的这个地方,当我用沉重的脚步从远方一步步靠近,那种温暖的气息越来越重,那种熟悉的味道越来越重,那种亲切的感觉越来越重。
从我记事起,土墙围住的老屋里,是泥的墙皮,墙壁已经斑驳,可以看见裸露的土坷垃,房顶的柳木橼,七扭八歪,晚上依稀可以漏下星光点点。屋里有一面坐西朝东的土炕,炕墙上有一个四根榆木见方的小窗子,大人的头也能钻出去。在土炕的旁边有一个只抹了泥皮的土台,是用来放被子闲衣服的,土台上有一个木箱子,这是母亲锁馍馍的地方,姊妹弟兄多,只有分着吃。地下还有一个柜子,是家里装粮食的地方,也算是家里唯一的家具。
那时的炕上,只有一片竹席,有几个地方烧的发黄。入冬,母亲总会用山里铲来的草皮烧炕,炕上温热着一家人的身体。不过温度有时不稳定,有时炕煨的太满,只有屁股底下热,脚底不见热,炕里的灰掏空了,母亲把炕煨的太后,脚底热屁股底下凉,早上起来,屁股上印满竹席的痕迹。
那时一种叫壁虱的东西横行,白天钻到裸露的土坷垃里,一到黑夜吹灯,肆无忌惮的叮咬人,它的叮咬有一种发热的感觉。当你点亮煤油灯,壁虱总是列队而来,好在它们的速度缓慢,父亲就用鞋底在满墙乱抹,抹着壁虱的皮壳炕的边边角角都是,看着壁虱抛尸,没有了那种烧痛,而是被胜利的感觉所代替。
屋子里的老鼠也不是好东西,虽然不咬人,为了偷吃地下柜子里的粮食,在盗窃时吱吱作响,苦了一天的父亲不管母亲的抱怨,只是闷头大睡,就是不肯起身和老鼠一搏。后来,母亲发明了捉老鼠的办法,用纳鞋底的锥把碗边支起,在锥子上扎上杏仁或者馍馍,当老鼠钻进碗里拨动锥子,碗就会把它盖住,这时父亲急忙起身,转动碗边,直到老鼠的尾巴出现,父亲就会抓住尾巴,掀过碗,用摔跘的极刑让老鼠呜呼哀哉。
老屋是我的守望,它和母亲一样,是我心中的至亲。站在老屋的院子里,月夜,如水的月光照着眼前的残痕断臂,我在杂乱的蒿草边,独自拾取留在这里的每一个记忆的碎片:西边的土屋里,土炕依在,应该是母亲煨得暖暖的那座土炕了,我好像和母亲在一起,看母亲纳鞋底,听母亲讲故事;北面的厨房里,被柴烟熏黑的潮湿里,有一种尘封的岁月,我又一次看到母亲从墙角的缸里取出舍不得吃的白面,在锅里烙成了饼子,塞进兄弟姊妹上学的书包里。
山村,老屋,我无法释怀的眷恋,有我的童年,有我的成长。那被熏黑的屋檐,被风雨浸湿得残缺不齐的黄土墙,老屋顶上恍惚飘来的炊烟……似乎,一声长唤,从老屋门前飘来,是母亲又在呼唤我的乳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