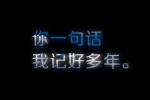人民日报高考议论文满分作文【一】
丹麦有这样一句话广为流传,“就算我们失去一切,我们仍有一个安徒生。”虽然安徒生已长眠地下,但他创造的伟大的孩提王国连同他的精神一起永不坍塌。也正是这个王国,让所有孩子沉浸在欢乐的海洋,甚至那些大人,也不必再戴上严肃的面具,像个孩子一样,获得清凉的慰藉。虽然我们不在丹麦,但却可以分享他们的信仰,唤醒心中的安徒生。
大人与小孩究竟相隔多远?或许只有一粒尘埃,而那尘埃之中却容纳了万水千山。随着孩子的长大,懵懂的褪去,必然要接触许多的教条,也正是这些教条压抑了个性,如一条条无形的枷锁,镣铐了曾经的梦,封闭了心中的安徒生。所有的好奇、幻想都被斥责为幼稚,所有的坚守都被理解为固执,大人已经失去了单纯的童真,难道要把孩子唯一的乐趣也扼***了吗?
现实总是那么残酷,生活也并非总是那么美好,大人为孩子做的事或许并非不能谅解,但沉闷的社会,缺少了童真,孩子般的心态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呢?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思考,大人就是迷路的“孩子”,在前方的道路上迷茫、孤单地行走着,但实际上他们与如今本质意义上的“孩子”只隔了一道门,这道门无论历经多少沧桑,也愿意为那些迷路的“孩子”敞开,帮助他们唤醒心中永恒的安徒生。
其实生活需要的就是这些“孩子”,他们乐观顽强,从不颓唐,更不会沮丧,那些社会上漂浮着的虚假、背叛与勾心斗角也从来不舍得伤害他们。我不禁想到了圣埃克苏佩里,这个被世界宠爱着的孩子,不喜欢大大家眼中充斥的利益,更害怕有朝一日会变成他们,于是和小王子一起离开,追求生命的意义。他,唤醒了心中的安徒生,像个孩子一样幸福地过着,最科留给大家的,是无限的遐想与向往。
孩子,就是这个世界现形的天使,肩负着净化大家心灵的伟大使命。他让我思考:人世匆匆,为什么总是在奔跑?朋友在前,为什么脸上挂着的意是虚假?为什么就不可以撕去伪装的面具,洋溢笑容地面对生活?
丰子恺曾说过:孩子的眼光是直的,不会转弯,孩子是单纯的,从不会虚情假意,故作姿态,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变成孩子,只要你愿意唤起心中的安徒生。
人民日报高考议论文满分作文【二】
生活不是一场戏,它确定不了生命的尽头是完美还是缺憾。生活往往就是如此,没有片头和片尾,有的只是那些情絮飘零的日子,那些——随波逐去的年华。
小浪花就像连绵不断的雨,经久不息,不曾断绝。生活不是静止不动的站台,而是长鸣而去的列车。如果把生活比作天堂,这天堂里却没有阳光;如果把生活比作地狱,生活却还不至于如此绝望。时间就像被撒旦的魔杖一带而过,回首往事。才发现——流动奔涌的才是生活。
有些人匆匆地走了,留下的只是秋季里一个灰蒙蒙的背影。汽笛响了,列车开了,站台上凄凄凉凉,只剩下离别的悲伤。徐志摩说:“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淡淡的悲伤,淡淡的愁,我才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有那些——情绪飘零的日子。
情绪飘零的日子,天,是灰色的。漂洒着点点滴滴的忧伤。每个人都有失意的日子,但生活还是继续着。所以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告诉自己:“没有离别的忧伤,又怎会有重逢的喜悦。”轻轻的把一片落叶拾起,轻轻地不留下一丝叹息。每个人都会有那个——心灵中的天堂。
最真实的东西,往往离生活最近;最美丽的东西,往往离自然最近;最想要的东西,往往离梦想最近;而最朴实的东西,却只记在孩子的心里。无奈是生活的必需品。每个人面对无奈时,都会做出无奈的选择。有些人他选择了坠落。在人世沉浮中,他们将纯真如泥沙般埋入心灵的湖底,在人生的旅途中,他们将自私装进了那即将带走的行囊。可我总相信这个世界告诉我,昏暗的天地中总有一放净土,一片碧海蓝天,不信——你听,泪滴的声音。
听到心跳的声音,你感觉到生命的存在;而听到泪滴落的声音,天使说,那里心灵最紧处的震撼,可悲的人没有任何情感而言。天使说,那就是他们生命的——尾声。
生活不是一场戏,生活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生活既像一首诗,又像一首歌,它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放飞的风筝离开那条线就不会飞得太久;生活走出那个圈却走不到尽头。牵着你还是那条线,围绕的还是那个圈,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那就让我们幸福的期待,期待着幸福生活的来临吧!
人民日报高考议论文满分作文【三】
古语云:“易有三训,一训简易,二训变易,三训不易”,“易与天地准”,之于常识,不也是如此吗?我们生活在常识中,“春暖花开”、“秋高气爽”,我们不假思索地运用它们,是为简易;同一事物不同时刻有不同的表现,变化无穷,是为变易;常识由生活而来,经久适用,是为不易。故庄子云:“道在便溺”。因常识,于生活,我们泰然。
老子云:“大象若希”。正是由于常识之于我们太过习惯了,时常,我们会无所察觉,如同时空之于我们过于静止与绝对,在爱氏之前,我们被蒙骗了千万年。于是我们在恍然后明白,常识虽常,但亦要知之、行之、思之。
所谓的对常识的知之,并非仅仅为热则却衣寒则添衣的自然反射,而是对自然存在的用心观察。没有这用心,何来常识?没有常识,何以行之?不得而行之,必遭祸患。譬如之于人,了解交通拥挤之时间,于约会便不会误时;又譬如拿破仑不知俄国之地广与冬天之寒冷,便因俄国坚壁清野而为滑铁卢之役埋下伏笔。
人民日报高考议论文满分作文【四】
守望遥远 我们的天堂 月是古人的家乡,是知己的思念。那种遥远到无可触及的神圣光晕,幻化成诗人笔下的魂灵,口中的吟咏。东坡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阿姆斯特朗带走了人们的月。那个印在沙丘灰尘上的脚印,让李太白的月下独酌成为历史,或许人类已经摆脱了几何时的愚昧,距离已经不是往日那般遥远,然而那枚挂在苍穹灼灼发光的玉盘已经褪色,是古人的距离,生出那枚曾经的月亮弯弯。
我是那样讨厌近距离,近在咫尺的梦想,我不要。当在酷暑里挥汗如雨时,梦幻中的象牙塔是我惟一的支点。我想象它的宏伟宛若天堂。尽管每个人都会有现实的一面,然而我坚信遥远生距离,距离生美。无可企及构出理想的神圣。张开五指,刺眼的光折射出天堂的模样,我独自守望。理想是宝石一般的晶莹透亮。遥远观望,它是我的天堂。我喜欢失真的美,就像古人的月亮。
无意中想起了海子,那个传说中始终愤世嫉俗的诗人。当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成为希腊神话一般的虚幻时,海子无言了。在他的眼睛里,整个世界,远看是伊甸
园盛开的美丽花朵,近看才知这个世界给他的失望。大海留不住他,春天也留不住他,诗歌的翅膀折断了,只剩下山海关的铁轮
隆隆而过,海子的灵魂伴随伸向远方的铁轨通向了天堂。有人问,到底是什么伤了他,伤了这个时代的诗人,人们也许不明白,因为自己置身这个世界,未曾远观它的美好。文人与世俗的距离永远太大,反差太大。在海子焚烧诗集的熊熊火焰里,盛开了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世界。这距离是悲剧,是文学女神的眼神。远望与近观的世界让海子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完成了本质上的蜕变。我想,仍然坚持远观世俗的海子永远幸福。
这就是距离的美感。永远置身在纷乱的世界,这让人类开始麻木,甚至开始淡忘远观时那种令人窒息的美感。当努力构建所谓的“美丽人生”时,人类是否忘记了那份遥远的守望,忘记了儿时曾经的天堂,忘记了古诗中月亮的眼泪,忘记了希腊神话里挥着翅膀的安琪儿?科学的发展放松了人类最后的一根敏锐的神经,一切诗意消失殆尽,只剩下世俗世界的繁华汩汩流淌。
看看天边的月,看看风流千古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守望那份曾经有着“蛮荒文明”年代属于人文精神的真实,看遥远带给我们的令人窒息的美,诗歌、散文、楚辞会滋润这个时代的麻木,遥远的美好让我们重新点燃希望的神话,精神之船重新起航。
守望遥远,守望天边只属于我们的永恒……
人民日报高考议论文满分作文【五】
理性与浪漫常作为两种基本的打量世界的方法论,充当我们价值观的梁木,支起人生的苍穹。
理性的求真与思辨本就是人之本性,无论是对浩瀚星辰、物理准则的追问,还是对人作为个体应处之位置的拷问,都是理性在人的精神中闪耀的凭证。无理性,十八世纪的启蒙家们无法为欧洲解除封建王权的束缚;无理性,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无法建造如此伟大的科学王国。可信的是,由人猿进化到当代,理性始终是人扎根的土壤。
而浪漫的\'审美与诗意则更关注人的情感,行事处世适心随意,最终“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熊培云“在时间的溪水边垂钓”,周国平“煮豆撒盐”的恬然淡泊,和东坡“朝嬉黄泥之白云,暮宿雪堂之青烟”,未尝不是中国士大夫对浪漫二字最生动的注脚。浪漫大抵可为川端康成所倾心的生命的海棠,于无声处沁香。
诸如以上,二者立场看似对立,实则不然。便是如濠水之畔的那场传世辩论,惠施的理性逻辑,与庄生的人情宇亩,又何必分个高下,争个胜负?
理性不是美杜莎的眼睛,流云与霓虹不会因其存在而石化僵化;浪漫亦不是伊甸园的蛇,破坏世间的规则与秩序。恰恰相反,无理性,浪漫成为“驰于虚声、骛于空想”的不切实际;无浪漫,理性成为一板一眼、功利至上的不合时宜。因而最理想的方法论是糅此二者合一——于理性土壤之上,海棠花开!
卢梭想必是极有发言权的,他在推崇政治理性的同时,也重视生于浪漫的宽容与和谐。若说庄子不重理性只重浪漫,似乎也有失偏颇,其对“逍遥”的拷问与沉思不也绽放着理性的沉静的光辉。爱因斯坦在物理理性上的造诣可以说无人能及,但其秉持着一颗浪漫且搏爱的心,以实际行为述说人性的尚尚与和平的辉芒。
世界并不是偏狭的,它容许和谐与包容,为理性与浪漫都预留各自的位置。这也并不是二者必择其一的抉择,而是如何将其统一贯彻的思考。
或许我们只需在纸上写下一个函数,再仰首望一轮明月。在理性的土壤上耕耘,静待海棠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