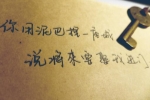我也想上领奖台作文500字【一】
大人口中的任性,是孩子对世界的探索。可是,无人知晓……只有孩子彼此,互相安慰、互相转告。我不明白,曾经,身为小孩的大人,为何不懂?
面对生活压力,孩子们渐渐变成了“唯我独尊”的大人。所谓大人,我对他们的理解,其实就是格式化的\'小孩。他们有着孩子的成熟外表,却再也没了孩子幼小的心灵。读过我写的,“一只橘子”的人都知道,孩子,是青涩美味的小橘子;而大人,则是外表美味、里面酸涩的橘子。孩子格式化,就变成了人性化的机器人。若大人就是没有童真的机器,孩子们还会想成为大人吗?一定不会了。
所以,我想任性,想要永远成为本真的我。可大人总那么霸道,不允许我们偏离预期轨道一点点。殊不知,任性,只是一种保持、只是一种童真的表现。大人眼中的世界,和我们差的太远了。
坚强了那么久,我也已经承受不了了。请你们继续听我说最后一件事:你发现,你最近爱哭了。别惊讶,只是因为你无法再坚强下去。没关系,任性一下吧,回归本与真。这不可怕。
我真想再任性一次。
我也想上领奖台作文500字【二】
是啊,怪谁呢,只能怪自己怕吃苦,每次提起笔还没这几个字,心就操到了别的地方,学习上不去,妈妈老师的教导经常在耳边响起,有时是有那么些不甘心,但是一拼搏起来却发现好难,于是便徘徊开来。
然后有一天,我刚画好了一幅画,画画是我所感兴趣的,哥哥进来了,拿起画看了看说:“很不错嘛,小妹挺有天赋的,谁教你的呀?” 我笑了笑:“没人教啊,自己比着书上画的\'。”哥哥摇了摇头说:“我不信,你肯定学过画画,不然肯定画不这么好。”我说:“没,真没拜过师,就是随手画的。”哥哥把画放下了,看着我认真的说:“小妹,你挺有天分的,但你好像不当回事,你看吧,你老是做些你并不擅长的东西,你擅长的你却并不在意,就算你有特长的地方,”
我也想上领奖台作文500字【三】
一边看电影,一边吃零食;通宵上网,看电视;在课堂上忽然想起好笑的事情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翘课出去玩……这些几近疯狂的念头,似乎只会出现在电影或漫画里,我是多么渴望尝试一下。可是,人的一生,都被束缚着,根本容不得我放纵一下自己。于是,这种念头产生时,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不能这么做,我告诉自己。这些念头,便只能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做好学生有点累。上课时,托起下巴沉思者有之,讲小话传纸条者有之,坐在位子上两眼呆滞无所事事者更有之。而我,上课听讲者也!我也想传纸条,也想走神,但我是好学生,如果被老师发现,自己觉得很丢人,老师也会很失望,所以我不得不克制自己。当我的思想飘出窗外时,我便尽力把它拉回来,关在我的脑子里。考试时我也想交白卷,作业我想不做,可接下来是什么后果,我也一清二楚。当差生没写作业时,我承认我会有点幸灾乐祸,但更多的是可怜与羡慕。他们可以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已经习惯了。我的内心则不堪一击,考试一次考差了,作业忘交了,被老师骂了,我急得都快哭了,能让我情绪低落好几天了。
新闻报道常常说,xxx 市又有人自***了,而且大部分是学生,学生中又有大部分是高材生,高材生中又有大部分是考试没考好。或许人们会觉得很荒唐,不可理喻——活着多好,干吗非寻死不可呢?可是,没经历过的人不明白,他们外强中干。人们都只看到好生光彩一面,又是拿奖,又是状元的;而背后的付出,人们都知道,但依然只看到好的一面。俗话说,勤奋出天才,为了一次考试,我不得不扔下我手中的小说、漫画,去看作文书、散文集。平时大家在上网,我却在做习题。当我跟朋友诉说时,他们的却一脸惊讶:“你会看漫画?我才不信呢!”我无话可说了。我也是人啊!我就这么像整天只会学习的人么?我只不过是多付出一点罢了。
在家里,母亲也会对我很好,但她有时也会骂我,拿我跟姐姐比,我也无法反驳。小时候,我曾问过,像牛顿、郑渊洁、爱迪生,都是小学功课门门不及格的,还被缀学,为什么我还学习呢?母亲便会叹一口气,现在不一样了,你就凭个小学文凭,谁会要你呢?
有时候,我真的很想放纵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人生来便被束缚:小时候被家长束缚,上学了被作业束缚,长大了被法律束缚,年老了被时间束缚……
我也想上领奖台作文500字【四】
而她抱着这世间所有母亲都有的深深盼望和希望看着我,用双手怀抱住我,露出了一个微笑看着我。
就是这一眼,敲定了我们一生的羁绊。
也是这一眼,注定了一辈子需要不断的拥抱,不断的互相伤害,不断的哭泣,不断的深爱。让我甘心烫痛,都不想放手。
在这么多年的时光中,原谅我总是无法提笔去描述我的母亲。这位在我的狭隘人生中给予了生息,希望以及绝望的母亲。于我而言此生,她是我的光芒,我的门锁,我的生命和情感的来源。
其实时至今日我依旧不能将我对她的感情如流水般倾泄,因为一切太过庞大,太过的沉重,也因为她是我的珍藏于心。
她,就像是一首歌,唱尽了我的人生,我的爱。
有些时候,令人感到致命的伤害并非是他人给予的肉体疼痛。而是他一举击垮你的精神支柱,你信仰的上帝。我在看《沉默之丘》这部影片时,只记得女主角对另一个母亲说:“母亲是孩子眼中的上帝。”如果说父亲是我追逐的`光明,那么母亲就是我的上帝。无论她是怜悯还是无情,我都永远以她为我生存的尺码,为我生命的衡量。
照片中母亲有及肩稍长的长发,小巧的嘴巴,圆嘟嘟的脸蛋,高挺的鼻梁,黑裙白衣。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显得干净而温暖,又如毛绒一般厚实令人安稳而眠。哦,那时的母亲真的好美。
然而这些,终究最后被现实磨去了。
如今她是一个十足的家庭妇女,每天在女儿和丈夫之间操劳,年轻的美貌也经过岁月的洗刷变成人们口中说的黄脸太婆,本来秀丽的黑发如今也参杂着丝丝白发。心疼她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只好放在心里默默感伤
再一次回家的路上她搂着我的腰说:“你的腰还挺细的。”
我说:“是吗?”
她又替我理了理帽子,然后把头靠在在我右肩上说:“你不觉得你和父亲在一起生活奋斗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吗?”
我张了张嘴说:“挺好的感觉。”
然后她没在说话。
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她又对我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整天都不笑,板着一张脸,好像我们都欠你一样,你为什么对家里人好像对外人一样,不和我们说话也不去玩。你有什么压力啊,你只需要现在帮我好好做事听话,好好读书就可以。有吃就吃,有睡就睡,有事做事就可以了,你还天天这样干什么?自寻烦恼累不累。”
我一路静静听着她说,不时点点头表示我在听。
回到家后,爸爸正在等着我们回来吃饭,桌上洗好的水果摆着,她又转过头对我说:“你看看,这才是家,这才是温暖。”我点点头,没说话。
那时我嫌她啰嗦,如今远在他乡没人在旁边没完没了的说话,突然感觉身边空荡荡的,有时发呆的时候就会看到她就那眉飞色舞的和我讲话,觉得很好笑,又很想念。
其实每次回家我多想抱抱她,对她轻轻的说:“妈,我好想你啊。”多想在她难过的时候抱抱她说:“妈,别怕你还有我。”
可是天生那么傲慢的我却不肯主动伸手去拥抱她,哪怕说说安慰她的话。
我现在还很年轻,短短十七岁。比朝阳探出的光辉还要更为年轻,可正是在这充满未知的青春中,我唯一依靠的只有父母。
我最大的愿望,不是美满的爱情,生死相许的友情,而是一个平凡的家,父母健康,子妹和谐,虽贫犹福。
我也想上领奖台作文500字【五】
有时我也想隐去。隐去,既可得到人们毕生追求的某些事物:逍遥、快活、无忧无虑。可以与尘世隔绝,忘却一切,忘却所有痛苦,没有哀伤,没有后顾之忧,做一个在世上“不曾存在过”的人,在深林之中,在摇曳的竹林之中,整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有时,我也想隐去。游历于名山大川之间,使心灵与大地共存,去寻找那个人类追求不到的事物,最终快乐地在一间平凡的小茅屋中死去,安祥、宁静。没有人在我身边哭泣,没有人在我身后留骂名,没有人为了争夺我身后的物品而鱼死网破,没有人为了我而受到伤害。
有时,我也想隐去。冲破那一层尘世间虚伪的“面纱”,无虑地指出任何人的.成败。任何人都与我无关,我只是随性而为,享受着世界的每一分芳香,笑看人间风云。即使被人说成“怪人”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样生活的美好。“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有时,我也想隐去,用自己的感觉去触碰人世间中一切的一切,用自己手中的那一枝笔,随性地用方块字谱画出一张又一张美丽的画卷。整日都挂着一张发自心底的笑脸,毫无愁思,毫无酸楚。
有时,我也想隐去。也许有人会说,你不可能冲破尘世的“面纱”。尘世的“面纱”实际上算什么!只要我的思想已经穿过了它,那它就早已子虚乌有了!
我也想上领奖台作文500字【六】
知了声嘶力竭地喊着夏天来了,我们依旧在课堂里挥汗如雨。夏日的热情吸引了正在与课本苦斗的我,老师的声音渐渐远去,我不由自主地想……
期待着猛然能有一个晴空霹雳,让瓢泼大雨瞬时撕开晴空虚伪的面具,猛烈冲刷燥热的大地。趁着这个机会,我将兴致勃勃地跑出课堂,去感受一个“野孩子”肆无忌惮的快意。
我想奔出校门,像上学要迟到一样的疯狂奔跑,甚至脱掉鞋子,让赤脚踏出水花打到我的脸上。大雨滂沱,电闪雷鸣,可我一点儿都不害怕。我纵情地欢笑,此时的我,不在意是否优雅和得体。
我还想卷起裤腿,沿着屋檐慢慢地走,静静地聆听着雨滴齐奏。和我一起在屋檐下的是一只小鸟,它仔细地梳理着美丽的羽毛,似乎准备在天晴之后展示它更美的服装。
我还想去看学校隔壁宠物店的鬃毛狗。它懒洋洋地趴在那里看着雨里的荷塘。那幽怨的眼神,那静默的态度,难道它也懂得“留得残荷听雨声”中的美丽?
我还想插上翅膀飞上云端,去看勤劳的仙女,她们正在纺织着天地间最美的画卷,她们自由而欢乐。仙女们邀请我和她们一起生活,放出美丽的丝线缠绕住我,我大喊着:“我还要去上课!”
醒醒啦,老师叫你了,同桌拼命摇晃我的胳膊。啊,我还在课堂上,我伸了个长长的懒腰,告诉自己,任思绪驰骋飞扬吧,终会有一双自由飞翔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