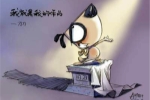红薯岭作文最后自然段【一】
小时候,家里经济不是特别好,母亲也总是勤俭节约,省吃俭用。她很喜欢吃摆在路摊上的红薯。每次小贩吆喝经过时她总是会时不时的暼几眼,再深呼吸,然后漏出满足而又欣慰的笑容。
那是一个冬天,母亲像平常一样接我回家,也像往常一样暼一眼红薯摊。
妈,呐,我也好想吃!我指着红薯摊,撒娇的看着母亲,其实我并没有奢望母亲会给我买。
母亲摸摸口袋,豪爽的说走,我们去买!
我惊讶的看着母亲,平时自己省吃俭用都舍不得买,今天却如此大方!
她凑过去,掏出口袋的钱,骄傲的对着小贩说来!给我来个大的'!我给我奴吃!
拿过红薯,她立刻递给我,笑呵呵的说来!这红薯热乎着呢,还很甜,快吃快吃!
妈,我们一人一半吧。
不不不,我又不饿,你自己吃。
你不吃那我也不吃了。
傻孩子,好吧好吧,我们一人一半。
她小心的掰开红薯,露出了红薯特有的嫩红,明显她分给自己的只有三分之一,但她却笑得那么满足。
我一口一口慢慢品着,品着这甜蜜的母爱。
红薯岭作文最后自然段【二】
下午四点我们准时出发,走了大约十几分钟,到达目的地。我们一齐动手,挖了一个蓝球大的坑,已经是满身大汗,也顾不上那么多,忙着找泥土,倒水,和泥巴,最后把和成的泥巴裹在红薯的外衣上,就可以防止红薯的皮儿烧糊,前面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下一步就是烧,我们分头行动,四处寻找干柴,不一会儿,就有一大堆干柴。阿姨拿出打火机,啪的一声,干柴逢烈火,熊熊的`大火迅速燃烧起来。稍不留神烟呛的我们值咳嗽,熏得两眼难睁泪汪汪,但热情干劲依然不减当初。
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忍不住了,趁阿姨去找干柴的功夫,我们悄悄的把火扑灭,把红薯扒出来,想看看烤熟没有。这时,我们扒出来一个东西:“呀,这是什么呀?”怎么是黑棕色的,我用手摸摸,温温的,硬硬的……“啊!这是红薯!怎么变色啦!”原来湿泥经火烧熏,已经严重变色。啊!阿姨就要回来了,我们又赶紧把红薯扔进土堆里,点上火,继续烧火,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阿姨抱着一大抱树枝树叶过来了。我们找出来几片大的树叶在一旁扇风,一边和阿姨说笑。一会儿我们又忍不住了,求着阿姨让我们看看,最关心的问题:“红薯烤熟了没有?”阿姨受不了我们的死缠烂磨,终于答应了。又把红薯扒出来。这次外面裹着的泥已经变成深黑色的了,刚拿出来,有一些碎末渣落下来,我摸摸,挨着地的那一面是凉的,而被火烧着的地方有些软,好烫。我们把它翻了个个,又开始烧起来。
可真是个漫长的等待,大约过了四十多分钟。阿姨说,红薯可能烤好了,我们便火速把火熄灭,用树枝把灰尘挑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糊黑糊黑一个圆疙瘩,我伸长脖子仔细端详:红薯的“外衣”已经变成黑灰色的了!赶紧抓起来,哇!太烫了,不得不扔掉。过了一会儿,我才把红薯捡起来,拨开皮,一阵阵甜甜的浓浓的香味儿扑鼻而来.我们像饿狼一样,吃的津津有味。 真香啊!自己做的东西就是好吃!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半年啦,但我一想起来脸上就会路出丝丝笑容,心底就会有无限的想往。真的好希望还有下一次机会!
红薯岭作文最后自然段【三】
记得上世纪四十年代时,居住在辽宁南部靠山傍水的我们一家,虽地质不错,但土里刨食,人多地少,年年总是寅吃卯粮。特别到了收红薯时,不等秋收就提前充饥了。
红薯身上全是宝,叶与茎洗净撒上盐当做咸菜吃。长得匀称一点的红薯留作来年做种子。看不上眼的切片晒干,加工红薯面。特别小的红薯煮熟和在玉米面里蒸窝头吃。另外红薯粉可烧汤轧粉条作宽粉,又当主食又是好副食。那个年代每当红薯熟时,家家妇女带上孩子,把整个红薯地翻了又翻。谁能找到被锹镐刨伤了的红薯谁高兴,但最幸运的是找到被主家遗漏在土里的稍大块的红薯。不管怎样,只要你肯出力气,多刨点土,一天总会找上一小筐红薯。我在家排行最小,哥姐们各自都有另外的活儿,唯独我一人跟着母亲干这些无望中寻找希望的事。那时候的`农家,前大半夜熟睡,后半夜饿醒了,光凭喝凉水只能顶一阵儿。有天一大早,我起来方便时,听父母在悄悄地说有两块红薯地的主家明天要收红薯,让小虎子(我的乳名)多跑两趟,一旦有了确切消息咱起个早去找。
此后就觉得天过得很慢,盼了日落盼日出。终于和我爸关系不错的放羊二叔告诉了那家人要收红薯的消息。第三天一大早,父母把我从被窝里叫醒。我和妈妈每人手拎一个筐,天还黑黑的就下地了。满以为我们是捷足先登,哪知道那里早就有人了。我和妈妈择一块靠边的地刨起来。别看妈妈是女人,一会儿就找了大大小小足有半筐底的红薯,望着红鲜鲜的属于我家的红薯,恨不得搓巴搓巴先吃几口。妈妈看我盯住她的筐,急忙训斥我。我刨着刨着,一条足有半斤多的大红薯被我的齿耙搂住。太遗憾了,因为我伤了它。尽管这样,我的信心更足了,早忘却肚里饿了,一个劲儿地刨。这时早来的人有的已经回家了,有的还在刨二遍三遍。
还别说,就那年最困难,就那年吃饭成问题,就因为有红薯可找,全家人只有弟弟因蛔虫病死了以外,其余人个个都挺过来了。
而今我看到一车车红薯,望望父母亲的坟的方向,心里难受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