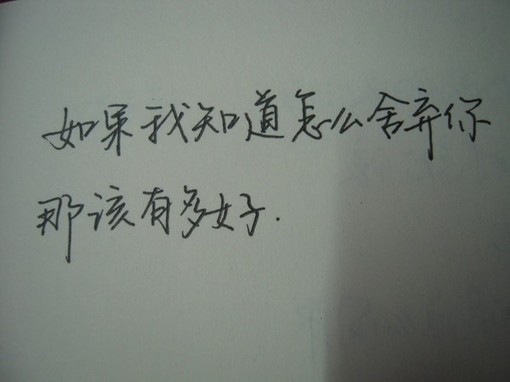
朱子家训作文素材使用【一】
《朱子家训》中有两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其中一句是“子之所贵者,孝也。”意思是子孙能做到孝是非常可贵的。现在有许多小孩子在家中得到妈妈、爸爸和祖父母的溺爱,宠成了“小皇帝”“小霸王”等等。在小孩眼中,“孝”字渐渐变得暗淡无光,有的孩子甚至不知道“孝”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从记忆中找回这个“孝”字,从《家训》中深刻理解“孝”的含义,让“孝”行动起来,让“孝”字从人们心里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还有一句话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意思是不要以为是一件小小的善事你就不去做,以为一件小小的坏事做一做没关系。这句话使我想起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
八岁那年,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公园玩。我看见了一个水龙头在那哗啦哗啦地流着水。我正好从流水的水龙头边走过,却当没看见似的走过去了。而读完《家训》后的我却认识到自己错了:地球这么缺水,如果每一个人都节约一滴水的话,世界上有几十亿人口就能节约几十亿滴水了。
就在去年,有一天我到公园玩耍,看见公园门口有许多漂亮的蝴蝶花。我看了看四周没有什么人,就偷偷的摘了一小朵蝴蝶花,心想:反正这儿有这么多花,我摘一朵有什么关系?正巧,一位公园的管理人员带着微笑朝我走来:“小朋友,应该爱护花草,公园才能充满绿色。”当时,我很不服气,我就说:“就摘你一朵,干嘛这么小气?”说完,我转身走了。
这两件事就应了“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现在我决心从每一件小事做起,使自己从小都做好事,把每一件小事积累在一起,不就成了一件大好事了吗?我们应该把《朱文公家训》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社会上的人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朱子家训作文素材使用【二】
我对朱熹的认识缘自鲁迅。鲁迅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是“中国的脊梁”、“中国的良心”和“中国的希望”,以启蒙为己任的鲁迅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人,其中就包括我。客观上讲,从汉武帝到宋理宗,这一千多年是董仲舒的儒学时代。董仲舒倡导的汉代经学,已经偏离了儒学的原教旨,加进很多汉代人特有的迷信。千年的世事沧桑,到了南宋时,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进步,汉代经学已经是破屋漏雨、破船漏水,无法自圆其说了。朱熹的理学于是应运而生,红火了几百年。中间虽然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冲击,几番较量后,还是理学占了上风。到了清末民初,被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气蒙了的文化人,开始反思。先是龚自清,后是谭嗣同,再后来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诸君。反思的结果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是朱熹的理学盛行,国民性孱弱不堪、奴性十足,造就出来的都是没有血性、没有狼性的彬彬君子。鲁迅有名的理学“吃人”说,就如此深刻地印在我这一代人的思想中。至于朱熹的理学本身究竟为何物,一般人其实并不懂得。文革中的批孔闹剧最滑天下之大稽,说它上承五四精神吧,却闭口不谈科学与民主;说它下开思想自由之先河吧,却对钳制自由思想的法家推崇备至。这笔糊涂账还没有算清,八十年代的李泽厚们就高举启蒙大旗,发起又一轮声讨封建、其实是声讨朱熹理学的思想战争。这场思想战争到今天还在继续,年轻一代(相对李泽厚先生而言以新批判主义为大本营,以启蒙为己任,继承着鲁迅,批判的锋芒依然直指朱熹理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思想之芒》,简述过论战的情况。我曾经是鲁迅的崇拜者,是李泽厚的崇拜者,是新批判主义的拥趸者,我的许多文章都对朱熹理学大加挞伐。说句不怕丢丑的话,我从来没有想到去认真读朱熹先生的原著,所有的观点都是时代教给我的,所有引用的朱熹的话,都是被精心挑出来供批判用的材料。及待我读了朱熹的原著,方知在很多方面误解了朱熹。朱熹理学的真理程度且不论,起码,一百多年来的民之疲弱、国之外侮,不应归咎于它。它也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或许还是中国未来思想大厦的椽檁和砖石。
朱熹理学,顾名思义,“理”在朱熹的哲学中占着重要的位置。什么是“理”呢?朱熹认为,万物有万理,万理加起来就是“太极”。很有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理”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开天辟地之前,“理”已经先天存在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见《朱子语类》“气”在朱熹那里也是非常重要的,“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理亦无挂搭处。”朱熹认为“气与理”是不可分割的伴生物,“气”好像是“理”赖以存在一种形式。也就是说,真理是以物质运动为前提的,没有物质的运动,也就没有真理。实际上朱熹已经摸到客观真理的门口,与辩证唯物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朱熹到了这里就止步了,他说:“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也就是说先有意识的“理”而后有物质的“气”。前边说理、气之序无先后,后边又说理在先,气在后。反映了朱熹思想中的矛盾性,他无法自圆其说时就用“相似”二字来搪塞。这一“相似”,就把朱熹的哲学思想“相似”到唯心主义的阵营。朱熹是一个熟练的佛学家,他把佛学中精巧细致的思辨用于哲学的论述,较之于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更有系统性。这样的哲学思想显然不会在大众中流行,不会产生国弱民疲的后果。受人诟病最多的是朱熹世俗的儒学教化。他认为儒学的精华不仅在“五经”之中,更体现在“四书”里边,而汉代的经学不以“四书”为念。经过他重新解释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成了理学的经典。用以克服颓废的魏晋风度、改变唐代的尊卑失调,纠正南宋的萎靡不振、人心涣散。朱熹希望建立一个周密的、有秩序、有效率、符合人伦道德的社会。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君臣同心,抗击外族的侵略,才能担负起国家救亡的任务。他专门为青少年编著了《小学集注》,教导他们如何遵守秩序、修身齐家,非如此不能担负起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收复北方山河的重担。他编著了《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期望从儿童起就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待人接物的习惯。如穿衣要整洁,说话要和气,读书要耐心,吃饭要慢咽,待人要持敬,做事有涵养,做人莫放纵等等。这些要求即使在今天看来,对儿童的成长也是有好处的。由于朱熹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投降、主张武力收复国土的主战派,他要人们“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灭仇寇”,所以投降派们视朱熹为敌,视朱熹的理学为“欺世盗名、不宜信用、遗祸于世”的“伪学”。投降派还企图从人品上搞臭朱熹,监察御史沈继祖就捏造朱熹霸占友人财产、引诱尼姑当小妾的“罪状”,逼得朱熹不得不向宋宁宗认罪,违心承认自己“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逼得朱熹的学生们或隐居山林,或改换门庭,或放荡勾栏,即使如此,还是被当局罗织了一个以朱熹为首的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案”。庆元六年,朱熹在失望与苦闷中离开他挚爱的国家和人民,他在理论上构建的新社会理想,注定在南宋那样一个腐败无能的朝代无法实现。
朱熹理学走上神坛,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盛世尊孔的需要。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追求的最高目的是周礼。周礼是一种秩序,即在尊卑有序的前提下,社会各个阶层都温情脉脉地谨守本分。上无苛政之疾,下无造反之心。理学没有动摇孔学“礼”的根本目的,但是把长幼尊卑秩序纳入礼的范畴,并把它说成是天理,而个人的***是无穷的,不能放纵,只能克制,否则人欲横流,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这就是朱熹著名的论断:“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任何一个专制社会的统治者都乐于看到的景象。元、明、清三朝,都把理学奉为治民的不二法门,也就不奇怪了。二是把理学极端化。封建统治有个特点,就是政治和思想的高度专制。理学既然有此治民的功效,元仁宗时代就规定,科举题目就在“四书”中,答案以朱熹的解释为准,其他思想都是异端,必欲铲除而后快。明代末年有个叫李贽的向理学发起挑战,最后死在监狱。理学的负面作用由此而始,鲁迅没有错,问题出在政治家对思想成果的操弄。只说半句真话等于撒谎,强调真理的某一部分,就意味着否定真理。
在人类文明的灿烂原野上,思想是最自由的花朵,就像春有桃、夏有荷、秋有菊、冬有梅一样,强制要求“我花开后百花煞”,其结果必然是“百花凋零一花谢”。思想又是一条流动的河,漩涡、浪花、激流使得河水生生不息,一旦河水停止了流动,再清的河水也会死寂。理学被封建政治极端化、单一化的结局只能导致理学的衰落。理学是为那个特定时代量身定做的思想。试想,产生于宋代的理学,却要求它观照清代的现实,岂非刻舟求剑?这不能责怪朱熹先生,甚至也不能责怪理学本身。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不能责怪奥古斯丁一样。就像希特勒发动二战不能责怪尼采一样。就像东欧解体不能责怪马克思一样。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一个时代背景,离开这个背景,思想就不能适应,需要进化、修正甚至解构。世界上没有凌驾于万世的思想。
朱子家训作文素材使用【三】
为弘扬传统文化,宣传国学思想,武夷书院讲坛2日在福建武夷山正式启动。历史记载,武夷书院位于隐屏峰下平林渡九曲溪畔,是朱熹于宋淳熙十年(1183年所建,为其著书立说、倡道讲学之所。
根据规划,武夷书院讲坛每年举行六讲,邀请海内外朱子文化专家学者做主题演讲。同时,武夷山正着手加快修复一批书院,将其打造为普及朱子文化、传播儒学思想的重要平台。
朱文公第二十九世裔孙、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朱杰人表示,在中国大力倡导“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具有现实意义的朱子文化正迎来多重机遇,将会促进中华文化海内外的传播和交流。
武夷山市官方还披露,将实施朱子文化建设“五项工程”,建立朱子遗迹遗存数据库,对五夫镇、风景名胜区等重点区域朱子文化遗产实施有针对性的保护修复;适时提升一批文化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格。
作为东亚文明的象征,朱子学传入日本、朝鲜、欧洲等地区后,至今影响深远。在对外交流方面,武夷山将推动朱子文化对外交流,配合举办“朱子之路”研习营、海峡论坛配套活动等对台对外朱子文化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