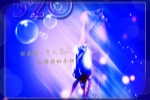以童年这本书梗概写作文【一】
有个胆小的小女孩儿,因为胆怯,她孤独,一个人,她不聪明,自卑,失败,她的心是灰的。
天,蒙蒙
人,廖廖
我望却人心,灰暗
一皎月光,双眸淡了
心,凉凉
人,无情
心,无感
万物,繁华,在眼似硝烟,
心,死了。
开始,年小的我。
天,朦胧,而远远的山影,模糊,似披上白纱,轻盈,神秘,迷人。
小径上,独自踏着小碎步,撑一把小伞。嫩小的脚踝踩在地上,水花溅起,绽放。伞内只有我一人,抬头,望去,看着伞外的世界,人往来,车驶去,但从始至终,仅我一人。
从小,胆小,害怕逐渐发展成如今的孤僻,冷眼旁观周围三三两两的同学,形如隐形擦过,离去,心生冷意。台阶,上去,转身,合上小伞,我懒散的走着,路上伸出手任凭细密的小雨点点地轻拍在小手上,满满的,流下,荡成一季娇艳樱花的飘散零落。
我紧合眼帘,在这绵延无情的雨中,只剩冰冷的水珠与之摩擦的细微响声,对还有这幼小却冷血的心跳。轻启眼帘,一个花季的女孩,清浅的微笑着:“天冷,别玩过头,小心着凉,进来点吧。”随后,她走了,而那清澈空灵的声音却在徘徊,心好像有了什么。
在家,乡下,那泛黄的日历上是我,那日,我在校门口,一个老人,一身灰衣,在那伫立,像一座雕像。但在我走进,它变成了我的外公。他呵呵的笑,陪我回家,在公交车上,我刚想投钱,却只见外公按下我手,掏出了一个塑料袋,解开后又是一个袋子,打开,里面是一张张破旧的角角元元的钱。他把钱放进去,剩下的给了我,那时外公的手在不停的颤抖着,龟裂的手尖意外的冰冷,我莫名的害怕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外公那天是走来的,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心,那灰白的世界,那死寂的天,死寂的谁,死寂的心碎了。
转眼间,我变了。单调的童年,有我的改变,或许,只有一点。
在街道中,夜幕是我娱乐的地方。我的梦,我长大的童年在寂寥长空绽放着绚丽的花朵。
我很喜欢烟花。尤其是那细长的一根,上面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成分,下面是一根短短的铁丝。偏褐色,微微有些气味。只要点上火,拿在手中,便可“画”出一道又一道的美丽图案。不过经岁月的洗礼,它的名字变得神秘,只记得,那闪烁的亮光,那飘渺的舞蹈,那快乐的笑声。它闪耀在角落里,轻轻诉说,挥舞起来仿佛流星滑落,于是,在小小的童年里,它是我的一种实梦者。天边的流星我从未见过,手中的“流星”却填补了我的失落。“流星”,我的寄托,在洒满烟花的夜空下,闪闪舞动。让天鹅绒般天际如少女般娇艳,而随着“劈啪”的响声大地披上了彩衣,点亮了夜间的精彩逗笑了星星……记得那时喜庆的热闹,嫩稚的我在奔跳,在哥哥的身边,略享风儿中的美丽,心中的好奇与无知我同大人争吵,好不容易获得了点烟花的使命,小小的手握住带着火心,激动又紧张,一步步接近,心一轮轮兴奋,慢慢地我点燃了烟花,立马跑开,然而就在站定转头的一瞬,“碰——”的一声烟花绽放,天际上五彩斑斓的烟花交织在一起,绚丽自己的妖娆。风摇摆树儿伴着花朵在花火中摇曳,“沙、沙”的树声陪伴着渐暖的晚风拂过簇簇火花,让无言的愉悦悄悄流入我的心底,我痴迷了,在那是单纯天真的幼小心灵,天,那是梦中天堂,精灵世界,朵朵花火飘舞,零落,竟令那本单调,灰暗的城市变成了幻境,冰冷而宏伟的建筑映着光芒如脱胎换骨般栩栩动人,刚硬中带着柔美,寂寞中暗涌着期望,夜,偎依着亮空久久徘徊在这流光之中而我是痴迷了脑海夜色的花火如一朵鲜花,绽放,是漫天的绚丽繁华,燃尽,却令我无比怀念……
童年,我,这是最后完美的我。童年中,我渐渐长大了。现在,我的童年花朵结出的果实,已经成熟。
以童年这本书梗概写作文【二】
我只说您永远也收不到我的那封信了,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您的信竟能邮来,就在您死后的第十一天里。今天的早晨,天格外冷,但太阳很红,我从医院看了病返回机关,同事们就叫着我叫喊:"三毛来信啦!三毛给你来信啦!"这是一批您的崇拜者,自您死后,他们一直浸沉于痛惜之中,这样的话我全然以为是一种幻想。但禁不住还在问:"是真的吗,你们怎么知道?"他们就告诉说俊芳十点钟收到的(俊芳是我的妻子,我们同在市文联工作,她一看到信来自台湾,地址最后署一个"陈"字,立即知道这是您的信就拆开了,她想看又不敢看,啊地叫了一下,眼泪先流下来了,大家全都双手抖动着读完了信,就让俊芳赶快去街上复印,以免将原件弄脏弄坏了。听了这话我就往俊芳的办公室跑,俊芳从街上还没有回来,我只急得在门口打转。十多分钟后她回来了,眼睛红红的,脸色铁青,一见我便哽咽起来:"她是收到您的信了……"
收到了,是收到了,三毛,您总算在临死之前接收了一个热爱着您的忠实读者的问候!可是,当我亲手捧着了您的信,我脑子里刹那间一片空白呀!清醒了过来,我感觉到是您来了,您就站在我的面前,您就充满在所有的空气里。
这信是您一月一日夜里两点写的,您说您"后天将住院开刀去了",据报上登载,您是三日入院的,那么您是以一九九○年最后的晚上算起的,四日的凌晨两点您就去世了。这封信您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呢,是一九九一年的一月一日白天休息起来后,还是在三日的去医院的路上?这是您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更是您四十八年里最后的一次笔墨,您竟在临死的时候没有忘记给我回信,您一定是要惦念着这封信的,那亡魂会护送着这封信到西安来了吧!
前几天,我流着泪水写了《哭三毛》一文,后悔着我给您的信太迟,没能收到,我们只能是有一份在朦胧中结识的缘分。写好后停也没停就跑邮局,我把它寄给了上海的《文汇报》,因为我认识《文汇报》的肖宜先生,害怕投递别的报纸因不认识编辑而误了见报时间,不能及时将我对您的痛惜、思念和一份深深的挚爱献给您。可是昨日收到《文汇报》另一位朋友的谈及别的内容的信件,竟发现我寄肖宜先生的信址写错了,《文汇报》的新址是虎丘路,我写的是原址圆明园路。我好恨我自己呀,以为那悼文肖先生是收不到了,就是收到,也不知要转多少地方费多少天日,今日正考虑怎么个补救法,您的信竟来了,您并不是没有收到我的信,您是在收到了我的信后当晚就写回信来了!
读着您的信,我的心在痉挛着,一月一日那是怎样的长夜啊,万家灯火的台北,下着雨,您孤独地在您的房间,吃着止痛片给我写信,写那么长的信,我禁不住就又哭了。您是世界上最具真情的人,在您这封绝笔信里,一如您的那些要长存于世的作品一样至情至诚,令我揪心裂肠的感动。您虽然在谈着文学,谈着对我的作品的感觉,可我哪里敢受用了您的赞誉呢,我只能感激着您的理解,只能更以您的理解而来激励我今后的创作。一遍又一遍读着您的来信,在那字里行间,在那字面背后,我是读懂了您的心态,您的人格,您的文学的追求和您的精神的大境界,是的,您是孤独的,一个真正天才的孤独啊!
现在,人们到处都在说着您,书店里您的书被抢购着,热爱着你的读者在以各种方式悼念您,哀思您,为您的死作着种种推测。可我在您的信里,看不到您在入院时有什么自***的迹象,您说您"这一年来,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它不来自我个人生活,而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又说您住院是害了"不大好的病"。但是,您知道自己害了"不大好的病",又能去医院动手术,可见您并没有对病产生绝望,倒自信四五个月就能恢复过来,详细地给了我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且说明五个月后来西安,一切都作了具体的安排,为什么偏偏在入院的当天夜里,敢就是四日的三点就死了呢?!三毛,我不明白,我到底是不明白啊!您的死,您是不情愿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而死的呀,是如同写信时一样的疼痛在折磨您吗?是一时的感情所致吗?如果说这一切仅是一种孤独苦闷的精神基础上的刺激点,如果您的孤独苦闷在某种方面像您说的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三毛,我完全理解作为一个天才的无法摆脱的孤独,可牵涉到我,我又该怎么对您说呢,我的那些书本能使您感动是您对我的偏爱而令我终生难忘,却更使我今生今世要怀上一份对您深深的内疚之痛啊!
以童年这本书梗概写作文【三】
??本书真好看-500字晚上七点,家家香气弥漫,当然东东家也不例外。从厨房里传来一阵叮叮咚咚的`声音,原来是妈妈这位大厨正在做着晚饭,身为球迷的爸爸也抱着电视机看着球赛,不时的欢呼着:“太好了!进了!”,而一向成绩很好的东东,却不知在卧室干着什么。“开饭喽”随着妈妈温柔的呼叫,爸爸就像个小磁石一样,被吸铁般的饭桌吸了过去,爸爸刚要拿起筷子夹一块又红又肥的红烧肉,就被妈妈制止了:“没看见儿子缺席了吗。赶快叫他去。”爸爸无奈,只好去卧室找东东。
“东东,快来吃饭,有你最爱吃的红烧肉!”爸爸大声叫道,可是没有回音,爸爸的脚步加快了,决定去一探究竟,爸爸推开了卧室门,看到儿子正在津津有味得看着一本书,爸爸推着儿子说:“吃饭了,”儿子这才记起该吃饭,便走向客厅,爸爸瞟了一下了书……
东东坐到了座位上,妈妈问:“你爸呢?”东东摇摇头,跑向卧室,爸爸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本书,儿子说:“爸爸,我不看,怎么你又看起来了,”爸爸笑着,不好意思地走向客厅。
东东边吃边想:这本书可真好看,爸爸差点就被他迷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