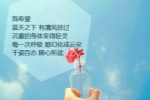山火蔓延飞机坠落作文【一】
问我们为什么笑,时间还要到回去年了,也是这个时间,我也住在了舅舅家,我们一次买了二十多个孔明灯,回到家就跑到顶楼放去了,刚好姐姐也在,我打着灯,他们拆,想当年够衰,一个没放出去,还留了几个呢。
回到屋里,哥哥翻出了前年的孔明灯,包装袋儿,还好好的,不过落了一层灰尘,哥哥甩了几下,到处都是灰:“走,今年得打破去年的记录才行。”啊?难道一个都放不出去了吗?为什么要打破去年的记录啊?放个负的不成?
“想什么呢?走喽,叫上你姐,当年也有她呀。”我们一想到被姐姐一烦撕了一个大口子的孔明灯,又笑了。
顶楼阳台。
“来,你还打灯,我们来拆,我就不信放不出一个。”哥哥愤愤的看着地上散落的孔明灯。
“我说去年为什么没中500万,就因为孔明灯没放出去,不怪我就怪他。”姐姐分分不平的向哥哥手中的孔明灯抱怨,我们望着他一阵无语。
拆了第一个,哥哥小心翼翼的拿着边缘转了个圈,让他灌风撑起来,这个还可以,我们便开始点蜡,蜡被哥哥弄的`怪怪的。蜡慢慢开始燃烧起来,我们渐渐的看着它撑起来,等了一段时间,哥哥看差不多了,便要试试行不行,用力一举,向上去,啊!我们三个一齐向后退去,看清后笑得直不起腰,原来是孔明灯飞走了,蜡油却留了下来,在地上燃烧着,没办法喽,又放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几乎每个都以不同的方式阵亡,难道是风水不好。
“还有一个。”我刚说完,楼下就传来了小外甥的哭声,姐姐闻声便下去了,我们拎着那一个决定去二楼试试风水,到了二楼,一样的流程却顺利很多,难道是因为姐姐不在,有可能。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我们还是去三楼放吧,这风不好。”
“行。”
哥哥小心翼翼的向上走,我在后面护驾,轻轻一举,孔明灯果然起飞了,向前飞去,注意是向前飞去,不是向上,前面是什么?交错的树杈呀,正想着,眼看有向上的趋势,一阵风直直得让孔明灯撞上树叉,那个孔明灯是在挣扎,竞挣了出来,但又撞向另一棵树,滚了两圈,和不知道第几个孔明灯躺在了一起,光荣阵亡。
又一阵无语。
“肯定又是姐姐,她一定要许了今年要中100万的愿望,所以所有孔明灯才一个都没突破重围飞出去。”我扭头又看了一眼树上快燃起来的孔明灯,一定是这样。
“对,我们一会儿下去就说放出去了,骗他们一下。”
“好啊……”
虽然孔明灯又一次没有放出去,但在这一年我也要蒸蒸日上啊。
山火蔓延飞机坠落作文【二】
摩加迪沙伏击其实是一次多兵种联合行动,主力是陆军的游骑兵和三角洲特种部队,但参加战斗的还有160特战航空团(夜行者)、海军海豹特遣部队和空军的通讯、救护特种兵。分析这次战斗,可以看出美国特种部队有多强——还有难以避免的弱点,当他们在一个文化迥异的第三世界国家采取行动时。
索马里的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怀疑那里可能是本拉登的一个逃难地点。中情局发现他的“xx”组织向索马里港口运装备。索马里跟阿富汗一样,也是一个乱糟糟的无政府国家,本拉登要躲藏,确有很多有利条件。
索马里位于非洲东部,在所谓的“非洲之角”,与阿拉伯世界的亚洲部分隔洋相望。居民也和阿拉伯人一样,信仰伊斯兰。十九世纪后期,索马里逐步沦为英国(在南部)和意大利(在北部)的“保护国”。一次大战后列强重新瓜分世界,英国曾把肯尼亚东部的索马里人居住地区让给意大利。二次大战时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该国南部的索马里人居住地地区也与索马里通成一片。大战之后,联合国在1949年通过决议,索马里北部由意大利代管,十年后独立。这期间,英国也在南部逐步建立代议制度和执法系统。1960年7月1日,南北索马里合并,同时宣布独立。
独立之后,当时掌权的倾向欧洲的温和派主张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邻国搞好关系,将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但是,一个民族新生时必然伴有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令很多人念念不忘在这两国的“自古以来就是索马里的神圣领土”。要打仗的左翼少壮军人在1969年10月21日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政变***西亚德(MohamedSiadBarre)宣布,“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导人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由他自己担任***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则自然是领导索马里事业的核心力量。1974年,西亚德签订了苏联与非洲国家的第一个互助友好条约,并拿着苏式武器开始进攻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但是,也是在1974年,埃塞俄比亚也发生了左翼军人政变。9月12日,海拉西皇帝被废黜。苏联自然不希望两个亲苏政权兵戎相见,这下气翻了西亚德:埃塞俄比亚在动荡之中,正是索马里攻城略地的天赐良机。1977年11月,西亚德废除友好条约,赶走全部苏联顾问。接着他转向中国,翌年4月访问北京。当时中共早跟“苏联修正主义”闹得不可开交,立即答应供给苏式武器。后来美国游骑兵要面对的,就是拿着中苏两国制造的冲锋枪和火箭筒的索马里兵民。
当时苏联威风尚在。俄罗斯大哥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岂容只有上校军衔的西亚德踢他屁股?苏联立即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运了一万古巴精兵到埃塞俄比亚。我们没有雇佣军可派,只能眼睁睁看着刚认下的黑小弟被北极熊揍得尿滚屁流,折兵损将逃回索马里。
山火蔓延飞机坠落作文【三】
??落在轮回里面的星星我的生命是一根缰绳,珍贵只是牵满了星星,我的年华是一块夜屏,可爱只是匿藏着歌唱,星星的歌唱。
都只是在哀悼轮回?
透明胶上的粘着的文字,都是我的一些过往罢。很久就睡在回忆里,梦着那些曾经很真实的满天星星璀璨的岁月;但是,梦属于过去,梦想即便属于未来了,不是么?于是幻想。单纯的幻想着下一个轮回,在圈圈圆圆的生命第二次。我扬起脸,看到的闪烁繁星和明明无无的月光,可没有月亮,便亦无圆与缺之谈。
我是一只乌鸦,那个冬天是我第二次生命的开始。我不明白,白色的季节为什么赐予我黑色的羽毛,茫莽的`阴影搁伤了我的喉咙,“呀——呀”的叫声混淆着空气变成哭泣。
不过单调的生活很快让我习惯自己。
也许我的命运很糟糕,但是我一直过得很真实、纯朴。并整天整夜如此乐观地歌颂我自以为了不起的生活意义,尽管我的歌声使我狼狈——人们把我视为倒霉之物,把我的忠告听成诅咒——如此狼狈。
而我知道,这不过仅仅是黑色的奉予罢了。
举头,侧目,忽见微闪星星。
我忍不住又叫:“呀——呀——”夜空很狰狞,欣悦只是星星灿烂地冲我笑。我也希望像星星一样,微笑,大笑,甚至狂笑。可是我不懂得。
冬天的夜,漫无温热的夜,我孤立在光秃秃的枝头,望着自己的投影不断地打寒颤,于是飞回窝里去。刺骨的寒风使我难眠,漫长寒夜,我数着天空中的繁星,直到启明星也消失,然后对自己说晚安。
树下面有位老人,是乞丐,老人蜷缩在树边,挣扎在生命线的最后。生命是一条线段,有两个端点。起点很欢悦,但终点不一定。几道寒风的镂刻,老人终于在颤抖中死去,但身子便不颤抖了。这是伤悲里的幸福么?我在老人上空盘旋了几圈,然后哀鸣:“呀——呀——”随即下面走过的路人说:“该死的乌鸦。”
其实,我何尝不是在哀悼老人?
我依稀听见星星的歌唱,歌唱老人的轮回。
那些星星的影子,摇曳在老人的明眸里,最后坠落于他的轮回,老人目光呆滞。
这是我的第二轮回,只是还没走到尽头,我懂得这叫浓缩,浓缩在一颗闪烁的星星里。
我是一只乌鸦,当走到线段的第二个端点,那便是我第二次生命的消亡,也是生命的第三次开始。我知道,坠落在轮回里面的仅仅是星星的影子。
繁星。璀璨。
闭上眼,等待下一个轮回。
山火蔓延飞机坠落作文【四】
记得今年断断续续可以看到过去一年的光影记录,那些我憧憬却不曾去过的地方。
而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也已经再也不能在午夜听到火车的汽笛声。
而那条可以通向很远地方的铁轨,也再没爬上去过。
——题记
儿时的家在铁轨后面,大人说,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去穿越铁轨下方的桥洞必经的那个下坡去看火车。
可其实我对这件事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记得火车出发之前会有汽笛,可是现在近乎听不到了。
广严哥总说:多出去走走,会长很多见识,女生应该多点见识。
顺便刚才看到了他最新旅程结束——
瑞安-杭州-北京-多伦-蓝旗-锡林郭勒-东乌旗-宝格拉苏木-巴彦霍布尔-宝格达乌拉-乌拉盖-霍林郭勒-扎鲁特旗-阿尔山-辛巴尔虎左旗-辛巴尔右旗-阿尔山-满洲里-海拉尔。
他去过太多地方,海南,厦门鼓浪屿,浙江乌镇,江西婺源……统统是我想去的地方。
不知道毕业之后他到底是在工作还是在干嘛,可他的骑行之旅一直到现在好像都没有结束,也没有因为长途跋涉瘦成木柴反而日渐发福。我记得他买户外装备的时候我还对于“双层帐篷”浮想联翩是不是跟双人高低床一样,结果其实是差不多双层保暖的意思。
看吧这就是没见过世面。
五月份的时候收到了广严哥婺源回来寄来的明信片。他说在婺源遇到了三个九三年出生的小女生逃课出来,聊了很多好玩的人和事。
他说,旅行不仅仅是遇见人遇见事,更多的是去发现另一个自己。
不知不觉间我就被他成功灌输为一心想要逃离这个小城市去外面看看走走的人。
我甚至觉得,总有一天,他会走出国境,并且只要他想,这种事情不会太久。
甚至可以想象到他这近乎要遍布中国的旅程遇到了多少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遇到的奇人趣事。
他所到之处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一段路可以有多远?
小时候我爬上过铁轨,也走在铁轨上过。可能有些东西就是天生注定,从小喜欢看火车的我,长大了一心都在想着去远方。
北方太过枯黄的色彩挡不住我对江南的向往。
可是你不知道在乌镇写那15张明信片的时候,如果我有充足的时间,我会安静下来一点点写给你们我从上海的城隍庙到黄浦江畔再进入浙江是怎么样的心情,以及我多喜欢江南的糕点小吃。
广严哥一定会很乐意听我跟他讲这些事。
我知道他想去的地方还不止这些。
可是在我还在想为了生活要怎么努力拼搏才能生存下来的时候,他明明比我少了那么两三年可浪费的时间,他却在把我们共同讨论过的这些地方已经化作了亲手拍下的照片。
可能我需要的只是一点说走就走的勇气。
例如年初再去北京的.时候,坐上了动车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心烦事都没了。哥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上车,有什么想法。我说:尘埃落定。
走过我熟悉的每一站,看过我所熟悉的所有风景。
也许我们的共通性就是浪迹天涯。
这种不切实际的事把它变成现实却这么令人羡慕。
海南的椰汁。鼓浪屿的奶茶店。杭州的西湖。乌镇的小桥流水人家船舟摆渡。婺源清晨的云雾缭绕。敦煌的封印的尘埃神话。西藏神圣的佛教和绝美的纳木错。台湾小吃街的蛤仔煎。上海的黄浦江。蓬莱的海市蜃楼。北京的故宫皇城。内蒙的辽阔草原……
相较起来可能会更爱日本的北海道,巴黎的埃菲尔,大溪地,巴厘岛,或者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的食人岛。
我们想要触碰的世界太大。
高楼大厦围堵的城市之外,我们想要的都在那里,可能也不在那里。
你说,沿着铁轨的方向一直走,会不会就不会迷路,就会走出一直迷茫着的那个自己?
可是总有一天,我也会漫步在婺源清晨云雾缭绕的油菜花丛,我也会在纳木错的苍穹之下触碰天际。
不管是我们的事业,还是我们各自不同的另一个目标,亦或手持单反游天下。它们始终没有停止过萌芽长大。
你告诉我:旅行要发现的是,那个完全摆脱了束缚,释放出真我的另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你相信我,总有一天,这些不曾停止萌芽长大的梦,会开花结果。
一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