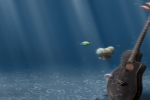民国满分作文心之力【一】
楚庄王有一次主持朝会处理政事,一直到很晚才结束。樊姬走出屋子迎接他,关切地问:“为什么这么晚才结束?难道大王不饥不倦吗?”
楚庄王说:“今天听到忠诚贤能的臣子进言,所以我不感到饿,也不觉得累。”
樊姬问:“大王所说的忠诚贤能之士,不知是诸侯国中的宾客呢,还是楚国内的哪一个人呢?”
楚庄王说:“就是沈令尹啊。”樊姬听了,掩住嘴巴笑起来。楚庄王奇怪地问:“你为什么发笑呢?”
樊姬回答说:“我侍奉大王您,负责沐浴、梳洗、铺席,已经有十一年了。但现在,与我身份同等的有十人,比我贤明的有两人。我难道就不想独揽大王的宠爱吗?我是不敢以我个人的私欲来遮蔽别人的美好啊。沈令尹辅佐大王好多年了,但他不曾推荐贤能之人,也不曾贬退无能之人,这怎么能算得上是对您忠诚呢?”
第二天早晨,楚庄王上朝时,把樊姬的话告诉了沈令尹。沈令尹立刻向楚庄王推举了孙叔敖。孙叔敖治理楚国三年,使楚国成为了诸侯国中的霸主。楚国的史官提笔在简策上写下:“楚国成为霸主,是樊姬出了大力啊。”
【说明】 这则寓言说明,一个真正贤能的人,不仅要尽职忠诚,更要善于发现、推举比自己强的人才。
民国满分作文心之力【二】
齐景公让弓匠为他做一张弓,弓匠做了三年才完成。
齐景公拉弓射箭,连一层牛皮的箭靶也穿不透。齐景公大怒,要处死那个弓匠。
弓匠的妻子前来求见齐景公,说:“我是蔡国人,嫁给这个弓匠为妻。这张弓,是我丈夫用泰山之南坚韧的柘木、燕国的牛角、楚国的麋鹿的筋、黄河里的鱼胶制作而成的.。这四样东西,都是天下最精良的做弓材料,做成的弓射箭不应该只穿透仅有一层牛皮的箭靶。并且我曾听说,奚仲发明的车子不能独自行走,莫邪剑尽管非常锋利,也不能独自斩断东西,必须有人正确使用才行。射箭的方法,应左手稳稳地像靠着石头;右手好像拉着树枝,手掌好似握着鸡蛋,四根手指像折断的木棍;右手发箭,左手根本不受影响,这才是射箭的正确方法啊。”
齐景公按弓匠妻子所说的方法射箭,果然一下子穿透了七层牛皮做的箭靶。这位蔡国女子的丈夫立刻被释放了出来。
民国满分作文心之力【三】
枝繁叶茂的大树想去远方,又或有热情洋溢的人想让人生熠熠发亮。
唯独忘却自我力量。
大树从前只想借外物之力到达另一个境地;所谓青春年少也只不过依靠着周身的真实支撑。
我们总寻求寄托,摒弃实践;总沉迷念想,忽视作为;总着眼外界,无睹内在。
理想的寻求与达成,终究回归于自我饱含深情的起点,对自我的思索与发掘,对自我的革新与创造。
无数人败给了外力。
对己身不满,然后是无声的控诉与无可奈何的归于平静;对社会持异,改造人世的理想最终又被悄无声息地否决,再又回到对暴烈摧残生命的默许,对性别不公之象的`熟视无睹,或对《熔炉》、《素媛》事件持续发酵的司空见惯。
大多时日,大多数人,坚信自身力量的微乎其微,执着于自身对理想的无能无力。
然,正如大树冲破阻隔,凭己之力去往远方,芸芸众生间,亦有不懈于梦,无愧于心的人们,夺得了潜在的力势与优长,达到了心之所向。
听伊迪丝唱《玫瑰人生》,146厘米的个子,带她穿过了废旧的巴黎老巷,逃过了父亲的谩骂,避开了曼哈顿的繁华,皆因在音乐中觅得了梦想的真谛。
读柴静《看见》,她说,我们浑然难分,就像水溶于水中。纷繁的乱象与缺失关照的弱势群体,她将自己作为发力的来源与希冀的个体,将镜头深入山间树林,深入被黑暗笼罩的生命,终于寻获心之所想。
看约翰·纳什《美丽心灵》,数学家与精神分裂,不可思议的激烈碰撞。但他未曾屈从于现实,三十年,三十年对数学的热爱与往复的搏斗,他以自我无可匹敌的顽强与坚忍,战胜了所有喧嚣。
漫漫岁月,从个人到群体,从滔滔黄河之水到遥远深蓝的爱琴海之岸,浮于表层成为现象武装,当点到即止化为惯常思维,自我改变与自我追寻便显得稀缺,弥足珍贵。
去追,如霍金以病残之躯写成《时间简史》,靠《万物理论》;去发扬优长,如简·奥斯汀以细腻温和笔触力被封建屏障。
如大树,不仅是自我念想的实现,它的种子已在各个角落生根复蓬勃生长;如平凡又伟大的个人,柴静,纳什为梦想所贡献的,亦生长成人类社会的宝藏。
正如法国诗人兰波在其《深谷睡者》中所写,闪烁的太阳已越过高傲的山峦,幽谷中的光点有如泡沫浮泛。
以我之力,追我所愿,挣脱世间繁杂的禁束,去往内心无垢的星空。
民国满分作文心之力【四】
这是最好的时代,群雄汇聚,英豪四起,无论是工程科技还是文学艺术,都在此有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充斥苦难的四十年左右光阴里,民国大家们留下了太多值得称道的经典。然而当我们真正走近他们,看到辉煌,看到疮痍,也少不了喟叹一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细说民国大文人》记述评说了包括鲁迅、林语堂在内的七位文学大师的生平经历。我们能从中感受到林语堂的真挚淳厚,梁实秋的温润风趣,张恨水的才华横溢,鲁迅的执拗不羁,沈从文的浑朴淡然。在他们身上所呈现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一群追求真知孜孜不倦的学问人,更是战争时期每一个爱国者的肖像。他们无不历经坎坷,满腹的报国壮志和经纶才气,无论出自高门或是生在蓬户,唯有对于文学的热爱是始终相同的。
在我们憧憬先辈们传奇的生命之余,还应从他们身上领悟一些额外的精神。书中大师们有的蔼然仁者,有的恣肆狷狂,有的温润似水,有的刚烈如火。其中我更为欣赏张恨水,小康出身,也没有什么留洋经历,从报纸杂志被领进文学殿堂。他会的似乎只是编故事而已,但其才华之出众却有目共睹。作为一位文品俱佳的高产作家,他曾经同时创作六部小说,共创作中长篇小说多达110余部。他能够“楼上口占打油诗”。他以一支笔养活了其数十人的大家庭。他的作品虽常常被讥为“鸳鸯蝴蝶派”,风靡程度却远令人咋舌,上至党派高位者,下至闾巷莽夫,无不有恨水先生的忠实书迷。
更可贵的是他不参与政治。回溯中国古代,出仕以考究文学为主,有文采的人多半能摘取一官半职,由此养成了中国文人爱指点江山的秉性。然而文学与政治又有多大关联呢?反而在其受贬之际,远离政治才更易出佳作。张恨水单纯把自己放在一个写书人的位置上,从不像其他一些作家,但凡有了个人影响力,就试图大谈时局,妄言政策,却又无切实可行之举,甚至过度追求西化,全不考虑是否符合国情。
他也没有时下文人好打笔仗的毛病。左联成立后,在泾渭分明的.政治立场之下,几派文人于互嚼舌头的纸役中失了斯文,展露出可爱的凡人嘴脸,倒是颇具讽刺感。恨水先生几乎没什么文人通弊,却只在爱国上有些许特别的执拗。他的文学天赋实在叫人赞赏,老舍曾称他为“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作家”。
然而时隔数十年的今时今日,张恨水在年轻人中的知名度却不及老舍。原因大约有二:一来今天的年轻人们有了自己的文学偏好,已难接受先贤的种种佳作;二来又确实受了鸳鸯蝴蝶的掣肘。在为年轻人选取的名著书单上,现今的教育者们似乎是羞于将恨老的情情爱爱摆上台面,反而更好引取老舍的风趣正经了。就连《京华烟云》等享誉中外的通俗经典都堙没在当代言情小说的流行中,这种白话的普及甚至趋于退化的现状,恐怕是胡适当年不曾料及的。
我想说的是,中华文学之美瑰丽无匹,民国文学当称其中明珠一颗。在文学的传承中,我们不应再三将其简化,而更应深入其内涵。面对无涯学海,我们该想着如何畅游其中,而不是舀一碗喝过后,就敢说它是咸的。文学的甜当是隐匿在高处,在江海源头的某一座雪峰吧。
民国满分作文心之力【五】
多少伟人成就了自己的梦想,可他背后的付出又有谁能,谁能知晓。古人提倡“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高尚情操。中国礼仪一直传承与弘扬于后人,缅怀历史,只有认清和面对历史,才能更好地发展与进步。
仰望苍穹,漫长的路程何时可以结束。人生因有梦而美好与精彩,也因追梦而饱含幸福,正因为这样,人生才有意义,有价值。经历挫折与坎坷,战胜阻碍与磨难。也许这就是“苦尽甘来”。
曾经鼓舞自己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今只因心含愧疚。正处于青春年华之际,也是最把握不了的`短暂时光,也许刹那间什么都没有存在,只有内心的愧疚与自责,就像魔鬼一般缠于终身。也因此一生碌碌无为。
兄弟朋友之间,一句话可能让他们反目成仇;被关押的犯人,一句话可能让他们改过自新;等待救援的人,一句话可能让他们努力坚持。也许这就是一句话的力量。
一句不经意的轻浮的话,有时会自毁前程;而一句关怀别人的话语,却能让处于绝望的人有生存下去的理由与勇气。生命的过程是一种学习,任何人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免遇到困难和迷惑。给人一句鼓励的话,让人生奋起飞扬,何乐而不为呢?
请牢记,滴水可以穿石,掌心可以化雪,一句话也话也拥有无穷大的力量。但因为这样,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更应勿忘初心!
民国满分作文心之力【六】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