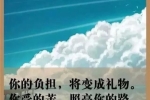背影为题疫情作文【一】
蓦地,一个熟悉的身影扑入我的眼帘。这不正是我的奶奶吗?奶奶身穿一件深灰色棉布衬衫,撑着一把宽大的雨伞,手臂间挎着一个略显破旧的菜篮子,微微佝偻着的脊背,在风雨中显得那么苍老,那么单薄。奶奶冒雨出门买菜,她步履蹒跚地向前走,只因为我早上吵着嚷着要吃红烧肉。望着那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的心中泛起一阵阵酸涩。记忆中,奶奶的背影是那么精神抖擞,那么宽厚,是我的依靠,给我安全感。可何时奶奶的背影变得这么苍老了呢?
记忆中,奶奶的头发只是夹杂着几根银丝,脸上永远笑容可掬。我永远不会忘记,奶奶牵着我的小手走进幼儿园微笑着叮嘱我,要好好读书,然后转身离开。那时的我追逐着那背影,不由自主地喊着闹着。我永远不会忘记,奶奶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做着我最爱吃的油炸冰淇淋,滚烫的油溅在奶奶那长满老茧的手上,尽情地跳舞。我永远不会忘记,奶奶在夜深人静的夜里为我掖好被角。望着那缓缓走远的背影,不知何时,眼泪如断线珍珠似的滚了下来。
光阴似流水一去不回头。如今我长大了,奶奶却老了,我想对奶奶说:“奶奶,我长大了,您在也不用那么辛苦了!该让我来好好照顾你了!”
背影为题疫情作文【二】
今年是鼠年,本来是一个美好而又充满活力四射的年,可是今年呢,却爆发了一种可怕的病毒,也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心形冠状病毒感染上的人呢?虽然大部分都出院了,但还是有一些人没有出院,可能他们,也在积极的接受治疗,毕竟心态好一些,比什么事都好。
在这期间出门都要戴口罩,不论你是做什么事情,而且要与人保持一段距离。一任里护士医生都在紧张又有序的忙碌着,他们努力的维护着病人,而且有的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也有家,他们也是人,但是他们有不一样的使命。他们甚至可以为了大家摄去一个自己珍贵的小家。有的家中有年老的父母,有的家中有还不到满月的孩子,还有家中苦苦等待的家人。他们都在苦苦等待着自己的家人。
而在一线上的医务人员们,他们不仅仅只是医务人员,他们是英雄保家护国的英雄,他们是家里亲人们的思念,哪一个家庭不期待着自己在一线上保护病人们的医护人员,平安归来,哪个不是呢?都是。他们都明白着这个重大的使命。
虽然他们努力地维护着我们的平安,可是有些人却不珍惜,还在损坏自己的身体,比如有些人,不但不戴口罩,还到自己的小区门口大声的骂着公务人员,如果你是这公务人员,是不是觉得太冤了?不过是不让出去,可以,谁出去?那不是白白送死吗?又危害了大家的安全,如果想自己出去,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去,也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虽然不想戴口罩,但也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你虽然不喜欢自己吧,但是我觉得你也不喜欢自己,但也别危害人呐!
在这非常的期间,我们要为他们点赞,为医护人员点赞,为奋战在一线的医生们点赞。最后我还要为所有奋战在一线的公务人员们和医护人员们都点一个大大的赞。
背影为题疫情作文【三】
终于,我拖着拉杆箱再一次,头也不回渐渐地远离了你的视线。
每一次,在火车的鸣笛声中,我们都在用着焦急的目光寻找着彼此的身影。但,似乎每一次,你的眼神都那么地沉稳而又急躁,而我却是那般的模糊与不安。也许我知道,每一次的再次相逢都意味这彼此的抱怨会再次升级。我总是会先在车厢里,找到一个高大却又瘦弱的身躯,那个一直支撑着我们那个小家的高大却而瘦弱的身躯,那个我又爱又恨的高大而瘦弱的——我的爸爸。
靠站了,我总是埋着头,拖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而你却悠闲地走在一旁。直到我开口说了句:“爸,帮我一下”,你才恍然大悟般轻巧的接过那大包点的东西。可是,你不知道我还是很累?其实,并不是劳累,是心累。没一次你都这样。从西站到军博,还有一段路程,于是我继续驼着,跟着你的背影,努力地穿过一群又一群匆忙的行人。而你却一点也不顾及我的感受,依旧走在我努力寻找的方向,你给我留下的是无情的背影,然而是你的无情伤了我的有情,所以,我怨,并且越发的怨。也许就是这样,使得我一直很独立而然而孤独。
挤卡刷,挤人流,挤地铁,你留给我的始终是模糊的却又在熟悉不过的背影。我也始终记得,我一个人驼着货物般行进在军博地铁的异样!而他们也和我一样,拉着各自的货物,吃力地挤地铁。而我必须紧跟着你,我一直在加速,我想看看你的正脸是否也有怜惜的眼泪,哪怕是一丝神情!我也就“欣慰”了,你呢?却从不曾缓慢你的脚步,留给我的依然是背影,可怨可恨的背影。
于是,陪你进货时,我从不帮你,而一直以来都是你一个人在凄清的凌晨——酷暑、雪冬,两点半出门,穿过整个北京市,挤地铁,挤公交,一个人拉着一大堆货物,滑稽地,吃力地穿越人海。而我紧随其后,纠结着,我决定帮你一把。那一瞬,你笑了,我哭了,我知道你依然也在怨着我,但你更爱我,只是你,不允许有柔情。
时光是短暂的。相遇的必然决定了别离的决然。我还是明白了你的认知:她该独立。于是,我拖着拉杆箱,一个人,头也不回地走着……
背影为题疫情作文【四】
记得在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女生,听说好像是个傻子,所以几乎班上所有的同学都讨厌她,不断的欺负她。
那时我并不是个开朗的人,也不关心一切,只是远离别人,默默的看着她被同学们排挤。她的位子总在最后,似乎连老师都有些讨厌她。这个班没有她的地位,这一点谁都清楚,可是没有人提出来。他们总踢她、打她,她的存在让我们班所有人都有了出气的对象。他们也许是在用这种方式暗示她,让她滚。可她是个傻子……
终于,她的妈妈来领她回家,或许她妈妈看见了她身上的淤青,或许她发现自己的`女儿真的伤了。她妈来领她回家的那天,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在欢呼,他们的心理仿佛得到了满足。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的存在实质上并没有对他们造成什么威胁甚至妨碍啊,难道就因为她是个傻子吗?
她傻傻的笑着,就那么对着曾打她、骂她的同学笑,全班人谁也没有理她,就因为她傻……
她就这样被她妈妈带出了教室,没有人送她。
当我抬头,正好看见她的背影。夕阳的余晖洒在她的背上,没有嫌弃她傻。她在夕阳下,沿着走廊一直走,那个背影没有什么特别,甚至有些木讷、有些难看,连头都没回,就渐渐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再也看不见了。可不知为什么,那个一步一步离去的木讷的背影我怎么也忘不了!
后来,班上又恢复了正常,全班人的记忆里似乎都没有了这个人,只有最后的那个位子一直空着,似乎在等着她。可我还是那么清楚的记得她让人打骂时的大叫、看着全班同学时的傻笑,还有那个没有回头的木讷的背影……
可能是因为她太傻吧!
背影为题疫情作文【五】
那年冬天,我的母亲去世了,临时委派的职务也卸职向后任交代了情况,近几天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几年未见的儿子从北京回到徐州打算跟着我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我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了母亲,眼泪不禁簌簌流下。我劝他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虽如此劝他,可我的心里却不住地咽着苦水:母亲去世,交卸了差使,以后的日子要怎样度过?
回家把家中的财产都抵押出去才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时日,家中光景惨淡得很,一半为了给母亲办丧事,一半为了我赋闲。丧事办妥后,我要到南京谋事,儿子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儿子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我因事务忙多,本已说定不去送儿子,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可怎么也不放心。再三嘱咐茶房,但又怕茶房不妥帖;我再三犹豫:行李这么多,车站买票的人也很多,还要办很多事情,他一个二十岁的孩子又没来过北京几次怎么办的妥帖?家里已经出了这么多事,他不能再有什么闪失,我就是要办的事情再多也要去送他!儿子再三劝我不必去;我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儿子买票,我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可我们的钱也不多了,只好忙着和他们讲价钱。可能那时儿子总觉得我说话不大漂亮,非要插嘴不可,但我也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他上车。我给他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他将我给他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我嘱咐他路上多加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他,以免他不能很好的料理自己。可他能明白我这一片苦心吗?
他说道:“爸爸,你走吧。”我往车外看了看,总觉得还缺点什么,突然想到儿子在路上还没有解渴食品,便对他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我虽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要费事些,可是给儿子买橘子还是我自己去吧。我走到铁道边,探身下去再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感到有些不容易。我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我走到月台的栅栏外的小摊旁买了一些又红又大的橘子。到火车这边时,儿子赶紧过来搀我,心中感到阵阵暖意。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他的皮大衣上。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儿子在路上也有可以解渴的'吃食了,这下也放心了些。我下车后还是有些担心儿子,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他望着我走出去。我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他,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回去后我便很轻松的走了。
近几年来,儿子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更是一日不如一日。我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我看到家庭如此败落的情况,心里感到悲伤,自然无法控制自己,使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情感积聚在心里不得发泄,自然要发泄出来;家庭琐屑的事情也往往惹怒我。我待儿子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我也忘却他的不好,只是惦记着他,惦记着他的儿子。他北来后我写了一信给他,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背影为题疫情作文【六】
自从上学后,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就少了很多。印象中,父亲总是忙忙碌碌,我都很少能有机会看清父亲的模样,但是父亲的背影却像烙印一样印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那年夏天,外面很热,知了在树上不停地叫着,我依旧立在门前等待着爷爷。随着“叮铃铃”一声铃响,爷爷的脚踏车便停在了家门口。我迫不及待地冲上去,踮着脚用小手在爷爷的车篓里搜寻着零食,半个身子都挂在了车座上。“噢,我找到了!”得意忘形中一不留神,“嘭……”我整个身子摔在了地上。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猛然间,我发现我的右腿被纱布半吊着,疼痛袭来,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突然有人抱住了我:“孩子,别怕……”我止住了哭声,抬头望了望,是爸爸。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红红的,像刚哭过一样,眼角还存留着一些未擦***泪水。我用小手在父亲的眼角擦了擦,爸爸勉强笑了一下。可我还是感觉到疼痛,不禁又哭了起来。爸爸拍拍我的背说:“会好的,一定会好的。”我顿时觉得温暖了许多。我有些睡意了,便把头埋在爸爸的衣服里。蒙眬中,我隐约看见爸爸那焦虑的背影,是那样的疲惫,又是那样的坚定。
接下来的几个月,爸爸每天都及时帮我换纱布,帮我活动筋骨。窗外不时能看到爸爸为我筹集医药费而忙碌奔波的身影。甚至有时不小心摔了一跤,他也顾不上拍一拍灰尘,爬起来就去继续工作。那时,我的心在隐隐作痛。其实,医药费东凑凑西凑凑也差不多够了,但父亲为了让我吃得更有营养些,拼命工作着。他每天很晚才回家,回家后还总要为我做些好吃的。当我看到爸爸来来回回忙碌的身影,我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爸爸闻声立马赶了过来,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我没有说话,只是怔怔地看着爸爸。才几天光景,爸爸整个人看起来都憔悴了:岁月的痕迹悄悄爬上了爸爸的额头,原本乌黑亮丽的短发也在不经意间点缀了根根银丝。爸爸拍拍我的头说:“睡吧!”当爸爸为我盖好被子,转身离去时,我又一次看清了爸爸的背影,是那样的憔悴,又是那样的疲惫。
当我的腿康复时,爸爸微笑着哭了。说真的,那还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哭。也许,每当我午夜梦回被疼痛惊醒吓哭时,殊不知爸爸也已经疼惜地哭过多少回了。想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我又看见那憔悴的、疲惫的背影……
背影为题疫情作文【七】
一步一步,一栋栋高楼后传来一阵脚步声,一圈又一圈。
又是一个休息日,我按平常时间来到楼下,开始跑步。一圈,两圈,三圈……喘气声渐渐加重,我快迈不动腿了,汗水一滴一滴。虽然还没到夏天,但真的好热,外套脱掉,身子好像轻了些。跑跑跑,冲冲冲。
咦,这个人还在跑。我刚下来时就看见了他,他也慢慢地跑着,我并没有太在意,毕竟只是一个陌生人。我现在看着他的背影,不知怎的,追随他的背影,一直跑,一直跑。我眯了眯眼,摆正已经歪掉的眼睛,看着路灯下的他。他一步也没有停,一直跑,一直跑。这肯定是一个疯子,我在心里嘀咕着,不然哪有人跑了这么久都不休息的。
风起,树叶摇曳。两旁的路灯映的树影纵横交错。昏暗的光线下,他离我越来越远,我加大步伐,追上去,可我并没有超过他,默默地跟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默默的跟着,时近时远。
再坚持一下,我咬着牙告诉自己,可真的好累,我望了望远处的他,不甘地拍了拍额头,他都能坚持下来我为什么不能?我还是体育课代表呢,凭什么那么容易放弃。一步一步。汗水一滴一滴,眼镜出现了一点点水雾。
终于,我停了下来,一种无力感蔓延整个身体。该死,为什么要停。心里虽是这么想,可身体却越来越沉重,差点要倒下去。不甘心,愧疚,还是期望,想在的我有一点想笑。我甩了甩头,强迫自己心静下来。抬起头,嘴角上扬,重新开始,只是他不见了。好累,我撇了撇嘴,还是搞不清楚,他怎么跑了那么久都不停。跑着跑着。
一位嘴角上扬的的妇女站在路灯下,昏暗的灯光拉长了她的身影,近了近了,那种熟悉的感觉……她转过身,“晓晓,该休息了。”说着递给了我一瓶水。微黄的灯光,照着她含笑的眸子,格外耀眼。
“妈妈!”我正好渴到不行,一大口一大口,没几下就见底了。
“嗯,慢点喝。”她看着我笑意越发浓重。
“妈妈,我们比赛,看谁先到家。”我随口说了一句话。本以为妈妈不会同意,没想到妈妈一口答应下来。
妈妈已经开跑,我却还愣在原地。“晓晓,走了。”
“嗯”我看着她那另人安心的背影,快步追了上去。
原来,那只是生命中的昙花一现,不是我的迟早会失去,我也不必懊悔,他只是一个过路人而已,一段记忆而已。我看着妈妈笑了,趁你还在我身边,我会好好珍惜的。
我霸道的拦在妈妈面前,轻声说:“妈妈,幸好有你。”妈妈的眼角,一颗晶莹的泪珠滑落。
幸好,你不是昙花,而我看到的也不仅仅是你的背影……
背影为题疫情作文【八】
我与儿子不相见已二年有余了。
那年冬天,我的母亲去世了,临时委派的职务也卸职向后任交代了情况,近几天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几年未见的儿子从北京回到徐州打算跟着我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我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了母亲,眼泪不禁簌簌流下。我劝他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虽如此劝他,可我的心里却不住地咽着苦水:母亲去世,交卸了差使,以后的日子要怎样度过?
回家把家中的财产都抵押出去才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时日,家中光景惨淡得很,一半为了给母亲办丧事,一半为了我赋闲。丧事办妥后,我要到南京谋事,儿子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儿子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我因事务忙多,本已说定不去送儿子,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可怎么也不放心。再三嘱咐茶房,但又怕茶房不妥帖;我再三犹豫:行李这么多,车站买票的人也很多,还要办很多事情,他一个二十岁的孩子又没来过北京几次怎么办的妥帖?家里已经出了这么多事,他不能再有什么闪失,我就是要办的事情再多也要去送他!儿子再三劝我不必去;我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儿子买票,我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可我们的钱也不多了,只好忙着和他们讲价钱。可能那时儿子总觉得我说话不大漂亮,非要插嘴不可,但我也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他上车。我给他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他将我给他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我嘱咐他路上多加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他,以免他不能很好的料理自己。可他能明白我这一片苦心吗?
他说道:“爸爸,你走吧。”我往车外看了看,总觉得还缺点什么,突然想到儿子在路上还没有解渴食品,便对他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我虽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要费事些,可是给儿子买橘子还是我自己去吧。我走到铁道边,探身下去再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感到有些不容易。我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我走到月台的栅栏外的小摊旁买了一些又红又大的橘子。到火车这边时,儿子赶紧过来搀我,心中感到阵阵暖意。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他的皮大衣上。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儿子在路上也有可以解渴的吃食了,这下也放心了些。我下车后还是有些担心儿子,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他望着我走出去。我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他,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回去后我便很轻松的走了。
近几年来,儿子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更是一日不如一日。我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我看到家庭如此败落的情况,心里感到悲伤,自然无法控制自己,使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情感积聚在心里不得发泄,自然要发泄出来;家庭琐屑的事情也往往惹怒我。我待儿子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我也忘却他的不好,只是惦记着他,惦记着他的儿子。他北来后我写了一信给他,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