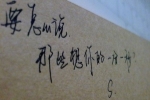不能过度执着的作文【一】
我,是一台电话。我被放在了客厅的桌子上。
我对我的主人十分有用,因为主人每天都要煲上好几个小时的电话粥,他对我爱不释手。
可是,我的命运在发生了转变。这一年,非典肆虐世界,人们一片恐慌。我的主人也是这样,对非典十分恐惧,谁要是说了个“非”字,他准会发半天抖。
一天,他的一个老朋友又给他来电话了,我朝天大喊:“零零……喂!零零……接电话了!零零……”主人跑来拎起话筒聊了起来。因为害怕非典,主人这几天连门都基本不出,所以一接到我的召唤,他就分外高兴,敞开了聊。
可是,当他听到对方的.声音时,脸色忽然变得很难看。他问对方:“你……怎么了……”“哦,我干咳、发热、全身酸痛,你说我这是怎么了?呵呵。”主人喉咙里挤出一丝怪异的声音,“啪”的一声,使劲地把我给挂上了,我好疼啊!主人可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哪!我好委屈……
主人在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边在焦急不安的念叨着:“非典……非典……电话传染非典怎么办……非典……”突然,他停下踱步,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似的,向我走来。
主人猛的一下把我的线拔了,吓了我一跳。他望着手中被拔下的线,长舒了一口气:“啊……这下好了,不用怕非典了!”主人在那儿高兴地说着,我只能无助地望着他……
其实,非典型性肺炎并不像我主人想象得那么可怕无视非典的危险固然可怕,但对非典的过度恐惧才是最可怕的,它会让没有非典的人患上比非典可怕十倍的“病”。只有了解非典,再加上我们的众志成城,才能永远对sars说:“no!”
不能过度执着的作文【二】
图上的内容是这样的:在一个的寒冷冬天,一个穿着裙子、带着还没满周岁婴儿的母亲。她急急地向车站走来,车站里人山人海,因为妇女矮小,刚排好队又被人挤出来。妇女向四周看了看,看到“母子上车处”,只有几个人在排队,她高兴极了。 小跑过去,走进一看,原来是几个强壮的男人,妇女小声抱怨:“这里不是母子上车处吗?为什么会来几个男人。”
妇女无奈,只好站在一旁。穿大衣的人偷偷地斜视了“母子上车处”的牌子,穿甲衣的人干脆就闭起眼睛,装作没看见,后面一个人比较矮,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好像是个教师的,还有一个扣着口罩,没把牌子当一回事。那妇女用乞求的眼神望了望那些男人,他们却不加理睬。看见这般情景,我的心象翻腾巨浪一样不能平静。那些男人是多么自私自利,不顾别人的感受,假装文盲。这让我想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记得是前几天,是县城圩日,在长寿风雨桥,我看见东桥头一个“少者乞丐”正在地上爬行,小腿用布裹着,背上捆绑纸箱,举着牌喊着“行行好,给点钱”。我走到西桥头又看见一个“老者乞丐”,也正在地上爬行,蓬头垢面,手上托着一个面盆,举牌向行人乞钱。路上,人来人往,装作没看见,也没有给钱,绕道走开。圩散了,人也散了,少者、老者乞丐拖着空空的纸箱、面盆,无奈地回家了。
我愿,这一切自私,任风,吹去。
我愿,这一切自私,随雨,溶化。
我愿,这一切自私,腾云,散失。
不能过度执着的作文【三】
父母总把自己全部的爱给予孩子。什么都可以比别人差,但对孩子的爱,一定要比过别人。过度的爱,就像溺爱。接近畸形的爱。看似很伟大,但溺爱过度就形成了一种环行模式。最著名的溺爱就是早些年林娟痴迷刘德华,父母就是以过度宠爱的方式来处理。为了林娟借钱,甚至卖房,然而这种举动并没有。圆了林娟见明星的.梦,更是声称为了女儿愿意卖掉自己的一个肾。通过这种荒料的过度溺爱举动,林娟应该一直生活在溺爱的环境下。在这种环形模式下,孩子成了不孝子。最受宠的孩子反而与父母成为敌人,或许小时候林娟的愿望,父母可以帮他完成,但帮助一个成年人实现愿望是很困难的事。古代猿人因自己动手才进化了手脚。林娟的父母在林娟小时候为林娟包办一切,使林娟已经形成父母代替自己来办事。父母不忍看林娟受到困难,这实际阻碍了林娟独立自主的实现梦想。
过度溺爱阻碍了孩子的独立探索,使孩子依赖父母的帮助,并且没有帮助就无法自己自主完成,当在此时其他正常的孩子在没有帮助时,在遇到挫折时,仍能靠自己完成愿望,而被溺爱的孩子是只能靠他人来实现愿望。就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过度溺爱使父母只能给鱼而不能授渔,而被溺爱的孩子只会吃鱼而不会捕鱼。至恰恰实现已无法实现他的目标,这个孩子的世界就会崩溃。
毕淑敏写过一篇文章《孩子,妈妈教你看病》。起初孩子也是在妈妈的溺爱下以至于如果没有爸妈就一直忍着病痛,但是毕淑敏作为母亲,他放手让孩子独立成长。而孩子虽然用了很长时间,但他依旧完成了看病的目标。儿童中的小鸭和小鸡在父母过度的宠溺下,已经没有意识去独立自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
在孩子成长中都必须经历自己独立面对生活,总有一天要离开父母远去航行,而父母并不是航行者本身,而是航行者指南针,那么就要停止过度溺爱,及时停止过度溺爱带来的过度阻碍。
不能过度执着的作文【四】
耳边响起儿时传唱的歌谣:“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船头……”其实,孤独,或者执着的又何止是月?
还记得第一次发现月亮会跟着我的脚步走的情景,先是惊讶,然后便是兴奋。一个人在自家门前的院子里迈着稚嫩的步伐,一次次地印证着,还火急火燎地匆匆跑回家把大人拖出来告诉他们这个惊天的秘密,嗔怪地问,为什么月亮老是跟着我。这又似乎只是昨天的事情。月如旧,温和、清淡娴雅,一如往年。
月承载着一个人、一个乡村,或者一个城市的秘密。
我真正地走进月光里,是一个夏日的夜晚。我刚刚从城市回到乡村,结束了两天异常紧张的考试,带着劫后逢生的忐忑踏入这片土地。天已经完全暗下来,月儿早已爬上树梢,内心澎湃着的属于城市的喧嚣早已被乡村的安宁覆盖。路上有几个和我一样的行人,均是拖着行李箱,背着书包,他们有着和我一样的倦容,在茫茫的月色下显得更加苍白无力。我判断他们和我来自同一个城市,但是不一定是同一所学校,就这样我们却不约而同地走在了一起,彼此沉默,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我走进村口的时候,就有一种莫名的\'窒息感,内心极度复杂,失落。没有人告诉我,我的家里正在发生着什么,又有什么是我始料未及的。总之,那天我披着月光走进家的时候,就发现很奇怪,一屋子的人围在正屋里,嘈杂和安静和谐共处。我的父亲就躺在凉床上,双眼微闭,脸色苍白如纸。我的母亲在一旁手足无措地低泣,神色灰暗,完全失了往日的神采。那些围观的人统统给我让路,站成两排,用同情的眼神盯着我。用几分钟了解了情况后我果断地拨打120,在颤抖中我的耳边传来一名女子的声音:你好,××救护中心,请讲。由于我一直在极度压抑着眼中的泪水,颤抖的声音,和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向她描述我所在的地理位置,费了很大的劲才让对方弄明白。哪个女子对我的断断续续的语言表现了极大的忍耐,或许这样的事情在她的眼里在平常不过。她甚至还安慰我,安顿好伤者,不要乱了阵脚,救护车半个小时之内到。
一通陌生的电话就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光亮。
我含着泪,像一只夜晚迷路乱窜的羔羊,不知东西,做着平时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事。用最快的速度找出家里的现金和存折,给父亲拿换洗衣物,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必须要带的呢,我不停地在房间里转圈,想到一样拿一样,身份证,户口本。我不知道住院办手续需要那些证件,就把我能想到的都带上。当我们到达市人民医院的时候,已是深夜,我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月光,皎洁如玉。
三个小时后,我又一次来到了这个城市。
急诊室里坐满了人,他们个个神色慌张,几个值班医生在一群家属的围问下显得有些不耐烦,语气冲得简直可以把人挡在一米之外。我胆战心惊地去挂号,然后排队,等候。我双手紧紧地捏着挂号的账单、病历本和找零的钱,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我竭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在这里,在城市的医院里我尽量不可以出丑,“扰乱军心。”只能再次望着窗外,看着圆盘似的月亮发出清幽、凄冷的光来,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月也和我一起悲哀。我拭去眼角的泪珠,看向急诊室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盯着我,带着无奈和仇视,好像是我扰乱了他们的心情一样。
终于轮到我了,医生给父亲查看伤势,手没轻没重地在父亲受伤的位置按压,看见父亲紧皱的眉头,我忍不住地求医生轻点。医生一脸的不悦和不屑,似乎在说,到底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紧接着,给父亲做一系列的检查。我跟在医生的后面,机械而被动,这里的一切我都无比的陌生,却又满是矛盾地对这里充满了好奇。
那个晚上,或者是说次日的凌晨,以父亲的输液而暂告一段落。月,似乎懂得人们的心理,悄然隐退了。我再一次望向窗外的时候,只剩下少许的星星散落在天空的角落,发出微弱的光线。我从口袋中掏出手机看时间,却是黑屏,没电,自动关机了。
迷糊中感到一丝光亮,朦胧地意识到天亮了。于是,立马站起身来,父亲已经醒了,一直看着我却没有说话。我用手简单地梳理了一下头发,便对他说,去打点水来给你擦洗,就飞也似地逃出了病房。我不知道怎么了,看着父亲就想流泪,怕忍不住会丢人,只好暂时离开父亲的视线。
就这样,我和父亲就在医院里,这个城市里“安顿”下来,过着不属于我们的生活。医院不停地催缴住院费、挂水费、营养费,和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每每有护士过来大声地叫道:“25床,缴费”,我都有种胆战心惊的颤抖和无奈。一次,我去住院部缴费的时候,看见护士在缴费单上漫不经心地划着或许连她自己都无法辨认的符号,一边还在和一旁的男士打情骂俏,说着属于他们那个阶段的黄色笑话。写好之后,机械地冒出一句:交多少?我战战兢兢地把手中都快捏出水来的五张纸币递给她说:先交五百吧。看着她那不屑的眼神,我心生厌恶,已经在心里痛骂成千上万遍了,只可惜她感觉不到。
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寄居者,她也并不例外。
城市的月光似乎更加清冷,夹杂着悲欢离合,穿过树叶的缝隙到达地面,斑驳的影子在风中跳跃,相互追逐,却什么也抓不到。医院里,每天都有人死去,重症病房门口总是会传来哭声,从一开始的嚎啕大哭,慢慢变成时断时续,然后是低泣,最后是完全失了声音。我不知道是哭哑了嗓子,还是认清了残酷的事实: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是留点气力给死者操办后事。总有围观者在事后议论这一家怎样怎样可怜,孩子小,担子重。我记得早上打水经过重症病房门口的时候,无意间瞥见那个病人,浑身插满了管子,无数个袋子挂在输液架上,只这么一会功夫人就没了。生命,在这里真的是微不足道,不断地有新的病人进来,也不断地有人离开,离开的人有的治愈回家疗养,有的却是和这个世界告别,永远不在了。
我不知道这个城市的秘密是什么,而承载这个秘密的月儿会不会和这个城市一样,深不可测?
乡村,或者城市。我一整个夏天就这么游走,像一尾鲤鱼,被炙热的太阳烤的通红,窒闷的气息纠缠得无力而乏味。在充满消毒水的病房里,我拿着笔一点一点地涂抹着我的高考志愿表,大学和梦想好像顿时变得遥不可及,我的所有动作似乎可笑到癫痫。没完没了的哭声、各个病房发出的痛苦***,好似一条条毒虫无时无刻侵蚀着我的骨髓,把焦灼的夏风弄得比冬日里的寒风还要凛冽。我的思想,在发霉、变质,最后像要当在大海里的帆船,失去了方向。
生活,真的就只能这样,如纸般脆弱么?我问月儿。
仍旧有月光从窗子射进,我闻到了腐旧的气息,现在的月儿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这样的光辉又要经过多少年才能到达地面呢?那么,是我多情了。固执地认为,月是通灵的,洞察人间一切,殊不知,是我自己执着地将自己的感受强加给了月儿。这个城市会有多少个人会和我一样,把秘密托付给月儿,我无法知道,也不知道在城市里“寄居”的人又多少,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种无奈的生活。
也许,只有月儿知道。月,始终温柔含蓄,赐予人们光和热,执着地开辟出一条条明朗的心路来。
不能过度执着的作文【五】
什么样的读者来信最让我哭笑不得,就是“点姐,我打算今晚就开始运动,但是我不知道运动前到底是应该吃个苹果好,还是喝点酸奶好,另外我去健身房要不要涂个隔离霜啊?一路上有很多灰尘,可是涂了隔离霜之后,会不会把毛孔堵住不能很好的排汗啊?运动完之后是不是要立即洗脸啊?可是洗完脸之后出门会不会被脏空气吹着了?…..点姐,运动真的好麻烦啊!”
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拧巴到眉毛打结的小姑娘,为了以上这些繁琐的问题,五脏翻江倒海半小时,最终的结果:还是不去运动了。
其实,无论你空腹或饱腹、隔离或裸脸,其带来的好处、伤害,都无法与实现运动的重要性相比,更何况,如此趋所有利、避所有害的好事儿,又有谁能够给你足够权威理想的理论根据呢?
我还曾目睹一位朋友在当当上购书,久久徘徊在5、6本之间无法拿定主意(我保证不是经济困窘。她头头是道地分析了每本书的优劣,细化到“如果我买了这本,好处是什么,遗憾是什么”,等到全部讲完之后,手一摊,撇着嘴问我,“我到底买不买了?”……
所以有时我更欣赏做事一根筋的人。每天拿出五成的时间思考就够了,因为剩下的还要留给行动。这样的人不会因为聪明而损失惨重。
其实就我的观察来讲,压根不动脑就扑上去三下五除二的人非常少,反倒是在脑子里滚来滚去一百遍,分析各种利弊可能,恨不得纠结到吐血前一秒,盼望着一个神明出来说一句,就这么做吧,我拿绳命给你保证没问题,然后才肯下手的人,比比皆是。
可是,活了这么多年,还没发现“人生压根没有任何保证“这回事吗?
“三思而后行”,到底要思多久?
自从我看到这句话之后,就把它抄了张小纸条,贴在了我家冰箱门上。每天路过,我就要想一想,万恶的大双子,你今天想的问题是够了,可你做的有多少?
坦诚地讲,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做计划、要走一步看三步的思维模式,真的也是一把双刃剑。被灌输的“凡事要三思而后行”、“谨言慎行”,其中的“度”其实非常难以把握。
于是,在每个人长大的过程中就碰上了这一段“成长剧痛期”,我们难以把握所学信条之中的分寸,于是所学所想与现实激烈碰撞带来了方方面面的疼痛。当迷茫的现状撞上野心勃勃的***,疼痛自然更加难耐。
我们很无助地发现,啃书的时候,只要我们把公式都记住了,难题都搞清了,就能考上个差不多的分数;不管多么另类奇怪的老师,都会信誓旦旦地给你一:只要你用功,就能考上好大学,就有一个好前途。
可是,当真正走入社会之后,我们面前所有的一者、同时也是保证者,全都不见了。就连一向苛刻的父母,也柔软下来,没有了高考这么凌冽的人生目标,我们仿佛只要有一份工作、能生存下去,就不错。
这时不满现状、性格里愿闯爱拼的人,就不免开始变得混沌,我的下一个目标在哪里?我努力就会有结果么?几条看似差不多的路我都想尝试,但只能走一条,有谁能够替我保证我不会后悔?
于是就有了无休止的绞尽脑汁和挠破皮的利弊分析,长此以往,我怀疑人的思维定势和行为记忆会控制你,在做大事小事之前,都要经历泥泞挣扎的“思前想后”和自我折磨。
而且,两种人最极致,一是读书多的,二是***大的。如果你读书又多,又野心勃勃,那祝你千万别抑郁了。
当然抑郁也是一件好事,不少人从抑郁的状态里走出来之后,都想明白了很多事情。有次我和一位好友在聊起“痛苦的思考”状态的时候,她说,现在她越来越不愿意将自己长久地放置于一种计划、斟酌、焦虑、不定的状态里了,想到什么,判断一下就开始着手,其他时候清清淡淡地不让自己胡思乱想。
“因为我知道,很多事情其实并不需要多么缜密的思考和斟酌,真的没那么严重,这只是我的惯性而已。而且我坚信,凭自己的判断力和智商,也压根不会作出多么离谱的选择。”
真的,除了升学、择业、婚姻、育儿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您格外操心,谨慎选择之外,日常生活中究竟有多少事情值得你思前想后,郁郁寡欢呢?
世上没什么事是被保证的
我感觉自己比以前成熟一些、也更轻松一些的一个标志是,我明白了一件事:nothingisguaranteed.(没有什么事是被保证的。
以前我大多的不爽和恐惧,都来源于对选择之后未知结局的担忧,我永远像一个悔棋不倦、在麻将桌上被人讨厌的弹簧手,恨不得来来回回地悔改。我总是希望自己做出最最正确的选择,绝对不能有误,这远远超出了完美主义的范畴。啧啧,完美主义是多么好听的一个词,我只能是病态到丑陋的完美主义者。
这不仅让我身边的人压力极大,当然折磨自己也更多。但可惜过了很多年之后,我发现如果有对错之论的话,我该选错的地方还是选错了,遗憾的地方也能写满一张纸,我并没有因为自己慎之又慎的神经质,而达到事事完美的皆大欢喜。
反倒是,很多本来说不定可以发出芽的种子,被我在思考之后摒弃了。由于不确定,所以也没播种。
若现在还能让神经质的我,再后悔一次,我选择后悔的是:我为何不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试一下,何苦把“试一下”的时间,都拿来苦思冥想了。
我更有切身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做你的担保人,除非上帝,因为没有人能用全视角来展望这个世界,并把未来三五十年间发生的事情提前透露给你。况且,有时保留一点命运留给你的神秘感,也蛮美的。干嘛非事事都要索要个明白?若真有人能告诉你,你咽气的\'时候有几套房子、有几个孩子、身边是谁、有多少票子,你真想知道?
况且,渴望看到确凿的结局,才肯付出,那和爱情里面斤斤计较、衡量再三、看到对方的真心才肯表露真情的自私鬼有什么区别?你对自己的人生也太不豪爽,太没诚意了!
老天爷,你啥时候给我一个男朋友,我跟他能不能不离婚?老天爷,我辛辛苦苦复习考研之后能不能在未来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老天爷,我天天运动累成狗,半年之后到底能不能瘦十斤?
就想说你一句:任谁都喜欢默默努力,心怀感激的孩子,你这么不可爱,老天爷凭啥回答你?水还没到,就问渠能不能成,你不光得罪了老天爷,还违反了自然规律。
所以,先做,别先索要承诺。有一万个细节决定你是否能如愿
日日手捧“思考”圣杯,为求一个完美结局而愁眉苦脸的人,一点也不性感。虽说思考永远是人最大的优势和进步的阶梯,但过度的思考也是人受困于情绪、招致痛苦的原因。苛刻的思考更会使一个人显得死板、沉重、了无生趣。
都说用深入的思考来指导行动,是非常明智的事。可当过度自我裹挟的思考,限制了你的行动,就太得不偿失了,毕竟,行动只是开始。
更多决定你是否能成功的因素,存在于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随时借助思考来调整航向、灵活变通,才是更重要的努力。
就好像有人把“领取结婚证”当作完美结局,而有些人却把“领取结婚证”当作战战兢兢的开始。婚姻幸不幸福,不在于你有没有选择结婚这件事,而在于你擅不擅于过好婚后的每一天。如果你是个废物,那么就算你干脆不结婚,也有可能是个失意的单身汉。
当我在家里呆坐十天,也根本想不清楚,应该先去哪个公司实习、尝试的时候,我灰头土脸迷茫得想跳楼。但当我最终随便选了一家,跑去上班的第3天,就遇到了一个碰巧懂行的同事,他跟我聊了一中午之后,就否定了我的另外几个选择——比我苦思冥想十天的结果轻松多了。
有时,你并不知道自己的哪一份积累,会在哪一个机会上为你争取致命的优势;你也根本不知道,在你广撒网的时候,会捞上来哪一种鱼。也许当你真的来到海边,看到一群一群捞鱼的人,然后突然顿悟,不想捞鱼了呢。
我在做Queen主义之前,不知道有多纠结。我不确定的问题不比我掉在地上的头发少。我不确定自己的潜力、不确定有没有人帮我、我甚至天天想象自己在拼尽全力以后摔得很惨。
但有一天,一个创业做的很棒的朋友,告诉我一句话:这世上真的有些事,是你以现在的视野所看不清楚的,你必须先走两步。
我现在特别庆幸我的开始,虽然未来仍是一片未知,但我每天的收获是可以垫底的,谁叫即便走错路也是满满的收获。
况且,想要真正地解决问题,首先,你得让问题先真实地暴露出来,而不是永远停留在设想。
是的,有些事需要先开枪,再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