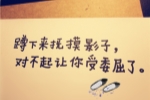在地下室怎么写作文【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念诞生和蜕化的历史,对他自己以及对读者们有着很大的决定意义。要说清这一问题只有一条途径:叙述自己的历史。《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正是这么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固然一直都在完成这一纲领,但却一直在用小说人物的虚构的姓名来加以掩饰。
在《地下室手记》的注释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手记的作者和手记本身一样都是虚构的”。而他自己的唯一任务就是描写“行将死亡的一代中的\'一个代表”。这种手法的作用却恰恰相反,因为读者一读便知,虚构的不是手记及其作者。而是注释。他所描写的地下室正是他自己的地下室。他害怕他所经历过的那些可怕情景,不得不创造了梅思金公爵、阿廖沙·卡拉马佐夫等一系列理想人物来抵抗。
有一些方法来区分正文和注释。例如,老套话一定是借用来的。另一种是根据叙述的形式:只要在对话中看到歇斯底里的发作、不自然的喊叫,就可以断定这是开始“注释”了。
但这些方法还不够精确,在解释整本小说的时候就可能出现错误。那么怎么办呢?办法就是:任意想像。如果读者猜出了寓意,那么这种任意想像就不再是随意的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憎恨自己过去的信念,而且唾弃它。他加入别林斯基小组时所相信的一切,后来一点也没有了。人们习惯把被推翻的偶像还看做上帝,把被保留下来的寺院看做教堂,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是这样,他诋毁过去所崇拜的一切。尼采说要重新评估一切价值,这是同一种过程。如果使人亲近的不是血缘、性格或生活背景,而是内部的一致,那么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必然是一对孪生兄弟。尼采用自己的作品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许多秘密。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爱预言,俄罗斯一定会把在那里被遗忘的博爱思想还给欧洲。他本人就是对欧洲人有影响的第一批欧洲人中的一个,然而又被渐渐遗忘。欧洲从俄国接受的第一个礼物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学”,也就是底下人及其变种——拉斯柯尔尼科夫们,卡拉马佐夫,基里洛夫们。命运最爱嘲笑凡人的理想和预言。
在地下室怎么写作文【二】
“但我当时还不知道,即便十五年后,我所想起的丽莎,依旧恰恰带着那一刻出现在脸上的那种可怜的、扭曲的、不必要的微笑。”
奇怪的是当我在读完后回顾整篇《地下室手记》,最为清晰的不是一张理应被想象得苦大仇深的地下室面孔,却是主人公在黑暗中点亮火柴,照见丽莎“受苦受难的目光”,仿佛那“不必要的微笑”确曾浮现在镜中我自己的脸上。这“不必要”精确得如此经络分明,带着同情、讨好的变味笑容被拒绝,是地位上的不必要,也是需求上的不必要:属于地下室的人并不真的需要一个微笑。或者不如说,他从来都不需要一个微笑,毕竟,“须知我写的是极其丑恶的真实。”
《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毫不避讳手记所展现出的人性丑陋,正如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写道:“您认为我是解放心灵、拯救灵魂、驱赶痛苦的人吗?许多人给我写信,但是我相信,我恐怕只能引起他们的失望和厌恶。”写作者深知诉诸笔端的这些信念指引的不是一条通往天堂之路,事实上,地下室人的丑陋如此真切,如此暴烈,以至于他那拒绝一切摧毁一切的冲动裹挟着读者去相信唯一真实的不是生活,不是幸福,而是苦难。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永恒的`追问:
“哪一个更好些——是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苦难?”
《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伊万被心底罪恶的告白逼得发疯,从他身体中分裂出的魔鬼嘲讽道:“因为苦难就是生活。没有苦难,生活还有什么乐趣?”而伊万无助地坦白,“我也在受苦遭罪,可我仍然不算活着。”伊万聪明精***外在几乎正是地下室人的一个理想形象,拥有可见的“高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本质上,他们无从和解的自我却深信自己无力抵抗,只能屈从于内心的恶。
地下室人的形象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形象,因为人只要存在,便永远为那存在之所在而焦虑。这种焦虑促使人的意识发出呐喊,促使个性反对理性,促使冲动抹除判断,对于那仿佛已经确信无疑的属于钟表里的一枚齿轮、管风琴上的一枚销钉的位置,对于那无法推翻的“二二得四”,以超越理智的渴望呐喊——“我是人”。地下室人过于清醒地认识到,“我尊重自己,是因为我自己身上至少还能够拥有懒惰”,这尊重是可悲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已再难找到身为独立个体更为积极的确证,但我们却无法否定这一尊重,因着这懒惰、这自主的堕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在为自己争取一种哪怕是无益的渴望的权利,以此证明自己的生活是谁占据着统治地位。
“须知我在这里并非崇尚苦难,也并非崇尚幸福。我主张……捍卫自己的任性,并且捍卫那在我需要时能为我的任性提供的保障。”
地下室人并不成熟。1864年,陷入债务纠纷、面对妻子和兄长相继去世的多重打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地下室手记》。与《死屋手记》不同,《地下室手记》更纯粹,但却更阴暗,仿佛是对从流放苦役中解脱后曾写下“至少,我已经生活过了;我痛苦,但我毕竟生活过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一番否定: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那活生生的生活现在究竟在哪里,它是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
但纪德却认为,《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涯的顶峰,“不行动的思想者”在地下室人身上寻找到他们逃不出的宿命。正如《地下室手记》全篇咬文嚼字的独白所彰显的,主人公只是倾诉,只是倒毒水——与言语相比,他的行动近乎愚蠢。他怀着异乎寻常的仇恨周密策划了对陌生军人的报复,而一切的结果只是两个人在大街上“扎扎实实地撞了一下”,于是主人公回到家里,“深感大仇已报”;他强行要求参加一场未被邀请的宴会,试图向一群过去的同学证明自己并不比他们卑微,却备受侮辱,以至于他坚信“我们将在黎明时决斗”,直到闹剧随着夜晚来临不了了之。
一切都是攻防,都是权力的游戏。在地下室人眼里,似乎没有他人,只有敌人。他在暗室中与丽莎的初遇就像是一场剑拔弩张的战争,从“怒形于色”,到“勃然大怒”再到“自卫”,到“粗鲁”,到“某种权威的口气”,到最后“你就等着吧”,仿佛人际交往只是你来我往的耍花招,只谈技巧,毫无真实。而在这种虚假、造作的交流中,他竟然还妄想着爱与被爱,妄想着情节发展将如某首备受他嘲讽的流行诗,奔向纯洁的爱带来的互相拯救。
“您有点……像是从书上搬来的。”
这几乎令人哑然失笑,丽莎不经意间说出了真相,地下室人的面具被戳破,露出他脱离真实生活、沉醉于精神世界的可悲嘴脸。不是不允许做梦,可怜的是连做个梦都如此傲慢的做梦之人。无怪乎到了最后仍然是必败的战争,那张躺在桌上被揉皱了的蓝色五卢布钞票,成为“卑劣的感伤灵魂”拒绝被侮辱、因而获得不比他卑下的尊严之证物。他已经无法再从旁人身上,找寻到自身生命的确证。
“爱就意味着虐待和精神上主宰一切。”
我们看到,地下室人对爱的定义已经只剩权力,只剩游戏。而这并不仅仅是他这一类人的危机。这已成为现代人的危机。伊格尔顿从《简·爱》中找到SM的身份替换,从《呼啸山庄》中挖掘自然与教化的权力斗争,感情沦为实用主义的道具,我不打算反驳他的理论工具,只是爱若仅是如此而已的事物,人的追求或者奋斗在价值体系之外便终究只能成为一场空梦。
而地下室人甚至否定价值。否定价值,否定人际关系,否定爱与同情,否定幸福与苦难,那到头来,“活生生的生活”究竟是什么?
“最主要和最珍贵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他笔下另一个从未停止的追问,提供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我在这样的时刻已开始意识到,我永远不能开始过真正的生活,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分寸,失去了对真正实在的事情的感觉。”
在早期的中篇小说《白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这样一个“幻想家”的形象,浪漫,明媚,但却早已隐隐有了“不行动的思想者”的雏形。他们是“在现实生活中拥有的太少”的那一类年轻人,“空虚而忧郁”,也正因为年轻,所以他的幻想还不会遭遇嘲讽,他甚至是迷人的,走在大街上,看见房屋、看见风景也是可爱的。他还没有遭遇到困扰地下室人终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也仍然相信着人际关系的可能性,相信即便注定只是一场幻象感情也有着存在和被表达的必要,于是他行动,虽然失败,但依然天真可爱。幻想家与地下室人最大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在于并未也不会对人际关系感到绝望,因为在幻想家的生命中,已经确确实实地有过那样一刻,那“够一个人受用整整一辈子”的“足足一分钟的欣悦”,那与所爱之人心意相通的时刻。在那一分钟的欣悦中,幻想家完成了与自我的和解。
这一瞬间是可以拯救世界的。《地下室手记》的最后,主人公追出门去,丽莎却早已消失在雪中。彼时,“万籁俱寂,大雪漫天,朵朵雪花几乎垂直地坠落地面”,却令人想起乔伊斯《死者》那无声的结尾,“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落下……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身上”。肩负着生命中、生活中“不堪承受之重”,所有人奔向那唯一且共同的归宿。随身携带着对那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的一瞬的怀念,我们奔向永恒。
“我永远、永远也不会麻木不仁地回忆起这一时刻。”
在地下室怎么写作文【三】
“但我当时还不知道,即便十五年后,我所想起的丽莎,依旧恰恰带着那一刻出现在脸上的那种可怜的、扭曲的、不必要的微笑。”
奇怪的是当我在读完后回顾整篇《地下室手记》,最为清晰的不是一张理应被想象得苦大仇深的地下室面孔,却是主人公在黑暗中点亮火柴,照见丽莎“受苦受难的目光”,仿佛那“不必要的微笑”确曾浮现在镜中我自己的脸上。这“不必要”精确得如此经络分明,带着同情、讨好的变味笑容被拒绝,是地位上的不必要,也是需求上的不必要:属于地下室的人并不真的需要一个微笑。或者不如说,他从来都不需要一个微笑,毕竟,“须知我写的是极其丑恶的真实。”
《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毫不避讳手记所展现出的人性丑陋,正如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写道:“您认为我是解放心灵、拯救灵魂、驱赶痛苦的人吗?许多人给我写信,但是我相信,我恐怕只能引起他们的失望和厌恶。”写作者深知诉诸笔端的这些信念指引的不是一条通往天堂之路,事实上,地下室人的丑陋如此真切,如此暴烈,以至于他那拒绝一切摧毁一切的冲动裹挟着读者去相信唯一真实的不是生活,不是幸福,而是苦难。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永恒的追问:
“哪一个更好些——是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苦难?”
《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伊万被心底罪恶的告白逼得发疯,从他身体中分裂出的魔鬼嘲讽道:“因为苦难就是生活。没有苦难,生活还有什么乐趣?”而伊万无助地坦白,“我也在受苦遭罪,可我仍然不算活着。”伊万聪明精***外在几乎正是地下室人的一个理想形象,拥有可见的“高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本质上,他们无从和解的自我却深信自己无力抵抗,只能屈从于内心的恶。
地下室人的形象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形象,因为人只要存在,便永远为那存在之所在而焦虑。这种焦虑促使人的意识发出呐喊,促使个性反对理性,促使冲动抹除判断,对于那仿佛已经确信无疑的属于钟表里的一枚齿轮、管风琴上的一枚销钉的位置,对于那无法推翻的\'“二二得四”,以超越理智的渴望呐喊——“我是人”。地下室人过于清醒地认识到,“我尊重自己,是因为我自己身上至少还能够拥有懒惰”,这尊重是可悲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已再难找到身为独立个体更为积极的确证,但我们却无法否定这一尊重,因着这懒惰、这自主的堕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在为自己争取一种哪怕是无益的渴望的权利,以此证明自己的生活是谁占据着统治地位。
“须知我在这里并非崇尚苦难,也并非崇尚幸福。我主张……捍卫自己的任性,并且捍卫那在我需要时能为我的任性提供的保障。”
地下室人并不成熟。1864年,陷入债务纠纷、面对妻子和兄长相继去世的多重打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地下室手记》。与《死屋手记》不同,《地下室手记》更纯粹,但却更阴暗,仿佛是对从流放苦役中解脱后曾写下“至少,我已经生活过了;我痛苦,但我毕竟生活过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一番否定: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那活生生的生活现在究竟在哪里,它是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
但纪德却认为,《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涯的顶峰,“不行动的思想者”在地下室人身上寻找到他们逃不出的宿命。正如《地下室手记》全篇咬文嚼字的独白所彰显的,主人公只是倾诉,只是倒毒水——与言语相比,他的行动近乎愚蠢。他怀着异乎寻常的仇恨周密策划了对陌生军人的报复,而一切的结果只是两个人在大街上“扎扎实实地撞了一下”,于是主人公回到家里,“深感大仇已报”;他强行要求参加一场未被邀请的宴会,试图向一群过去的同学证明自己并不比他们卑微,却备受侮辱,以至于他坚信“我们将在黎明时决斗”,直到闹剧随着夜晚来临不了了之。
一切都是攻防,都是权力的`游戏。在地下室人眼里,似乎没有他人,只有敌人。他在暗室中与丽莎的初遇就像是一场剑拔弩张的战争,从“怒形于色”,到“勃然大怒”再到“自卫”,到“粗鲁”,到“某种权威的口气”,到最后“你就等着吧”,仿佛人际交往只是你来我往的耍花招,只谈技巧,毫无真实。而在这种虚假、造作的交流中,他竟然还妄想着爱与被爱,妄想着情节发展将如某首备受他嘲讽的流行诗,奔向纯洁的爱带来的互相拯救。
“您有点……像是从书上搬来的。”
这几乎令人哑然失笑,丽莎不经意间说出了真相,地下室人的面具被戳破,露出他脱离真实生活、沉醉于精神世界的可悲嘴脸。不是不允许做梦,可怜的是连做个梦都如此傲慢的做梦之人。无怪乎到了最后仍然是必败的战争,那张躺在桌上被揉皱了的蓝色五卢布钞票,成为“卑劣的感伤灵魂”拒绝被侮辱、因而获得不比他卑下的尊严之证物。他已经无法再从旁人身上,找寻到自身生命的确证。
“爱就意味着虐待和精神上主宰一切。”
我们看到,地下室人对爱的定义已经只剩权力,只剩游戏。而这并不仅仅是他这一类人的危机。这已成为现代人的危机。伊格尔顿从《简·爱》中找到SM的身份替换,从《呼啸山庄》中挖掘自然与教化的权力斗争,感情沦为实用主义的道具,我不打算反驳他的理论工具,只是爱若仅是如此而已的事物,人的追求或者奋斗在价值体系之外便终究只能成为一场空梦。
而地下室人甚至否定价值。否定价值,否定人际关系,否定爱与同情,否定幸福与苦难,那到头来,“活生生的生活”究竟是什么?
“最主要和最珍贵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他笔下另一个从未停止的追问,提供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我在这样的时刻已开始意识到,我永远不能开始过真正的生活,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分寸,失去了对真正实在的事情的感觉。”
在早期的中篇小说《白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这样一个“幻想家”的形象,浪漫,明媚,但却早已隐隐有了“不行动的思想者”的雏形。他们是“在现实生活中拥有的太少”的那一类年轻人,“空虚而忧郁”,也正因为年轻,所以他的幻想还不会遭遇嘲讽,他甚至是迷人的,走在大街上,看见房屋、看见风景也是可爱的。他还没有遭遇到困扰地下室人终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也仍然相信着人际关系的可能性,相信即便注定只是一场幻象感情也有着存在和被表达的必要,于是他行动,虽然失败,但依然天真可爱。幻想家与地下室人最大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在于并未也不会对人际关系感到绝望,因为在幻想家的生命中,已经确确实实地有过那样一刻,那“够一个人受用整整一辈子”的“足足一分钟的欣悦”,那与所爱之人心意相通的时刻。在那一分钟的欣悦中,幻想家完成了与自我的和解。
这一瞬间是可以拯救世界的。《地下室手记》的最后,主人公追出门去,丽莎却早已消失在雪中。彼时,“万籁俱寂,大雪漫天,朵朵雪花几乎垂直地坠落地面”,却令人想起乔伊斯《死者》那无声的结尾,“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落下……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身上”。肩负着生命中、生活中“不堪承受之重”,所有人奔向那唯一且共同的归宿。随身携带着对那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的一瞬的怀念,我们奔向永恒。
“我永远、永远也不会麻木不仁地回忆起这一时刻。”
在地下室怎么写作文【四】
但我当时还不知道,即便十五年后,我所想起的丽莎,依旧恰恰带着那一刻出现在脸上的那种可怜的、扭曲的、不必要的微笑。”
奇怪的是当我在读完后回顾整篇《地下室手记》,最为清晰的不是一张理应被想象得苦大仇深的地下室面孔,却是主人公在黑暗中点亮火柴,照见丽莎“受苦受难的目光”,仿佛那“不必要的微笑”确曾浮现在镜中我自己的脸上。这“不必要”精确得如此经络分明,带着同情、讨好的变味笑容被拒绝,是地位上的不必要,也是需求上的不必要:属于地下室的人并不真的需要一个微笑。或者不如说,他从来都不需要一个微笑,毕竟,“须知我写的是极其丑恶的真实。”
《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毫不避讳手记所展现出的人性丑陋,正如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写道:“您认为我是解放心灵、拯救灵魂、驱赶痛苦的人吗?许多人给我写信,但是我相信,我恐怕只能引起他们的失望和厌恶。”写作者深知诉诸笔端的这些信念指引的不是一条通往天堂之路,事实上,地下室人的丑陋如此真切,如此暴烈,以至于他那拒绝一切摧毁一切的冲动裹挟着读者去相信唯一真实的不是生活,不是幸福,而是苦难。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永恒的追问:
“哪一个更好些——是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苦难?”
《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伊万被心底罪恶的告白逼得发疯,从他身体中分裂出的魔鬼嘲讽道:“因为苦难就是生活。没有苦难,生活还有什么乐趣?”而伊万无助地坦白,“我也在受苦遭罪,可我仍然不算活着。”伊万聪明精***外在几乎正是地下室人的一个理想形象,拥有可见的“高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本质上,他们无从和解的自我却深信自己无力抵抗,只能屈从于内心的恶。
地下室人的形象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形象,因为人只要存在,便永远为那存在之所在而焦虑。这种焦虑促使人的意识发出呐喊,促使个性反对理性,促使冲动抹除判断,对于那仿佛已经确信无疑的属于钟表里的一枚齿轮、管风琴上的一枚销钉的位置,对于那无法推翻的“二二得四”,以超越理智的渴望呐喊——“我是人”。地下室人过于清醒地认识到,“我尊重自己,是因为我自己身上至少还能够拥有懒惰”,这尊重是可悲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已再难找到身为独立个体更为积极的确证,但我们却无法否定这一尊重,因着这懒惰、这自主的堕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在为自己争取一种哪怕是无益的渴望的权利,以此证明自己的生活是谁占据着统治地位。
“须知我在这里并非崇尚苦难,也并非崇尚幸福。我主张……捍卫自己的任性,并且捍卫那在我需要时能为我的任性提供的保障。”
地下室人并不成熟。1864年,陷入债务纠纷、面对妻子和兄长相继去世的多重打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地下室手记》。与《死屋手记》不同,《地下室手记》更纯粹,但却更阴暗,仿佛是对从流放苦役中解脱后曾写下“至少,我已经生活过了;我痛苦,但我毕竟生活过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一番否定: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那活生生的生活现在究竟在哪里,它是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
但纪德却认为,《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涯的顶峰,“不行动的思想者”在地下室人身上寻找到他们逃不出的宿命。正如《地下室手记》全篇咬文嚼字的独白所彰显的,主人公只是倾诉,只是倒毒水——与言语相比,他的行动近乎愚蠢。他怀着异乎寻常的仇恨周密策划了对陌生军人的报复,而一切的结果只是两个人在大街上“扎扎实实地撞了一下”,于是主人公回到家里,“深感大仇已报”;他强行要求参加一场未被邀请的宴会,试图向一群过去的同学证明自己并不比他们卑微,却备受侮辱,以至于他坚信“我们将在黎明时决斗”,直到闹剧随着夜晚来临不了了之。
一切都是攻防,都是权力的`游戏。在地下室人眼里,似乎没有他人,只有敌人。他在暗室中与丽莎的初遇就像是一场剑拔弩张的战争,从“怒形于色”,到“勃然大怒”再到“自卫”,到“粗鲁”,到“某种权威的口气”,到最后“你就等着吧”,仿佛人际交往只是你来我往的耍花招,只谈技巧,毫无真实。而在这种虚假、造作的交流中,他竟然还妄想着爱与被爱,妄想着情节发展将如某首备受他嘲讽的.流行诗,奔向纯洁的爱带来的互相拯救。
“您有点……像是从书上搬来的。”
这几乎令人哑然失笑,丽莎不经意间说出了真相,地下室人的面具被戳破,露出他脱离真实生活、沉醉于精神世界的可悲嘴脸。不是不允许做梦,可怜的是连做个梦都如此傲慢的做梦之人。无怪乎到了最后仍然是必败的战争,那张躺在桌上被揉皱了的蓝色五卢布钞票,成为“卑劣的感伤灵魂”拒绝被侮辱、因而获得不比他卑下的尊严之证物。他已经无法再从旁人身上,找寻到自身生命的确证。
“爱就意味着虐待和精神上主宰一切。”
我们看到,地下室人对爱的定义已经只剩权力,只剩游戏。而这并不仅仅是他这一类人的危机。这已成为现代人的危机。伊格尔顿从《简·爱》中找到SM的身份替换,从《呼啸山庄》中挖掘自然与教化的权力斗争,感情沦为实用主义的道具,我不打算反驳他的理论工具,只是爱若仅是如此而已的事物,人的追求或者奋斗在价值体系之外便终究只能成为一场空梦。
而地下室人甚至否定价值。否定价值,否定人际关系,否定爱与同情,否定幸福与苦难,那到头来,“活生生的生活”究竟是什么?
“最主要和最珍贵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他笔下另一个从未停止的追问,提供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我在这样的时刻已开始意识到,我永远不能开始过真正的生活,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分寸,失去了对真正实在的事情的感觉。”
在早期的中篇小说《白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这样一个“幻想家”的形象,浪漫,明媚,但却早已隐隐有了“不行动的思想者”的雏形。他们是“在现实生活中拥有的太少”的那一类年轻人,“空虚而忧郁”,也正因为年轻,所以他的幻想还不会遭遇嘲讽,他甚至是迷人的,走在大街上,看见房屋、看见风景也是可爱的。他还没有遭遇到困扰地下室人终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也仍然相信着人际关系的可能性,相信即便注定只是一场幻象感情也有着存在和被表达的必要,于是他行动,虽然失败,但依然天真可爱。幻想家与地下室人最大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在于并未也不会对人际关系感到绝望,因为在幻想家的生命中,已经确确实实地有过那样一刻,那“够一个人受用整整一辈子”的“足足一分钟的欣悦”,那与所爱之人心意相通的时刻。在那一分钟的欣悦中,幻想家完成了与自我的和解。
这一瞬间是可以拯救世界的。《地下室手记》的最后,主人公追出门去,丽莎却早已消失在雪中。彼时,“万籁俱寂,大雪漫天,朵朵雪花几乎垂直地坠落地面”,却令人想起乔伊斯《死者》那无声的结尾,“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落下……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身上”。肩负着生命中、生活中“不堪承受之重”,所有人奔向那唯一且共同的归宿。随身携带着对那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的一瞬的怀念,我们奔向永恒。
“我永远、永远也不会麻木不仁地回忆起这一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