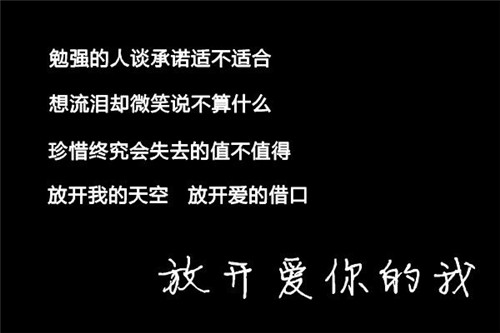
关于秋思的想象作文400字【一】
又到了秋天,沙沙沙,一片片的落叶飘到了地上。张籍独自一人走在洛阳街头,满眼却是故乡的幻影。在回家的路上,闻到了炒菜的香味,仔细一闻,仿佛闻到了母亲做的清蒸鱼时的熟悉味道。叹了口气后,满面愁容的,张籍接着往前走去,却幸运的偶遇了一位老乡,老乡说他明日就要回家了,张籍一听高兴坏了,马上就跑回家写家书。
张籍说:“我该写什么呢?怎么才能写好呢?”
我只有五六行,可是我有很多话要说,比如我要和父母说:“爸妈我爱你们,你们不要为我操碎了心,我现在过得很好。”
我还要和朋友说:“兄弟,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喝茶、一起写诗……”
十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张籍还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写好?甚至,想得都忘记了吃饭。张籍一想就是一天,他绞尽脑汁的想,可是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写好?终于在一天的清晨张籍想到了,真不容易啊!
他把那封信交给了老乡,就当老乡要走的时候,张籍,还要再看一眼,看看自己想的都写了吗?
最后,才依不舍的把那封信交给了老乡。
关于秋思的想象作文400字【二】
秋风瑟瑟,树叶黄了,草儿枯了,大树上的叶子化为千万朵蝴蝶飘飘悠悠地飞落而下,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枯黄的新世界,扩写《秋思》作文700字。诗人站在洛阳城中,秋风忽然乍起扑面而来,对家乡魂牵梦索的诗人凝望着蓝天,想起了故园,心中不由得泛起一阵阵酸楚:啊!离开故园有多久了?秋天果子丰收,正是与家人共享美好时光的日子......
诗人想写一封家书,给远在千里的亲人。只见诗人来到书房铺开信纸,提起毛笔,千言万语立刻涌上心头:儿女可好?兄.姐事可顺利?父母身体可好......面对眼中那洁白的纸,作者难以发挥,手中那笔似乎有千斤重。
时间流逝地很快,一分,一秒,一时......诗人费了好大功夫终于写好了,又长长的叹息,担心由于太匆忙,有些重要的话没有说完,于是,诗人反复的读,一字不漏地读。
· 第二天,诗人早早的起了床,百家书跌的工工整整,丝毫没有皱纹,像捧着宝贝似的把家书递给信使,还特地吩咐信使:“此家书一定要你亲手交给我家岳父大人!”信使接过家书放进包袱,诗人又一次提醒:“一定啊......!”
· 正当信使准备出发时,诗人突然有急促的大叫:“等等!等等!”信使急忙赶回来到诗人面前,用疑惑的眼神望着诗人:“有什么事吗?”诗人用双眼恳切的注视着信使说:“让我看看有什么忘记写了?”接着,信使从包袱里拿出家书递给诗人,诗人又一次打开家书,瞪大眼睛,看看家书,又从头到尾津津有味的读了好几次,最后发现没什么错误后,便不好意思地将家书还给信使,满怀歉意的说:“对不起,打佬您上路了!”信使很同情他,便安慰他说:“请您放心吧,这份家书我一定会亲手交给你的岳父大人,并告诉他您的心意!”说完,信使把家书放回包袱,跨上马,拽紧缰绳,绝尘而去。
· 洛阳城门只有诗人独自站在那,望着远去的信使,直至看不见人影为止,才肯默默离去......
关于秋思的想象作文400字【三】
在一个秋风瑟瑟的日子里,客居在洛阳城里的我,抬起头,望着窗外,看到忽如其来的秋风,将一片片掉落在地上的、黄黄的树叶卷了起来,黄叶就这样被带到别处。我写了封信。
正在这时,我瞄了一眼街头,发现自己的老乡正站在那儿,我赶紧出门迎接,并和他聊了起来,聊着聊着,我忽然想起了那封信,便问到:“老乡,是否回去?”他点了点头,问:“您也回去?”我摇头说:“我不能回去,在洛阳,我还有点儿事没办完。”说着,拿出那封信‘“这封信,您替我给我爸妈。”他点点头,正要走,我又叫住了他:“老乡,等一下,嗯——我那封信能不能还给我一下。”老乡很奇怪,但还是将那封信还给了我。我再一次拆开信查看了一遍,怕匆匆写的信没能把所有的意思表达出来。
我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将信郑重地交给我的老乡
关于秋思的想象作文400字【四】
我慢慢走在夕阳下,太阳的余辉把我孤独的影子拉得斜长。如今已是深秋,我孤身一人,骑着一匹嶙峋瘦马,
马儿伴随着我漂泊它乡已经多日,它也渐渐瘦了下来,再没有往日的健壮与活力,一阵西风吹来,拂动我的衣袖,把我的思绪拉到眼前。
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片凄凉,一如我的心境。一棵老树,一根枯藤。老树看起来疲劳乏力,如同正在慢慢衰竭的老人,似乎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随时会倒下。几根枯藤无力地缠绕着大树,发出哀伤的***,那扭曲着的打在树干上的结仿佛也打在我的心中,枯藤无力地缠绕在老树的枯干上,一种莫名的伤感萦绕于我心头。
“哇!哇!呱!呱!”一阵沙哑的鸣叫掠过耳畔,在冷冽的秋风中远去。那是一只乌鸦,它一定也老了,老眼昏花。它是不是与老树经历过同样的沧桑?它是不是对这晚景有着无限的感伤与惆怅?它能找到夜间的归宿么?
四周并无市俗的喧闹,一座小桥横跨在溪水的两岸,流水从远古流来,好像倾诉着无尽的悲伤。它的歌声令人心碎,如同一个游子的低吟。走过小桥,抬起头,忽见前面隐约有个小村庄,我不禁加快了脚步。炊烟飘渺,如同老母的思绪漫无着落。一片安静祥与的景象,这情景卷起了我深深的思乡之情,在外漂泊数载,未回过家乡,怎能不思念?一切都静了。
嬉耍了一天的孩童此刻该回家了吧?在温馨的屋中,早已摆好了饭菜正等着他们。而我,这断肠人,却仍黯然失神地独自漂泊在天涯。
关于秋思的想象作文400字【五】
他,二十六岁,一个进取的苏州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考中进士,成为一名官员,五十一岁时,被任命守卫西北边疆,防御西夏军侵扰,为期四年。他,一个崇尚完美的政治家,锐意革新,砥砺自律。
在戍边四年中的一个秋天的傍晚,他彳亍在边塞办事处(今陕西延安)的旷地上,亲临这荒远空阔的大西北,这呼呼凛冽的西北风,这秃山枯草的肃***景象,毕竟与家乡的流觞曲水不同。
他,塑像一般,凝望天穹中自由舒展尽意盘舞的雁群。如止水的心绪被啾啾欢鸣声撩拨着。终于,雁阵坚定不移地南飞了,要到避寒胜地衡阳的雁回塔那里过冬。他朝雁友消逝的方向迈了几步,眼睛里充满着光亮的渴望。
他认为城头上传来的号角声里夹带着挣扎的悲凉,仿佛四周的营房、城墙、野兽、山群、幽灵天籁、地籁、人籁都随之而响起来。
他遥望像屏障一样的山峰连绵起伏,稳固的长城跌宕延伸,炊烟清淡上浮,鹅黄的红日悬挂在云纱乌带间,禁不住地吟唱道:一片孤城万仞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最后一抹霞光也收敛了,城门也关闭了,这一天又结束了。
夜幕降临,他踱回寝室,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又喝了几盅,慢慢地心口暖和起来,心里想得也多了。他浓眉紧皱:还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家才最温馨最舒适,妻子儿女盼望着自己平平安安,也希望我能建立军功,再创辉煌他猛一捶桌面,目视窗外:耻辱哇,耻辱!没能像汉代大将窦宪那样领兵追击北单于于三千里之外,并在那里的燕然山上的一个巨石上刻文记功,荣耀而返。我,我有何德何能上报皇恩下安黎民近慰亲友?那么回家后又怎么办呢?老大不小的年纪了:五十多了炯然的眼睛里的攻无不克的光芒冷峻地逼射前方。
静夜深沉,羌笛悠悠,似断又续,那位长笛手一定也在思念亲人。清明的月辉倾泄在如浴的大地上,冻霜越发冰冷了。
他扶着窗框,一切静谧得像生铁一般。寂寥的时空凝固了。
一缕白发飘拂在苍老的面颊前,轻轻地又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