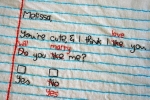109字作文语文【一】
今天是个令人激动的日子,因为在今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们乘坐宇宙飞船登上那令人神往的月球。
“3、2、1发射!”随着倒计时结束,火箭“轰”的一声发射出去,搭载着我们向月球奔去。飞船像一叶孤舟在太空中缓缓行驶,我们透过太空舱望着美丽的月球,它散发着淡淡的银光,我们仿佛看见了嫦娥在向我们招手。怀揣着期待的心情,飞船平稳地降落在月球上,我们兴奋地向地面中心报告:我们已安全抵达月球,我们将出舱与月球拉一次亲密接触!我们换上厚重的出舱服,慢慢地步出登月舱,踏在月面柔软的细小颗粒上,这感觉真像踩在地球的海滩上!说到地球,我们慢慢转身,在茫茫宇宙中搜寻着可爱的地球。啊,我找到了!那个蔚蓝的星球在宇宙中是多么的耀眼啊!那就是我们美丽的地球母亲!
在月球上做任何运动感觉都与在地球上做的感觉不一样。在地球上跑步只需几秒的距离在月球上跑却要用十几分钟来完成。不用说,跳远则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跳高是一个特例。你只要稍稍一用力、微微一蹬腿,你就能跳出让你意想不到的高度!
月球的表面到处都是一些坑坑洼洼的环形山。放眼望去,荒凉一片。但这片荒凉的地方也许将成为我们未来的家园。地球遭到人类无尽摧残已快承受不住。
采集了月壤和月岩的样品后,插上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我们即将搭乘飞船离开。真舍不得这片徒弟,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109字作文语文【二】
1.本体论的提问与构成论的回答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⑤[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0.
⑥[英]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391.
109字作文语文【三】
我们是小水滴,我们的家是大海.那儿有可爱的鱼儿,碧绿的水草,还有美丽的珊瑚! 一天,空中飞来一群大雁,向我们招呼:\"小水滴,快上来,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大雁姐姐,我们没有翅膀,怎么飞起来呀?” “你们可以请太阳公公帮帮忙嘛!”大雁姐姐说着,就急匆匆的飞走了。
第二天,太阳公公刚起身,我们大伙说:“太阳公公,我们要去旅行,可是没有翅膀,请你帮个忙吧!” 太阳公公点点头,微微笑。太阳公公升起来,放射出万道金光,照的我们睁不开眼,浑身暖烘烘的。不一会儿,我们的身体变轻了,慢慢的离开了大海,向空中飞去。大家快乐的叫起来:”我们长翅膀啦!我们长翅膀啦!”原来,我们都变成水蒸气了。
飞呀飞呀,我们觉的有点冷了。我们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紧紧的抱在一起,越抱越紧。一会儿,都变成了一颗颗很细很细的小水滴。风爷爷带着我们在空中飘来飘去,人们把我们大伙叫做白云。
啊呀,我们的身体怎么这么沉,越飞越累,越飞越慢,都有点飞不动了。过了好一会,我们想,到大地上玩玩多好呀!风爷爷好象猜到了我们的心思。”呼啦~呼啦~”刮起风来。
这时,我们里面有些大胖子,冷的缩成一团,又变成了小水滴,还来不及和我们告别就落下去了。只听见地上的小娃娃们欢呼起来,”下雨了!下雨了!”
大伙排着队又流进了大海。
109字作文语文【四】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以为近几十年来的作家都是一些没真本事的人,创作的作品也都没什么水平,及不上前人。我想这样的想法肯定不是基于我低端的水平能对那些作品有所客观正确地评价。毕竟在这个信息化社会中,别人的观点总能潜移默化的影响你。而近来读过路遥先生的大作《平凡的世界》后,才明白“精于此者,大有人在”是为何意。我也在领略作品艺术美的同时,也对先生起了深深地敬佩之情。能写出这样作品的人,怎样赞美都不为过吧!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平凡的世界》在很多地方都引起了我的共鸣,并深为感动。 首先是少平放弃在砖厂。农田帮助家人干活,过平稳的生活。独自一人去黄原城揽活的事。当时的他二十一。二岁,读过许多书,知道外面有一个广阔的世界,不甘愿在父亲与哥哥的下面做着既定的一些事务,如牛马一般。这不是说他想当家做主,他的内心是非常尊敬父兄的,他渴望的是去外面的世界闯荡。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泥泞难行,他都渴望前往。天地广阔,总不能做一只坐井观天的青蛙。我觉得驱使他前行的应该是他内心深处一种属于男人的尊严。
其次是润生辞职务农的事,当时村里一队实行了包产到户的政策,两户人家一组。润生的父亲,也就是大队书记田福堂因年事较高。身体又不好。兼之出席会议,没怎么干过农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教师的的润生毅然辞去教师的职务找到了队长孙少安和队员田海民。他知道父亲从小疼他,小时候就没让自己干过农活,现在必然会反对他,用自己剩存的体力换他的安宁。舒适。可是他更舍不得父亲受苦啊,他已经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啦。记得当时是这样描写的:润生对他俩说明自己替父务农的来意后,他俩很是理解,因为他们记得当年自己也和润生一样,意识到了对家庭的责任,并勇敢的承担起来了,而后海民欣慰地答应自己与润生组队。润生担起了他的责任,而我们或许还差了些吧!
最后想说的是作品中对爱情的歌颂,其中两次竟让我留下了泪。第一处是兰花和王满银的一段描写:王满银已经累得象散了骨头架;一绺头发聋拉在汗迹斑斑的额头上,手里拉着四岁的女儿猫蛋,松松垮垮地走着。不过,终于释放回来了,他脸上带着说不出的轻松和愉快,一路走,一路嘴里还哼哼唧唧吟着信天游小曲。兰花把两岁的儿子狗蛋抱在自己热烘烘的胸脯里,跟在她的二流子男人身边,也喜得眉开眼笑。半路上,兰花心疼地对男人说:“家里还有六颗鸡蛋,我回去就煮!你和猫蛋狗蛋一人两个!”王满银高兴得嘴一咧,竟然放开声唱了两段子信天游——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莹莹彩,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五谷里(那个)田苗子,唯有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那个)兰花花好……兰花脸涨得通红,跑过去用她那老茧手在王满银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王满银脖子一缩,眼一瞪,嬉皮笑脸地把舌头一吐——他这副鬼样子把两个孩子逗得直笑……第二处是秀英与少安的一段描写:少安和秀莲正准备回家吃饭,书记田福堂突然来到饲养院他们的新房。他拿来两块杭州出的锦花缎被面,说是润叶今天上午捎回来的,让他把这礼物转送给新婚的少安夫妇。田福堂把润叶的礼物放下,就告辞走了。秀莲马上奇怪地问丈夫:“润叶是个什么人,怎给咱送这么重的礼物?”少安尽量轻淡地说:“她是刚来的田大叔的女儿,她和我小时候同过学……”“肯定和你相好过!要不送这么贵的东西?”秀莲敏感地追问。少安承认说:“是相好过……”秀莲突然不言语了,背过身把头低下抠起了手指头。少安一看她这样,就很快转到她面前,开玩笑说:“你们山西人真爱吃醋!”秀莲反而冲动地扑在他怀里,哭了,说:“你再不能和她相好了!”少安手在她头上拍了拍,说:“人家是个干部,在县城工作着哩!”秀莲一听送被面的润叶是个干部,马上揩去脸上的泪水,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她就放心了——一个女干部怎么可能爱她的农民丈夫呢!我想这般朴实真切的感情在当今社会中是没有的,但人总是可以有这样的感情的。记得有句佛语是这样说的:“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尊佛,只是许多人未曾开启而已。”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对爱情的歌颂永远不会落伍。
经典总会流传,当地球绕这太阳又转过许多圈后,在某一个书店的角落里,总还会有读者会为经典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