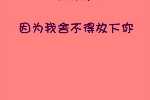放学以后一年级作文【一】
明天开始,我们就不能再上法语课了,这个噩耗对于大家来说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教室里鸦雀无声,隐约能听见几声嘤泣。韩麦尔先生迈着沉重的\'步伐上了楼,高大的背影显得佝偻而憔悴,我缓缓地将法语书一本本塞地书包,双腿似乎灌了铅,踌躇地走出教室。天色暗了下来,要下雨了,天地间仿佛蒙上了一层黑幕,我留恋地回望这美丽的校园,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大街上出奇的安静,行人稀少。铁匠华希特此时正和徒弟匆忙地收拾着行李,准备远离这片丢失的土地,只听见他边收拾边悲悯地抱怨:“这儿以后是普鲁士人的天下了,哪能容得下我们,指不定哪天还是会撵我们走,还不如自己走得远远的。”唉,哀莫大于心死,我抽答了一下,鼻子酸酸的。
天空中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仿佛在诉说着亡国的悲痛和对侵略者的仇恨。画眉依旧蹲在那棵老树上,似乎也很不愉快,尖厉的叫声好象也在控诉普鲁士人的恶行。那块布告牌仍然立在那里,只是人早已散去,村民们好象躲避瘟神一样远远地离开。不远处,一群普鲁士士兵正耀武扬威地拆除街道上的法语招牌,那些标注着熟悉文字的标牌被他们粗暴地踩得稀烂,然后点火烧掉……
我想:该死的,这里属于法国,他们没资格这么做,该有人去阻止的。但谁能上前阻止呢?这片土地从此已经属于普鲁士了,这里再也不是属于我们的家园了。
雨下得更大了,豆大的雨点无情地肆虐着,摧毁了周围的一切。我奔走在雨幕中,脑海里一片混乱。迷惘中,仿佛又看见自己正坐在那明亮的教室里,读着那些优美的文字。讲台上,韩麦尔先生的话语仍然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窗外,飘扬着鲜艳的法兰西国旗!
放学以后一年级作文【二】
我轻轻擦去课本上的灰尘,缓缓的将课本一本一本的塞进书包。想到明天就再也不能上法语课了,想到韩麦尔先生再也不能教自己了,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但当我看到韩麦尔先生高大的背影时,似乎又听到了韩麦尔先生铿锵有力的声音:法兰西人是最有骨气的,我们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顿时坚强起来,忍住泪水,抓起书包冲出了教室。
当我走到大街上的时候,镇上的铁匠华希特这时正和他的徒弟在收拾行李,准备逃离这座魔爪下的城市。铁匠华希特边收拾着行李,边对徒弟们说:我们已经成了亡国奴了,说实在的,离开这儿是对的,指不定哪天又发生战争了呢!听到这儿,我抽了一下鼻子,心中酸酸的。那块不吉祥的东西——布告牌,还站在原地,但是看它的人却渐渐地走光了,大概不想沾上它的晦气吧!此时的天暗了下来,下起了小雨,仿佛是上帝也在为阿尔萨斯哭泣。
画眉依旧是蹲在早晨的那棵大树上,但它的\'心情看起来似乎是糟透了。它的叫声变得凄惨起来,似乎也在诉说着失去国土的伤感。它瞪大双眼,望着路上的每一个行人,也许它是想从行人群中找出那个使大家都不愉悦的罪魁祸首。这眼神,在正义的人们眼里看来,它代表了大家的心里话;但如果是在像强盗那样邪恶的人的眼里的话,就会变成恐怖的、可怕的,还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普鲁士兵依旧一二一二地齐步走着,他们昂着头,得意地掠夺来的土地重重地踏在脚下,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我也不避让,瞪着仇视的眼睛看着这群流氓。一个普鲁士兵冲着我吼道快让,小鬼,都当了亡国奴了,也不老实点!我再也抑制不住情感,大吼一声:法兰西万岁!我们属于法国!然后发了疯般地冲向了镇公所的布告牌,一把扯下那该死的布告,撕了个粉碎。还没等干完,我的脑门上已挨了重重的一枪杆,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放学以后一年级作文【三】
我低下头,开始整理书本,那些历史啦、法语啦,原来是那么讨厌,现在忽然觉得它们是我最亲密的老朋友。原来带着它们是那么沉重,现在忽然觉得它们以前轻多了。我反复地翻看着每一本书,霎时觉得那里面的知识都是在离开之前应该熟知的。唉,我真懊悔当初没有用功学习!此时韩麦尔先生的那些话又在我耳边回响。
“法语是世界上最精确、最明白的语言,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仔细地回想着韩麦尔先生的话,我真后悔当初自己不用功。
东西终于收拾好了,同学们已陆陆续续地散了,我也准备离开,然而一直挪不动脚步。我呆呆地看着韩麦尔先生,虽然他背对着我,但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的心声:"小弗朗士,法兰西人应当有骨气!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千万不能丢啊!"
现在,我要和你分手了,韩麦尔先生,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希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最后一课,正如我永远也不会忘掉自己的祖国……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抱起我所有的书象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财富一样,默默地在一片哭泣声中走出教室。
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韩麦尔先生仿佛凝滞了,痴痴地呆在那儿。我看着他那惨白的脸,心绪乱得像一团麻,胸口像揣着小兔子突突地跳个不停。
难道我们就这样放弃法语做亡国奴?就这样若无其事地离开教室?一连串的问号挤进了我的脑海。我茫然四顾,目光被飘动的字帖吸引过去,那些小国旗似的字帖,那些闪着金光的"法兰西""阿尔萨斯",透过它们我仿佛看到韩麦尔先生熬夜制作它们的情景,仿佛听到它在激励我要和普鲁士人战斗到底的声音。
低低的啜泣声唤醒了我,我看到很多同学低着头,正在压抑着不让自己哭出声,坐在后面的郝叟老头高高地仰起头,那愤怒的目光透过镜片,射向远方。从前的镇长抿着嘴,脸色青黑。邮递员看着韩麦尔先生,双唇颤抖,似乎就要哭出来。我不能再看了,泪水迅速涌满我的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