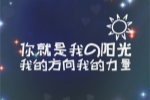亲情温暖我的岁月的作文【一】
温暖犹如千万朵蒲公英,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绽放。哪里有灾难,哪里有悲伤,哪里有……就会有它的身姿。社会中的温暖——在今年的4月20日,在四川雅安发生了大地震,在这一刻,我们都是雅安人;死亡人数每上升一次,可能我们中国人的血压就上升一次。所有的感动,都在这一瞬间袭来了。有一位母亲,这是值得一提的。地震过后,她自己又冲进废墟内,去抢救她的孩子。母女俩手拉着手,可是,都没能保住性命。这也许是‘最美动作’吧。所有人都在那个瞬间感动了,全部人都去献血了,一排一排的中国人……哦,不,是雅安人!在这一刻!我们都是雅安人!十多辆小汽车里面全部装载着矿泉水,方便面,为了就是能给雅安人多一点生的希望。
打与不打的温暖——有人说,温暖在一瞬间;有人说,温暖在长长久久;而我认为,温暖在点点滴滴中。我现在才知道,打与不打的奥秘。父母打孩子,是希望孩子吸取教训;不打,是因为其中有着温暖的爱。打与不打都有着无言的温暖。打,是让孩子隔绝最肮脏的品质的一种方式;不打,则是一位母亲或父亲对孩子的.宽恕。-班级里的温暖——步入新的校园,走进新的班级,微笑里掺杂了太多的无奈和忧伤。大家彼此都互不相识,为此,那班级里缺少了很多欢笑。也许是时间冲走了彼此间的那堵墙吧,班级里慢慢的多了些欢声笑语。上课时,同桌是警灯;没钱时,同桌是取款机;时,同桌是学习机。就这样,班级给了我们很多温暖。温暖的足迹——温暖在哪里?其实温暖就在我们的身边。匆匆忙忙的你停下脚步,你可以发现,温暖和我们没有距离。生活中不是缺少温暖,而是我们太在意那些阴暗面,从而忽略了太多美好的东西。其实温暖无处不在。
亲情温暖我的岁月的作文【二】
苹果的芳香妹妹飘入我的鼻间,萦绕在我周围时,我总会想起您——外公!您的爱,就如苹果的芬芳,氤氲在我心中,充盈着我的心房!
那一年,我趁着假期到外公家去玩,却突然看见,外公为我种的苹果树仍在,上面挂着累累的果实,看着满树的果子,我不禁咽了咽口水,抓住外公的衣袖,嚷嚷着:“外公,我要吃苹果!”
“还没熟呦!”外公满脸笑意,“等你下次回来看外公,外公奖励给你!”我依偎在外公怀里,拍手叫好。秋风拂过,那一树的叶,随风摇曳,似在吟着一首静谧温情的歌谣。
只是,此一去,便是五年,学业繁忙的我,再没去过外公家。
直到那个沉重得令我窒息的电话响起:“仔仔,快来医院吧,外公快不行了!”心中蓦地升腾起那个古老的落满尘埃的承诺:“外公,等苹果熟了,我一定回来看您!”
苍白的病房,惨白的床单,白得恐怖,浓郁的消毒水的气味夹杂着令人压抑的药味。推开病房的门,外公脸色苍白,无力地躺在病床上,眼睑耷拉着。大家正欣喜地望着终于醒过来的外公,医生一句“这是回光返照!”犹如当头棒喝,一下子浇灭了所有人心头升腾起的希望,沉默笼罩着病房。
我强忍住泪水,扑到外公床前,泪水朦胧间,我看见您长满瘦骨嶙峋的手中紧紧地握着一个布满黑点的苹果,那么虚弱的外公,却是那样用力地握着,您浑浊的眼中透露着只有我能读懂的不舍。
见我来了,您浑浊的眸子突然清亮了起来,挣扎着握住我的手,口中断断续续地呢喃着:“奖励……苹果……”您瘦弱的手拼尽了力气,颤颤巍巍地将苹果递到我手中,紧接着,您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
我望着您恬静的脸庞,心痛得似已无法呼吸,想起了那个久远却似又萦绕耳畔的承诺:“等你下次回来看外公,外公奖励给你!”“外公,等苹果熟了,我一定回来看您!”我食言了,我没有如约去看这个可爱的老人!每每苹果飘香之时,您定是站在苹果树下,独自喃喃不休,眼神充满期望地飘向远方:“苹果熟了,仔仔快回来了吧!”
窗外,风带着肃***的气息!
望着手中那残留外公手心余温的苹果,眼泪止不住地流着,这枚苹果,寄托着外公的情思;这份亲情,寄托着亘古不变的承诺。
风改变了它原有的肃***,如春风般温暖,心头不禁涌入一股暖流,这份爱,将一直陪我在记忆的长河中流淌。
又是一年秋风至。
老家院中的苹果树上挂满了果子,苹果的芬芳勾起了我内心无限的澎湃:“外公,苹果熟了,我来看您了!”
亲情温暖我的岁月的作文【三】
李欧梵先生是我敬重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读大学,第一次捧读《铁屋中的呐喊》时的震动和愉悦,及至读到他的《狐狸洞呓语》,始在语言的轻松机智和见解的独到深刻背后了解到欧梵先生“狐狸型”的治学方式和为人的性情,更添了一份学术之外的亲切。我耳闻后忙找来一睹为快,同时也在关注网上报端的书评;其间有两则评论、商榷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
先是9月7日《中华读书报》上刊登了徐慈威的一篇《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评李欧梵的新著〈我的哈佛岁月〉》,其后半月余,《新京报》“书评版”又登出了一则与徐文商榷的文章(9月23日,《“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兼与徐慈威先生商榷》),署名“舒平”。读完《我的哈佛岁月》,我原本想写点什么,一时没有下笔,正巧看到这两篇评论,还是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写出来。
这两篇文章的名字放在一起有点绕,先要解释一通。徐文题为“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在文中有一段关于“刺猬型”学者和“狐狸型”学者的论述,坦言“我宁愿相信,事实上李先生也是一流学者”,同时他认为“李先生的这本《我的哈佛岁月》,即使不用学术的眼光审视它,充其量只是二流著述”;而题中的引号一方面表明引自原作,另一方面也隐隐体现了徐先生的善意。舒文名“‘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一看即知化自徐文,舒平先生坚持称《我的哈佛岁月》是“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其实是以退为进的法子,说到底还是想让人承认《我》是“一流”学者的“一流”著述。
舒平就这个问题首先向徐文发难:李先生在书中明确地说过自己只是“二流学者,三流作家”,(书中欧梵先生说的是和“西方传统中的名家”相比,“以世界大师级的尺度来衡量”,“有时自嘲”,以此自况,这其实是看似自谦实则自负的说法),你非把他归入一流之列,莫不是想“借批判的对象来抬高自己”?进而以此猜测竟得出结论:“国内的批评界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些批评家专门喜欢拿名人开刀,借此打通自己的成名之路,即使批评的对象不够一流,也非要把他说成一流,否则自己的批评便会显得缺乏分量”。看完这段话我大吃一惊,徐慈威的文章写得很是平和中肯,(相形之下倒是舒平的文章到处显得尖酸),我竟没有看出包藏了这样的祸心,忙按图索骥地把徐文又读了一遍,除了读出诸如“由于李先生骨子里是位学者,所以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还是在在地透露出它所蕴含的或者说内敛的学术价值”等句子和为文的坦率真诚外还是没有其它——似乎是舒平虚惊了一常其实舒先生的话也并不新鲜,是文坛上的故伎了,前几年有个沪上文人就惯用此术,把一切批评者都看作“攀援的凌霄花”,这种话的恶劣之处就在于以自己已获得的话语权力而制止别人开口,幸而不是欧梵先生本人;我看到这类话一向有些愤懑不平,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发此旧论,让人不免惊讶,不过听来既颇为耳熟,就不会如小儿女羞赧而退,还要照做凌霄花。
舒平的文章存在两大问题,剖辨清楚,许多问题自然水落石出。舒文的第一类问题在于往往把一个问题推向极端,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歪曲了徐文的原意往往导致谬误,他再紧抓不放加以发挥,结果讨论的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我无暇指出文中无数的逻辑漏洞,仅举两例。
一例是徐慈威先生认为“以一个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而与哈佛女孩的妈妈去比试,去打擂,起点就不高”,舒平先生则说出这样一番话,“如果一个人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等,那就是思想有问题了”,“哈佛女孩的妈妈怎么了,人家能把女儿培养成才难道没有资格将自己的与众人分享吗?”前者提出的问题是欧梵先生作为在海外多年的学者、知识分子在书写个人记忆时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高度,这种被期待的精神高度使得论者认为李先生不应以一个畅销书作家——哈佛女孩的妈妈作为参照(至于到底应不应该,下面会详细讨论),后者并没有在这个问题的本质上作出回应或驳难,而是粗暴地给对方首先扣上“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思想有问题”的大帽子,然后是近似胡搅蛮缠的发挥,回头一看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什么时候前文中讲哈佛女孩的妈妈不能写书了呢?
另有一处,徐慈威举“罄竹难书”一例称《我的哈佛岁月》文字水平未免有些粗制滥造。至少在大陆一般的用法中,欧梵先生确实把这个词一连两次用错了。应该说徐慈威所指的“文字水平”就是指单纯的遣字用词,到了舒平的笔下,却颇为高调地称“我辈喜爱李先生文章,恰恰是喜欢李先生那种随意、潇洒,挥洒自然,天马行空的文风”,由“文字”到“文风”,舒先生偷换的概念可谓大矣!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舒平在文中提出,“徐先生认为李欧梵水平粗制滥造(看官注意,这里‘文字’又被置换成了‘水平’),我也想在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一句公道话’,仅从徐先生的这篇文章来看,徐先生自己的文字水平也未必堪称‘一流’,至少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都没能被说服!”云云,且不说这里的“文字水平”又不知何时变作了论理的水平,也不说徐慈威先生论理的水平到底怎样,批评对象和批评者之间有无可比,需不需要比,这大概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请舒平先生恕我言语稍有不逊,因为这里实在有些离谱了,“商榷”到最后却质问起批评者的水平以壮声势,实在有些不妥;我其实想说明的还是,当一个概念反复被置换时,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了。
舒文的第二大类问题,也是根本的问题在于舒平本人对于价值的评判缺少一种内在的尺度,这才导致了形形色色的不一致和整个文章的“格调不高”。舒文中至少出现了三种类型的著述:回忆录、畅销书和学术著作,对于它们评判显然不能执行同一标准:回忆录有自身的精神维度,畅销书要符合的是市场的准则,学术著作也自有一套学术的规范,当然回忆录也可能是畅销书,但总是要遵循最“本己”的价值尺度。舒平本人意识中这种尺度的缺席造成了文章的混乱和可笑,一方面质问“哈佛女孩的妈妈怎么了?……”,另一方面又毫无道理地假借正义之名批判所谓“所谓的学术著作”;尺度的混乱导致对所提及的诸种著述都缺少应有的尊重(误读也是一种不尊重)还是很表面的问题,我说的“内在”是指一本好的回忆录应是一部优秀的精神传记和心灵自传,而不只是身体和经历的纪录,欧梵先生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的研究者,作为“中国公共空间”和“人文空间”的实践者,作为海外“芝加哥大学中国思想者部落”的酋长,欧梵先生所代表的文化趣味、精神倾向和价值立场值得、也引起了无数的关注,人们有理由对欧梵先生的思想和精神高度提出更高的期待。舒平试图否定这种期待不仅没有抬高反而降低了这本书应有的品格。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以西方精神为背景、在俄罗斯思想烛照下的真正的“狐狸”,而不是一个在多元文化中栖身或逃避的供人玩赏的画了大花脸的波斯猫——难怪舒平先生那么津津乐道。
最后还是回到欧梵先生的这本新书。为写这篇文章,我把《我的哈佛岁月》又仔细读了一遍,无论是知识还是情感,在这本随性的小书中都很丰富,我认为其中写得最好、也是我最喜欢的,是几篇回忆老师的文字,如《史华慈教授》、《普实克》,《退休记事》也颇为感人,然而毕竟《我的哈佛岁月》是本匆促写成的书,没有来得及耐心地打磨,里面确实存在正如徐慈威先生所指出的一些不妥之处;至于书中“每每津津乐道的男女情爱之事”,徐慈威认为“未免不够恰当”(作为知识性的回忆录),舒平则认为是“率真”,是“真性情”的流露(作为个人的自传),我不作判断,而更愿意把它看作“道德判断被延期的领地”。不过舒文中说“今年终于读到了一本真正值得一读的书”,我还是觉得有些夸张了,如果舒先生真得这么以为,那实在是井中之论;而在其文末还有一段近似挑衅的话,我看后触目惊心,真真无言以对,其实舒先生多看几遍《我的哈佛岁月》中所论的书与人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东汉马援在《戒兄子严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深以为是,并同样以此为戒,愿与舒平先生共勉: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重之爱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饱学之士大多周慎守礼,肤浅之辈大多腾嚣猖狂。这里我绝无嘲讽舒平先生的这篇文章“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意思,我只是私下里觉得徐慈威先生一番寓褒于“贬”的平和之论可能恰恰是对欧梵先生的理解和尊重,不由让人想起书中写普实克教授和夏志清教授笔战的一段,一对朋友间的“笔墨官司”不但没有损害友情,反而见出了双方的学术风度和风范;而舒平先生以剑拔弩张姿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徐文的原意,自说自话近乎无理,更为令人遗憾的是与欧梵先生书中所透露的宽容平和亲切的人文气息相背离,同时也冲淡了回忆所弥散出来的可贵的温情。
亲情温暖我的岁月的作文【四】
先有李欧梵性格上的“狐狸”式之多变,才有其学术上的“狐狸”式之研究。李欧梵大半生经历与治学与此休戚相关。
《我的哈佛岁月》既以哈佛为题,自然撷取与哈佛有关的人生经历。故而书分两部分,一谈其哈佛八年经历,二述哈佛十年教学经历。此外尚有“附录”凑数,吹捧有之,可不必读。特别是他夫人的回忆文字,浓情腻歪,更可不读。
作为学者的一生,研究成果才是生命之花,灿烂无比,而人生经历或如缓流之江水,表面平静、方向明确,偶有暗流潜底、激荡不已。李欧梵从赴美求学至哈佛退休(2004年)的大半生历程,大抵也是如此。他出生于1942年,随后赴美,先是在芝加哥大学学了一年国际关系学,而后转学哈佛在专攻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现代文学,1970年获博士学位。1969年始,李欧梵先后就教于达特茅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后一站是哈佛大学,历时三十余年。看似平淡无奇,却又十分精彩。
或曰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用在李欧梵身上再恰当不过。李欧梵十分服膺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刺猬与狐狸之说。(有兴趣者可查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俄国思想家》26页)狐狸狡猾多变,刺猬专一精深。李欧梵常以“狐狸”自喻,所以在学术上每每“喜新厌旧”、“东摸西碰”。
实际上,应该是先有李欧梵性格上的“狐狸”式之多变,才有其学术上的“狐狸”式之研究。李欧梵大半生经历与治学与此休戚相关。从本书“序曲”一节便可看到,李欧梵大学毕业之时,决定他前往美国留学的原因并非有明确目的,而是“当时到美国读书是一种风气”,以至于到美国后究竟该学什么,他自己都迷惘不已。于是,也才有先到芝大读国际关系学,尔后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转哈佛大学学历史,再转而随史华慈教授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最后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却又兼顾思想史与文学的这么一连串“变数”。
把握此一关键,于李欧梵的求学、教学、治学等等一系列问题,便可了然于胸、无所滞碍。就连他在学生时代,为什么会上午到一图书馆,下午到另一图书馆,晚上再换一图书馆这样的小细节,都可以此观之。而他为什么前前后后就教的大学达七家以上,也不难理解了。
李欧梵的哈佛求学生涯,一言以蔽之,可以用费正清教授对他的称呼——freespirit(放荡不羁者)来形容。这指的是他在为学上的自由心态。所以,在博士资格口试的时候,费正清狠狠地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破天荒地考他历史的具体日期这一类细节问题——据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把他考得个丢盔弃甲,斗志全失。不过,费正清还是让他通过口试,并反过来安慰他“男人考博士口试,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生前有阵痛,痛完了生下来就好了云云。
让人艳羡不已的是,伴随李欧梵整个求学生涯的,是一位又一位的大师、名家。从就读于台大时的英美文学著名学者夏济安,到进哈佛后的费正清、史华慈、杨联升,乃至对他产生实质影响的普实克教授(该书附录有专文介绍)等等,大多是一代学术巨擘。这还不提他当年旁听时遭遇的如社会学家帕森斯等人。这在一般人眼里,却是想也不敢想象的。不过,所谓名师出高徒,李欧梵却似乎并未追从上述诸大师的脚步,却拐到另一条路上去了。当年他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时候,美国这方面的专家屈指可数。
至于李欧梵的教学生涯,该书亦有详细介绍。总体来讲,在具体教学上,李欧梵并非十分出色。特别是教本科生班,自己也承认失败。惟有五六人的小班,他得以因材施教(又是“狐狸式”的教法),故有“狐狸教授”美名。
亲情温暖我的岁月的作文【五】
如果要完整地了解李欧梵,藉由《我的哈佛岁月》这本自传,他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作品便有明晰脉络可寻,进而对他的学术生命及个人旨趣当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读书如坐地铁,到达终点之前必要一站一站地经过。李欧梵对我而言,也是一个站点。一度迷恋李欧梵,未曾谋面的老友绿茶故而寄来小说《范柳原忏情录》。在老家书房那硬木沙发上,曾为这本小书的文字倾心不已。如今在千里以外的寓所遥想那段可以静心读书的岁月,竟恍如隔世。虽然那不过是2001年的事。
后来,只要见到这一作者的书便会不由分说地买下,包括《铁屋中的呐喊》、《狐狸洞呓语》、《东方猎手》、《上海摩登》等等,学术论文、文化随笔、小说无所不包。那本《狐狸洞呓语》还多买了好几本送人。所谓FANS也不过如此。
这也算是与李欧梵老先生的一段书缘吧。于今想来,却有点儿莫名其妙的。到底自己喜欢这老头儿什么?买的他的第一本书是《现代性的追求》,这才代表他的正业——现代文学研究。但说老实话,这本书也是最近才嘱咐家人寄来,且匆匆一翻而过。也许是因着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才慕名拜读《范柳原忏情录》这本续貂之作?找出当时读书笔记,《范柳原忏情录》写得再好,与他自嘲为票房毒药的第二本小说《东方猎手》一样,不过都是他的“玩物”而已。可见,从一开始自己就没有正儿八经了解过李欧梵。
想来许多人也是如此。李欧梵得以确立其学术地位以及在美国大学里安身立命的现代文学研究,除非专业人士,想必许多读者都兴趣不大。试问,他那本研究鲁迅的大著《铁屋中的呐喊》有几人认真读过?而他的文化随笔倒是在内地大行其道,出了一本又一本。他自己也是一点儿都没有哈佛大学资深教授的派头,一会儿出书(《过平常日子》)大曝个人隐私,一会儿对话无厘头影星周星驰,乃至被称为“小资偶像”、“时髦教授”。即便是这本新书《我的哈佛岁月》,一开章就摆开要学《哈佛女孩刘亦婷》写畅销书架势,让人苦笑不已。
之所以花了那么多笔墨来描述作为“他者”的李欧梵,无外想说明其人其文某种程度上被“简单化”了。如果要完整地了解李欧梵,藉由《我的哈佛岁月》这本自传,他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作品便有明晰脉络可寻,进而对他的学术生命及个人旨趣当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亲情温暖我的岁月的作文【六】
父亲的车稳稳地停在桥上,这座桥是上学的必经之路,路有柏油铺成,而两旁的石雕石杆。存有古风余韵,桥正对着红绿灯,一停就意味着两分多钟的流逝,上学之路分秒必争,等待总让我心急如焚。平时,我的吵嚷催促,换来的总是他不急不慢的话语:“别急。”我每次都是在不理解中闭上了眼。这莫名其妙的减速停下,竟成了父子间的一道鸿沟。
那是晨光熹微,尚在路上的我享受着清晨带来的喜悦。我眯着眼观察着道路两侧,那条蓝色丝带浮现。绿灯上有十秒,必定能过!可我突然感到背垫的挤压,车竟减速,恰被拦在红灯前。惊鄂与不解如火般窜出,父亲缓缓转头,我赶忙闭上了眼,装作熟睡。耳中捕捉到他的笑,我可以想象出他微微上扬的嘴角,随即而来的是他的喃喃自语,多睡会儿,挺好的,心木然地陪敲击了,我紧抿着嘴唇,努力,抑制此刻的澎湃心潮,脑海中浮现出他微垂的双眸,父亲大概是无论绕了我的疲倦吧!
期末临近,每一次挑灯夜战,他从未像母亲一样道出关切的话语,那看似薄凉的心中在掩藏这份难以察觉的温暖!父亲正为彼此心间的鸿沟,以一己之力努力架起了通往我心上的桥,可我呢?车再度驶上桥,此刻的我并未享受着酣然,车一如既往地缓缓停下,透过眼缝,我看到他饱含深情的回眸。
“爸,吃个蒸饺吧。”我蓦然地起身让他温柔的眼神中多了一份惊愕,当我捧出放在书包的蒸饺盒时,他伸出的手竟有些为微微发颤。他因惊讶而伸展的五官隐有沟壑,年逾50的他是不是第一次享受到我对他的主动关心?我的心不由的钝痛着,巍巍颤颤地将真角和伸得更近些。他抓住蒸饺盒,指关节触碰到我的掌心,带着只只属于父爱的温度。他将蒸饺一下送入口中,这位,应送子上学而仍末吃早饭的父亲,他的脸上洋溢的不仅是如愿得偿的满足,他用欢喜的眉宇,张合的嘴巴,极力掩盖着眼角即将涌出的泪,好吃,他含糊不清地说,不知是因为嘴中的食物,还是因为内心的颤抖,心潮澎湃之中,我看到那座心与心的桥梁正在建起,高峡变得通途,不再是一种愿望。
灯由红转绿,潜行的车,弥漫着温情,弥漫着感动,心与心之间的桥梁,仅凭一人难以建起,唯有一起为之添砖加瓦,方有建成的一天,而当爱之车驶上这座桥时,将没有红灯,没有刹车,一路畅通无阻。
亲情温暖我的岁月的作文【七】
现代性理论是李欧梵的“手术刀”(当然不止于这一把,“狐狸型”学者的一大特征就是理论之“刀”又多又快),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
学者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这话的确精当,与李欧梵自承为“狐狸型”学者可谓款曲暗通,遥相呼应。在治学上,李欧梵多方出击,频频得胜。李欧梵的著作更是纷繁芜杂,极尽“狐狸”之所能。
他的老本行现代文学研究自不必说,一本《铁屋里的呐喊》就把鲁迅打回“人形”。在文化研究上面,一本《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集现代都市文学、报纸期刊等诸多文化要素研究于一体,奠定其内地文化研究先锋的地位——虽然有人说毛尖女士译得不好,并挑出毛病不下五十处。但至少在我当年读来,依旧让人心潮澎湃,茅塞顿开。特别是将《子夜》里的小资成分“揭发”出来,以及把张爱玲定位为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的终结者,让人为之耳目一新。
此外,李欧梵当年赴美求学时多有寂寞,便以看电影、听音乐打发时间,由此竟也闯出一条新路,从而对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通俗电影有独树一帜的研究。还有,他对上至琼瑶下至王文华等通俗小说也有高见。甚至于日本动漫《风之谷》,他竟用来作为教授卡夫卡的“道具”。可谓大俗大雅,雅俗共赏。凡此种种,可以参见他的新著《清水湾畔的臆语》。
现代性理论是李欧梵的“手术刀”(当然不止于这一把,“狐狸型”学者的一大特征就是理论之“刀”又多又快),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现在有转为“正业”的趋势)。对此,俨然已是老“狐狸”的他,当然深自明了。
所以,如果对李欧梵这大半辈子作反思,径直可以参见《我的哈佛岁月》“结语”一节。我对此节几乎全部赞同,除了有人说他是“二流学者”,而他却变本加厉地自嘲为“二流学者、三流作家”这一点有不同看法之外。我的意思是,我只同意前半句,不同意后半句。就目前来看,如果将李欧梵与他的业师们比起来,“二流学者”他是当定了(这就是吃了“狐狸”的亏)。然而,就写作水准来说,李欧梵不遑多让,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流作家,包括他的情书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