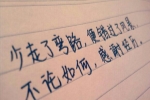秦腔作文200字左右【一】
落户西安,晚上出去散步,远远地听见了唱秦腔的声音,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是枣园的自建乐班在唱秦腔,他们唱得有板有眼,伴奏、音响俱全,观众也不少,在场的观众以中老年人为主,但这声音、这场景却唤起了我久违的童年记忆——在河南生活了十五年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秦腔了。因为河南是豫剧的天下,在那里生活久了,我也能哼一句“刘大哥说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但始终不喜欢豫剧,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节目办得非常红火,每一届都有出类拔萃的小戏迷被身边的人喜爱,我却没有感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一种地方戏剧。大西北的广袤,黄土地的厚重,孕育出了秦腔这种粗犷、苍凉的戏剧形式。
我生长在陇东高原,小时候每年春天的交流会、过年的庙会,唱大戏是最重要的娱乐方式,大戏就是秦腔,偶尔好像有眉户和碗碗腔。幼小的我总是软磨硬泡着要跟着大人们去看大戏,但看了一晚上一句唱词也没有听懂,充其量就像鲁迅的《社戏》中所描绘的那样,只是看着台上的热闹,特别是丑角出现的时候抬起沉重的眼皮,提着兴致看一会儿,其他的都迷迷糊糊,但唱秦腔时锣鼓喧天的热闹、板胡响起的激昂却永远吸引着我……
80年代在我们家乡陇东地区,应该是秦腔最繁盛的时候,看戏是要买票的,一张票白天5分钱,晚上1角钱,遇到新剧本观众是排队买票,交流会结束的时候还会加演,会提前预告,那种看戏的热情是盛况空前,县剧团的主角大人们是如数家珍,他们最期盼的就是西安来的演员,说起西安易俗社的秦腔演员,他们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不亚于现在一些明星的狂热粉丝(所以我送给久居福建的父母最好的礼物就是带他们去西安易俗社看一场秦腔)。
大概在我十一二岁那年的交流会期间,中午放学回家,我看见戏院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手里拿着票,排队进入戏院,我非常羡慕,很想进戏院看戏。这时我碰见了爷爷,我就嚷着让爷爷带我去买票看戏,也许爷爷舍不得那5分钱的戏票钱,也许爷爷还有事情要忙,总之,爷爷说他不能带我进去,但是他可以给我找个熟人带我进去(小孩子自己进去要买票,但是一个大人可以带一个小孩儿),我看见爷爷在卖票的地方张望了一会就过来对我说,他找到熟人了,让我跟在一个排在我不远处的老爷爷身后进去就行,他还再三叮咛我,你一定要拉着他的衣服啊。当时,我心里想:既然是爷爷的熟人怎么没有见他们打招呼啊,可是想看戏的渴望让我没有来得及多想,就战战兢兢地拉着那位老爷爷身后的衣服慢慢挪,那个老爷爷回头看看我也没有说话。就这样我混进了戏院,里面黑压压的人群,我根本看不见台上的演员,只听见锣鼓和粗嗓门的唱声,没有人和我说话,我突然觉得索然无味,很快就回家了。如今我已过不惑之年,爷爷去世也已经二十多年,但那次看戏的情景却历历在目,我后来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爷爷跟本就不认识带我进戏院的人,他只是不肯让我失望,就想了一个办法,让我大着胆子溜进了戏院。爷爷是个聪明的老头儿!
当时戏迷热情,戏剧市场也很繁荣,我想大概那时候秦腔演员的收入也不错吧,我们的街道就办了个戏校,邻居家的姐姐就此辍学去学唱秦腔了,七八岁的弟弟嗓门响亮,他拿根棍子在我们的地坑院子里经常吼秦腔,还有板有眼的学唱了一段《铡美案》中包公的唱段,在学校竟然被老师请上台清唱,后来县剧团的人竟然看中他了,让他去县剧团唱秦腔,要不是父亲的阻拦,他也是一名秦腔演员了。
我总认为在所有戏曲中,秦腔是最好听的,虽然我不会唱,也不大懂。但是我能感受到秦腔的灵魂:秦腔的悲怆会让人潸然泪下,秦腔的热烈会让人喜不自禁,秦腔的高亢会让人荡气回肠。
前一阵谭维维将华阴老腔搬上《中国之星》的舞台,让全国观众为之疯狂,可是我觉得那开场的一声吼,又何尝不是秦腔里面黑脸老生的唱法呢!
我希望陕西卫视的《秦之声》能够办得像河南卫视的《梨园春》一样的红火,这样会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秦腔,爱上秦腔。因为我的儿子不知秦腔为何物,他是听着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和周杰伦的歌长大的,已经长大的他不知道传统戏剧。秦腔是我的童年精神乐园,所以我骨子里喜欢秦腔,可是秦腔唱段好像一直是《三滴血》《屠夫状元》《铡美案》《三娘教子》之类的传统曲目,新创作的具有时代感的很少,能让年轻人接受的更少。
那个曾经吸引我的枣园秦腔班子已经被广场舞挤走了,因为听众越来越少……我也加入到广场舞大妈的行列了。不过,我依然深爱着秦腔,期待着秦腔的新昌盛时代!
秦腔作文200字左右【二】
一口气读完《秦腔》,只觉得字里行间有一种巨大的真实和感动。细细地反复读,便觉得眼前浮现出一张张逼真的朴实的面庞,耳边响起了高亢嘹亮的唱腔,它飘荡在辽阔的黄土高原上,起伏在沟壑间。一种民间音乐竟能在瞬间便显现出它的魅力,折射出它的光芒,这恐怕就是音乐的灵魂所在吧!
或许对于现代的都市人来说,秦腔是一个古老而又陌生的名词。的确,我们的身边有各种音乐,还有人把民间的河南梆子、京剧、黄梅戏称为音乐。音乐在装点人们生活的同时,不但陶冶了人的情操,也升华了人的灵魂,彰显着一种个性。
秦腔也是。正所谓“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曲存异……爱者便爱得要命,恶者便恶得要命”,由此便也不奇怪了。外婆的'家乡地处陕甘交界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秦腔作为一种民间音乐经久不衰,也正是因为处在秦腔的源头,在那里,不论男女老少,不论是闲暇还是劳作,顺嘴都会唱上一段儿。
清晨,看那拿着扁担挑水的村姑们嘴里唱着小调,一天便开始了;傍晚,暮归的羊群中放羊汉嘴里唱着秦腔,踏着夕阳回来了;晚饭后,女人们纳着鞋底唱着、哼着,男人们抽着旱烟打着板,月色和星光下,他们是快乐的,知足的。
我还记得外婆最爱听《窦娥冤》,对于秦腔我也是从外婆那儿知道的。她常给我讲窦娥的命是怎样的苦,怎样的含冤而死,使三伏天突降大雪……每次讲到这儿,外婆总是双眼蓄满泪水唉声叹气地为窦娥鸣不平,她是那样的全神贯注,仿佛已融入了戏中。我常想是什么使一个花甲老人如此全身心投入呢?因为秦腔来自生活,贴近人们的内心;因为“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乐趣,变得丰富。
音乐是有灵魂的,我惊诧于它的力量,它隐藏于人类
其实,有谁能诠释秦腔,又有谁能读尽秦腔?秦腔犹如精灵,钟情于每一个热爱他的人。面对秦腔,我仿佛在面对黄土高原上那些刚烈、粗犷的汉子们的痴迷、狂热。面对秦腔,我深深理解了这片土地上辛苦劳作的人民的大苦大乐,快乐知足。面对有灵魂的秦腔,我们便也有了一份平和,一份尊重!
秦腔作文200字左右【三】
《三娘教子》是一出传统戏,现在迟小秋老师为此剧增益首尾,又基本保留了传统戏的精髓,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谢温老师能给我这么好的开阔眼界的机会,虽然我接触程派艺术的时间还很短,懂的还非常少,但是已经被程派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尽自己的努力跟老师学习,不仅仅是学习程派的艺术,还要跟老师学习更多做人的道理。